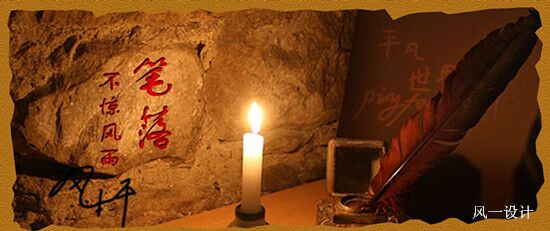【江山·根与魂】【东篱】为了一个字——峱(散文)
【江山·根与魂】【东篱】为了一个字——峱(散文)
![]() 一
一
在青州,我脱了一个字的盲。这个字就是“峱”,读作nao,阳平调。明大画家董其昌《画旨》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行千里路,认识一个字,也可以说,为了一个字,也不负青州识字一个之行。
青州博物馆的三楼北首设一个“峱专买”区,我是从服务员那学会了这个字,略知是特产于青州的古代怪兽。中国之大,峱,为青州独有,堪称大观。
这个“峱”字很奇特,在电脑的常用字库里一般是检索不到的,查辞海见词条:古山名,在山东省青州境内,靠近淄河。在汉字里,只为一座山而造一个字,并无别的义项,一座山,专用一个字,这是怎样的特权和殊荣!凭着这一点,我不能不重新审视。
走出博物馆,我站在博物馆下的广场入口,仔细端详两边的峱卡通动画造像,原本以为是个“四不像”,感觉就像个唐老鸭,并不在意。青州人给的名字是“峱宝宝”,面相如狮子,额头一簇火焰,鼻子深凹于眼睛之下,满口是舌头,四颗牙齿,浑身长着鳞角,又是一种可爱的样子。既然是上古神兽,画个什么样的造型,我们都不能说出什么。真是天下无奇不有,青州更奇!
应该说,峱,代表了青州有着很古老的历史,发现峱,大约在2500年前,也就是说,此时已经有了“青州文明”,为其命名,为其写诗,文字和诗歌是文明的显著标志,这就是青州的骄傲。史学界一直例外地统一了对文明的认识,认为文明产生的标志为金属工具、文字、城市的、国家的产生和出现。文字赫然列入,而且文明程度的高低主要由文字决定的。况且,青州还作为南燕国的都城而存在10余年,文明的根基无可撼动。一只峱,可以作为一种图腾一样存在,进入青州今天的文明进程,已经很不简单了。如果青州只宣传这只峱,我都会欣然前往。文明旅游,较之文化旅游的概念,更具探索性,旅游的深度发展,应该依赖于文明的底蕴开发。
就像我所在的荣成,我们都以秦始皇到过荣成的天尽头巡视大秦疆土而感到自豪,这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下的文明封疆之旅。不忘初心,也不能忘记迈开的文明第一步。
二
峱山,载着一章“齐王猎峱”的故事。春秋时期,在青州西部的淄河南岸的稷山附近,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野兽,相貌狰狞,人见人恐,鬼见鬼愁,践踏庄稼,糟蹋财物,扰民不安,地方上报请除。齐王亲自领兵而至,亲登山巅,趁着夜色,合力包围,短兵相接,弓弩齐射,终于剿杀。
传奇的围猎,是国王炫耀“尚武”的一种方式,峱山围峱,应该在一段时间成为齐王朝朝事的精彩主题。
晨曦东升,突然发现稷山的南北各多出一座山,北山如牛形,后人称“牛山”,而南山与北山并不对称,怪形如兽,不像马,也不似牛,不像虎狼,也不似猿猴,样子怪异。为纪念齐王猎怪,总要给这只怪一个名字,于是一干随行文臣就开始了造字。一犬一丑一山,加以组合,会意为“峱”,称山为峱山。
面对这个字,我想到“仓颉造字”,其实,仓颉只是造了部分汉字,很多字应该是众人合造而成。至于后世诞生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总结了六种造字法,书中把“峱”列为形声字,“从山狃聲”。这样说来,那个传说,应该是一种民间演义,虽不足为信,但更有趣味性。其中包含着精彩的审美,以动物象形,历来是中国山的命名方式,例如“象鼻山”、“马鞍山”……
关于“仓颉造字”最早的记载是《荀子·解蔽篇》,这是一个涉及文字起源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青州,在造字文明的过程中,就当下所知,有着一“峱”的贡献,“仓颉造字”的“造”也有着整理归档的性质。
《诗经》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更是文学的开山之作,几乎没有一首“国风”可以直接写一地风情的,而独章写青州“峱”的,赫然在列,名《诗经·齐风·还》,篇幅不长,请允许我全文引述——
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
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
并驱从两牡兮,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阳兮。
并驱从两狼兮,揖我谓我臧兮。
这是再现那次“猎峱”的场景,歌颂围猎人的敏捷、勇敢、善良和顽强,但主角变成了两个青年猎人。据说,这是齐哀公时期的一首民歌。诗歌对峱山的细腻描写,再现了峱山的风貌。从内容看,完全打破了纪实的格局,突出了创作的元素,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刻的启蒙意义。我们完全可以说,峱,对文学也有着贡献,能够进入文学的视野相当不简单,起码是一个奇特的文学歌咏对象。
“诗三百”,为了一个“峱”字,不惜篇幅,可见峱山在当时的名气,的确,“山不在高”,有故事也一样可以为人注目。在齐鲁一带,也只有泰山和峱山进入了《诗经》的篇目,有“泰山岩岩”(《诗经·鲁颂·閟宫》)句为证。峱山,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字学的贡献,不容小视,尽管这个字的使用频率今天几乎等于零,它的存在,让我们看见了古老。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不看出处,无论名望,常常是小人物却走进了文化关注的视野。一代君王,一个大事件,有的不一定被文学关注。这种包容性和柔性,足以让我们继承光大。
三
从凤凰山路返回,加足了车油,尽管青州还有很多风景都一再招惹着我,我还是要往峱山进发,我要去看峱山,看一座奇怪的山。我已经背熟了《诗经》的“还”篇,我觉得,此时能够做的就是背熟“还”篇,这是以我的方式,礼敬青州古老的文化。可车在导航下一直沿着“齐王路”向西北的“临淄”方向前行,峱山在哪?青州的山,不像云贵的喀斯特地貌,突然就耸立于眼前,也不高,很谦逊的样子,不喜欢挡住我的汽车。再次确定目的地是“峱山”,但没有国道,十多里的样子,哪见什么山,也许是样子太丑不肯出来见我?我窃改一下吧,去掉那个“丑”,把犬旁换成单人旁,怎么样?那还是峱山吗?有时候那些篡改历史的人,或许也像我这样跟历史开玩笑吧?只是图个有意思而已。其实,我产生这个想法也有根据,最早的“仙”,多是半人半兽的形象。或,人兽结合,或鸟人拼接,从“峱”字看,似乎也存在着这种关系。
我不能错过在峱山周围怀古的机会,打开手机的百度,去仔细阅读齐桓公和宁戚相遇的故事吧。齐桓公征伐宋国归途就走过峱山,或许我的脚步重印,或许就在《诗经》的“遭我乎峱之阳兮”,峱山之阳,它的南面是黑山和柏山,一条沟直通淄河,这里抵达临淄才是最通畅的路。或者是为了看看先祖齐哀公围猎的地方,折道而来。历史总是这么巧合,从不缺少故事。
一个名声很好的君王,一定有奇遇,他的一路肯定写着缘分。
被誉为卫国贤士、满腹经纶的宁戚,就站在峱山之阳,戴着破旧的斗笠,光着脚丫子,赶着一辆吱呀作响的牛车,时不时地敲击着牛角,哼唱那首讽刺时政的《饭牛歌》。歌词是后代元人洪希文创作的:“牛吒吒,蹄趵趵,枯萁啮尽芳草绿。自晡薄夜不满腹,撷菜作糜豆作粥……”锣鼓听音,唱歌听调,齐桓公到底还是听出了歌词表达的不满情绪了,齐桓公停车询问,宁戚傲慢不理睬,眼都不睁。
“绑了!斩首!”齐桓公哪里受得了这一介草民的傲慢!
宁戚不惧。
“吾歌饭牛曲,与你何干!”宁戚道,“我卫人,汝路过吾地,还这等傲慢!”
到底是谁傲慢?齐桓公有了分辨的兴趣,遂转怒为喜。
相国管仲却知宁戚是一个人物,便趁着齐桓公面带悦色极力荐举。
我不知齐桓公和管仲如何劝说了宁戚,宁戚怎么跟着去了齐国。后来,齐桓公拜宁戚为大夫,与管仲同参国政。据说,宁戚负责齐国农事,成就突出。史传,宁戚著有《相牛经》,是中国最早的畜牧专著,这与青州人贾思勰著有《齐民要术》这样的农学巨著,是否有着地域上,时代风气上的一脉相承的渊源呢?这与青州这片古老的土地文化,是否有着关系?以我的知识,无法断定,我只是站在峱山附近,有了这些模糊的思考。
这是齐桓公“礼贤下士”的经典故事,流传至今,依然生动。据说,临淄李园街道办事处柳行头村还有“宁戚大夫饭牛处”的石碑。我想,这个碑碣是不是应该置于峱山之阳呢?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人们喜欢这样的故事,尊重这样的文化,放在哪里都是正确的。宁戚“饭牛”之举,是不是和这个样子奇怪的峱山,有着几分相似啊!宁戚“饭牛”,并无求遇的心机吧,但他遇到了,遇到了敢于屈身求贤的齐桓公。为什么这个故事偏偏发生在峱山之阳,而不是别处?历史就是那么巧合,没有人深究这一点。我们也总是希望历史跟自己发生巧合,这是不是国人的美好心理使然呢?
四
一座山,峱山。我觉得,没有一座山能有峱山如此传奇。
一兽曰“峱”,一诗载于《诗经》,一贤叫宁戚。兽,是宝贝,怪不得在青州博物馆设有“峱宝宝”专卖,不要以为青州人喜欢“猎奇”,是青州深博的历史,让我们总能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到传奇和精彩。一诗,兴也。《诗经》开辟了“赋比兴”文学表达经典的先河,这样的“兴”,如果仅仅理解为“起兴”就显得不足了,这样的吟哦,也歌吟了青州迢远历史,尽管是一个开头,此后的青州,一定都是在歌吟的节奏里。一贤,才也!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人才始终是复兴的保证,人才不一定都在峱山之阳,华夏大地有太多的贤士,如今,不必像曾经那段齐王于宁戚相遇故事,依赖于巧遇,人才的通道一直打开着。未必唱着“饭牛歌”表达着怀才不遇,才会引起注意和重视,很多领域,都是敞开着门户,是人才可以走进来。
古老的中华文化,写在一座峱山上,这是文化之源,我们走过了文化贫乏的时代,迎来了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不应该忘记我们民族文化的出处。
为了懂得一个“峱”字,兜兜转转,一点也不觉得此行有什么不值。这个字,是青州文化的一个精彩看点,闪着光,与众不同,尽管我是刚刚做了入门的学习,但已经引起了我对青州这座古城的好奇,还有多少如“峱”有着相似传奇的字,多少值得一读的经典故事,未被我发现,我应该再次走进青州。
古籍记载说,齐哀公已经剿杀了那只峱,我以为并非真实。峱山还在,一定有峱出没,或许那些峱暂时躲避了,2500年的物种变化,说不定已经变了另一种样子,变得不丑了反而更可爱了,像宠物一样。我们无法睹见曾经的峱,但在青州博物馆的广场前可见,它已经成为青州人热爱自己的峱文化的图腾,灵魂不息。香港《大公报》在抗疫期间,盛赞峱是“青州的瑞兽”,有人推测,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貔貅,而青州7000年的发展史,也雄辩地证明着这个结论有可能成立。
峱,也给今天的青州带来文化生机。围绕着峱,诞生了文创团队,他们的文创精神是,把握峱文化的根柢、内涵与神韵,挖掘峱文化的时代价值。我在博物馆前见到的峱卡通造型就是这个团队的作品,他们把峱山文明和当代的博物馆对接起来,有了跨越时空的神奇感。
苏轼曾说“人生识字忧患始”,(《石苍舒醉墨堂》)他写字写诗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纯属牢骚话。鲁迅说“人生识字糊涂始”,是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要追根溯源何其不易!我在青州认识一个“峱”字,增加了学识,澄清了认知,一个字穿起了一段人文历史,让我认识了古老的青州,何其幸也!我要说“人生识字幸运始”了。
2024年7月17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