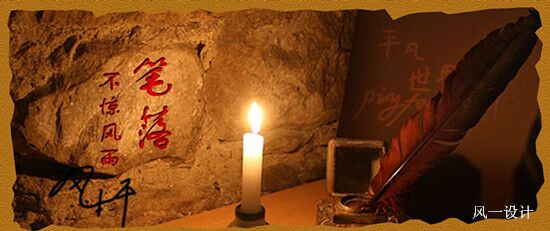【东篱】总有晚风惹轻愁(小说)
【东篱】总有晚风惹轻愁(小说)
一
李武刚到江北时正值风华正茂,而且还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心乐意。先好不算好,后好才算好。逝去的时光就像天际划过的流星一样,不知不觉李武在江北30多年,前些年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了。在岗时,李武天天觉得有做不完的事,常常被工作和因工作带的烦琐事折腾得心烦意乱,巴不得早点退休,过个悠闲自在的日子。殊不知,这早九晚五的机关生活,早已和他的身心和谐共生了。在这片由工作支撑起来的天地里,李武劳有所得,忙有其乐,看似很累,实际上这样的日子是很充实的。
退休了,办公室钥匙交了,自己的头像也从大门的人脸识别系统中删除了,李武已真正成为这个单位的“门外汉”。人走茶凉,偶尔有事回到单位,门卫还拦着盘问个没完没了。李武仗着自己在院里工作多年,对门卫说话也不礼貌,前朝圣旨管不了当朝臣,哪想到门卫压根就不卖他的帐,说除非有熟人来接,不然今天就进不了门。门卫这边碰了一鼻子灰也就算了,到了科室李武也是十八个不如意,科室里新来的不是不知道他曾在这里工作过,却依然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好似这李武跟这单位就没任何关系;以前的同事,打声招呼就各忙各的,往日的热乎劲一点也没有了。
退休后,竟受到如此怠慢,这让李武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单位时,李武是个科长,在院里好歹也算个人物,自己分管的事基本上也是他说了算。在位时大家都对他毕恭毕敬的,到外地出差,或探亲,带点土特产,有科室同志的必有他的,别人没有他也有。在这一点,同事带点不值钱的东西,是人家的一份心意,至于其他东西李武则一概不收。在纪律这一块,李武是拎得清的。扪心自问,自己在位时,也没对下属吆三喝四的,退下来之后,大伙对自己的态度变化咋就这么大呢?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热情,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冷淡,同事对退休后李武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漠,李武想自己肯定是有原因的。可能自己在位的作派早已引起同事不满,只是碍于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没有发作而已。
回单位如此,到在社会上也是这样,他在职时,也能替别人帮点小忙。下班回到小区,熟悉的人都会亲亲热热喊他一声。退下来之后,不就是一个平头百姓吗,有的方面甚至连普通百姓都不如。这人啊,一旦离开自己曾经的一亩三分地,别人半点忙也帮不上,有时,李武觉得麻雀看见自己也懒得叫几声。
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往往和拥有的权力成正比的。离开权力要想获得别人的认可,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刚退下来时,李武还真有点不适应,可时间一长,就想开看淡了。这人世间,大多事情是平衡的,也许在位时有多风光,退下来就会有多落魄。当点小干部退下来,或多或少,每人都会有这样的礼遇。
李武三口之家,女儿未嫁,那点家务事,还不够勤快妻子汪芹塞牙缝的。公事半点没有,家务事一点也不做,闲居在家的李武终日无所事事。人闲心懒,他对繁琐的人情世故越来越懒得理会了。李武在江南出生,高中毕业后离开故乡,辗转多处,最后在江北落了户。李武离开故乡时刚满20岁,那时的李武身材匀称,1.7米的个子,还不到120斤,虽长相一般,但也没到丑到引人注目的地步。青春就像天边的残阳,几丝晚风一吹就消失了。李武老了,几十年过去,体重陡增了40多斤,加上个子又驼了些。看着街上溜达的李武,活像一只艰难挪动着的企鹅。
落叶归根是因为老去的叶子抗不住地球的引力,人这一生,也有点像树枝上摇摇欲坠的叶子,人到归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想到来处。人在他乡,年轻时对故乡没什么感觉,可人老了,蛰伏心中的乡愁被唤醒了,醒来的乡愁就像深秋的晚风,常常把李武的睡意吹得一干二净。可父母一去世,维系故乡的绳子断了。李武有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失去引线的风筝,想飞也飞起来了,回故乡连起个意他都觉得很难。若不是遇到非常特殊的事情,十年八年李武也不会回故乡一趟。对于故乡,李武倒有着蛮清醒的认识。谁的故乡不是一地鸡毛,只是没有把花团锦簇的包装挑开而已。没有回到故乡,故乡是悬在游子心头的一轮明月,可回到故乡,特别是在故乡住上一段时间,悬在心头那轮无比皎洁的明月就会长满霉点,就像漂漂亮亮的姑娘,一夜醒来,已是满脸的雀斑。人性经不住考量,故乡也不能久住,住久了,心中对故乡的美感就会跑到爪哇国去了。邻里间为了半分地,一垄庄稼,甚至是一言不合,便破口大骂,吵得十八代祖宗都不得安生;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为了不起眼的事,也会大打出手。故乡在李武的心头渐渐地沦为一片荒芜的旷野。
到了李武这把年纪,在故乡过得再不济的发小、同学早已儿孙绕膝,而自己依旧膝下荒凉,暗自想想便觉恓惶。生活上的不如意,让李武内心越发规避故乡了。对“近乡情怯”,李武比其他在外工作的人有着更加深刻的体验。他所在村的村口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即便吃饭时,常有人捧着饭碗到村口边吃边聊。人以食为天,老一辈人对吃都怀有一种敬畏之心,他们一看到小辈端个饭碗乱走,便会嘟嚷道:“一到吃饭,屁股上就像长几条腿似的,是不是不‘迎饭灯’,吃饭就入不了胃啊。”“迎饭灯”是李武在故乡时的家常便饭,对老一辈的话,他是左只耳朵进右耳朵出。可老了,李武每每走过“饭灯”聚集的村口,就像武工队在探照灯下穿越敌人封锁线一般紧张。常思而不敢常回的故乡,就像一轮清月悬在李武孤寂的夜里。
二
退下来后,李武除了喝酒,也没啥别的爱好,喝酒好似成了他生命重要的支撑。有一天,李武和朋友小聚回家,自以为没喝多少。他踉踉跄跄上到大桥,被冷风一吹,“哇”的一口把吃掉喝下的全吐了。李武最怕吐酒,一吐酒就心悸乏力,豆粒大的汗珠直顺着他的粗脖往下淌。实在走不动了,就趴上大桥的护栏上缓缓。李武的目光由上及下,由远到近,只见天上星光点点,脚下波光粼粼,远处灯光闪烁,眼前一窗窗明亮中透出的天伦之乐……天上人间宛若一幅幅静夜图。而自己的生活却是一地鸡毛,酒后的李武觉得活得特别委屈。一时性起,他拨通了老家发小章三的电话,把自己积郁心中的苦楚统统地说给了章三。倾诉完,李武仿佛觉得勒在心头湿漉漉的青蔓被割断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快感袭上心头。
半夜口喝,李武起床喝水,猛地想起了自己在大桥上给章三打电话的情景,李武懊悔不已。若非灌了几两“猫尿”,打死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心病说给章三。李武不禁心里一急,前额竟沁出了汗珠。他翻身取出床头柜里记事本,在本子上记下章三的电话,随即把章三的号码从手机的通信录中删了。酒后健忘,不看本子,李武是记不起章三电话的,这下李武觉得踏实了许多。
李武和章三两家相隔不到半里路,李武小时候是村里“鬼王”,三天两头带着村里小孩从村东头疯到村西头疯。而章三恰恰是李武的“跟屁虫”,李武上房揭瓦,下河摸鱼,上树偷桃,下地摘瓜……每回都少不了章三,章三是李武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两人是典型尿尿糊泥巴从小玩到大的骨灰级的发小。
那时,李武生产队的耕地中央有十几亩良田是另外一个大队的,感觉就像“鬼剃头”把茂密的头发给卷去一块似的。何以至此,李武到老也没明白。别的大队来这片地里种粮食有诸多方便,为图省事就在地里就种上了梨。梨的品种很多,有雪梨、黄梨、苹果梨……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梨还没成熟村里娃们就馋得不轻了。几年一过,附近人就把那块地叫着梨园,梨园成了生产队当中一个无人撼动的“独立王国”。梨园的中央被那个大队整出一块平地,平地中间盖了一座通梁的大草房。这大草房是梨园的仓库,梨园里还住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据说是个光棍。这汉子平时打理梨园,梨子成熟看梨。他是邻村人,是个光棍,估摸着有四十来岁,姓甚名谁李武一概不知。此人精瘦,个子很高,脸色铁青,三句话说不到一块,就抄家伙要跟人打架。上有老,下有小,谁犯得着招惹他。此汉到梨园不久,村里就有人给他起了个“青面狼”的绰号,这绰号是根据《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起的,因为青面兽是一个正面人物,这看梨的光棍不配用杨志的别名。梨子快成熟了,青面狼就搬出草屋,在梨树下搭几个草棚,没人知道晚上他住究竟哪个草棚。青面狼就像一匹出没在这片梨园里的孤狼,尽心尽职地守卫着自己的领地。
一年中秋时节,梨园的梨子成熟了。阵阵香甜的梨味无遮无挡地飘进了村庄,落在了村民的枕边。村里有个不知深浅的毛头后生半夜饿醒,那勾魂的梨味就像一根根羽毛撩拨着他饥肠辘辘的肚皮。看着悬在梨树梢上的明月,后生实在按捺不住了。他披件深色的小褂,拎上一个蛇皮袋悄悄起床了。他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摸到梨园,刚摘下一个梨,还没来得及送到嘴里,就被青皮面狼逮个正着。可怜又可恨的小伙,被青面狼绑在路边的树上。整整一天,只给水喝,不给东西吃。那是个很批“私”字一闪念的年代,人们对偷鸡摸狗的事是深恶痛绝的。后生被青面狼绑在路边,路上人来人往,人们对后生指指戳戳。后来,还是村里几个老爷爷不落忍,拿着拐杖,从青面狼手里救出了后生。可小伙偷梨的事,一传十,十传百,就像风一样刮遍了十里八乡。从此,后生坏了名声,一辈子也没娶上个媳妇。自从后生被逮后,梨子成熟的季节,哪怕全果园的梨都烂在树上,村里再也没有人去碰梨子一下,青面狼俨然成了村民心中的魔鬼。
梨成熟季节,是没人敢惦记梨园。但梨还没鸡蛋大小时候,李武和村里不少小孩早已惦记着树上的“星星点点”了。李武所在的小学为了贯彻“五七”指示,在学校搭建一个简易房子,养了100多只兔子。为此,学校还专门开设了劳动课,劳动课其实就是让学生离校去拔兔草。
那年刚入夏不久,李武、章三和另外一个同学,上劳动课时,鬼使神差转到梨园边。其实,这三人在梦中不知多少回嚼过梨园的梨子了。李武朝两同学使了个“坏眼”,两人以同样的“坏眼”回应李武。三人心领神会,一拍即合。李武望风,章三上树摘梨,另外一个同学在树下拾梨。分工明确,不到五分钟,三人就“收获”半篮梨子。在青面狼眼皮底下偷梨,无异“虎口夺食”。得手后,三人窃喜之情难以言表。说实在的,并不是李武三人偷李手段多高明,而是青面狼压根没想到,竟会有人来偷这刚刚成形的梨子。
三人带着半篮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撤离了梨园。当他们感觉到安全了,便蹲在田埂上。刚抽穗的稻子将三人遮得严严实实的。他们将梨在衣襟上擦擦就往嘴里揣,梨一丁点的甜味也没有,满是苦、涩、酸交织起来的怪味,只是因为久入梦中的梨,才不顾一切地往嘴里送。每人一口气吃了七八个,嘴巴全被梨染成深褐色。实在受不了这怪味了,三人终于停止了咀嚼,抬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得哈哈大笑。
轻佻的夏风吹过稻田,稻田里窸窸窣窣的稻浪声仿佛是对三个小馋虫的嘲笑。三人把苦涩不堪的梨倒进了稻田,胡乱地拔点草,又把篮里找早弄得蓬蓬松松的,一路欢笑,到学校交差了。
老去的李武一想起和章三偷梨的情景,昏花的老眼里就晶亮晶亮的。
三
李武高中毕业后去了北方,他和章三各忙各的,来往很少,特别是李武在江北定居后,除了偶尔通个电话,两人就没什么交集了。但李武心里遇到个坎,他总是想到千里外的章三。那个长得墩实矮胖,憨憨的章三,老实而善良,特别是章三的嘴巴紧,从不嚼舌根。不像村里的某些人,堂堂八尺汉子,这嘴巴跟乡下老爷们大裤衩似的,各处透风。无论该说不该说,为图一时痛快,或是为了显摆,啥话都往外说,就连和相好床上的那点破事也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当故事说。李武即便憋出阑尾炎,也不会跟这样的人唠不句知心话。人是需要交流的,情感是需要宣泄的,而章三恰恰是李武宣泄的最好对象,还要什么比把自己的心思倒在与故土上,能让李武释怀的。与章三闲聊,李武觉得就像水银般的月光洒在了清澈的湖面。
章三高中毕业时,成绩不很理想,复习再考,能考上的希望几乎是微乎其微的。章三是个实在人,不切实际的事,他既不多想更不会乱做。章三有一次模仿着人的口气,语重心长对李武说:“我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学校只是陪我长大,却不会给我活路。我是农民的儿子,当农民和我的八字相合,农民只有吃苦才有回报,说的不好听点,农民是属鸡的命,刨一爪才能吃一口,意想天开只能喝西北风。要复习你复习,我再也不想乱花一分父母地里扣出来的血汗钱了。”这些老气横秋的话,却很对李武的胃口。
回到村子后,章三到亲戚朋友处借点,不够部分,又托人到信用社贷点款。即便手头再紧,他也没向父母张口要钱。父母那几个钱拿来也不顶什么事,还让他们担心受怕。高中毕业后,自己想做啥事,章三跟父母只字未提。
好不容易,章三凑够了钱,他把村东的一个占地几十亩的水塘承包了。既养珍珠,又养鱼,苦心经营了三年,翘首以盼的第一批珍珠终于丰收了。只是国际形势不好,以外销为主的珍珠行业普通不景气,好在章三的珍珠圆润饱满,色泽通透,被国内商家收藏了。章三还清了债,还赚了一些。没想到在风平浪静的鱼塘里讨生活竟跟貌似八杆子打不到的国际关系竟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全部家当都押在上面,章三已没有退路。章三觉得唯有更加努力,把珍珠的品质再提高一些,才能在变幻莫测的珍珠市场上为自己赢得一线生机。章三手里虽然有了些盈余,但人却一天一天黑瘦下去了,有时隐隐地觉得右腹部还有些痛疼,胃口也大不如以前。他老婆严雪蕊,劝章三去医院查查,但每次都被章三顶了回来。严雪蕊瘦矮个,皮肤乌黑乌黑的,未出门前在她娘家有黑玫瑰之称。嫁给章三后,因为超计划生育,被罚得家徒四壁。人过50岁,越发显得黑瘦了,人们联想再丰富,也不会把她和当年的黑玫瑰联系在一起。严雪蕊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连最基本的医学常识也不懂,记得她自己初潮来时,以为老年人嘴里所说的“血崩”,把自己吓晕了。看着章一黑瘦下去,严雪蕊只认为是活重,身子骨亏了,吃点好东西补补就好了。到医院检查一颗药没开,光检查费一项就得花上百斤鱼钱,花那钱还不如烀只老母鸡给自己男人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