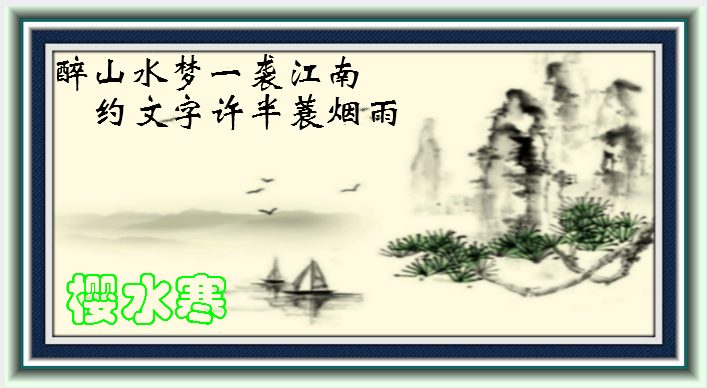【暗香】打年糕(散文)
【暗香】打年糕(散文)
十五岁上了高中,从此就错过了入冬后最快乐的事情——打年糕。
打年糕,是我们那里的土话叫法。实际上,年糕不是打出来的,而是几道工序后,切出来的一个个小方块。
上小学时,我看日本动画片《一休小和尚》里有一段打年糕的画面:两个人抡着木锤子交替着往石臼里捶打,几下之后他们坐地上美滋滋的品尝打好的年糕,嘴里不断地叫着好好吃,好美味。当时我还很不解地问妈妈,为什么他们的年糕是这么做,不应该是我们村上的年糕厂那种做法才对吗?
妈妈训了我几句:动画片看看就中了,你还当真了,看完了赶快写作业去……
年糕厂在我们村东边,开门见河堤,翻过去是三岔河口,地理位置绝佳。三座房子高矮相连,像极了手机的信号格。最高的那座一看建筑风格就有年头,青砖黑瓦,墙面的白石灰仅剩门头上的那块在强撑着,“年糕厂”三个红色宋体大字破破烂烂的就躺在这里。每年开工前,村里会安排人用油漆刷一遍——太阳一照,红艳艳鲜亮鲜亮,还挺好看。这里面放着锅炉和制年糕的机子,年糕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旁边的房子矮半截,也是青砖黑瓦,专门用来碎米蒸米的,里面三口灶锅和一台碎米机东西相望——这里也是我和弟弟当时最喜欢蹲点的地方。最矮的那个是后来扩建的,用作厂长和会计的办公室,从外面看就是个小破篷子。几种建筑材料混搭,放到现在就是行为艺术品。村里捡来的石头块做的地基,东边的墙是长短不一的红砖头,西面是从乡里砖头厂拉过来的废弃水泥通心砖;漏风和见缝的豁口用干稻草和小石块塞住;房顶铺的是扎好的干稻草,也就这块看着舒服整齐。
我们几个那时常窝在墙根下,偷听里面大人们的谈话。有时候还淘气的拿个小棍棍往里面捅他们的鞋后跟,做完坏事立马就跑远处躲起来,里面的大人跑出来骂骂咧咧,我们则放肆的哈哈坏笑。我记得有年热天下大雨,西边的半面墙塌了,留下了个大大的黑窟窿。后来用了一整块的塑料油布遮挡起来,底下用石头压着。每次起风的时候,掀的油布呼啦呼啦的响。虽然丑了是更丑了点,色彩上确变丰富了。
办公室里面很小,靠北边一副写字桌椅,两边各一条板凳,围一圈也坐不下几个人。因为没有窗户,黑黑的,白天也得开着灯。这个昏昏暗暗的小房间总给那时的我一种神秘感,像电影里的某个密室,每次去厂里都忍不住偷偷溜进去瞅瞅。
开工前,必要的机器检查和其他的准备工作要忙起来了:叮呤咣啷的响声不断从房子里传出来,外面架电线装电灯,拖拉机一车车地往厂里拉煤,往河里放管子引水路,河堤上大人们在钉木桩,搭晾干年糕用的架子,河里有人在刷洗晾干用的竹编床……差不多弄好这些,年糕厂会用毛笔写很多张大红纸告示,派人到临近各村张贴。接下来十几天,河堤上人车如流,比过年还热闹。
年糕厂的机子一转动,大烟囱就冒出长长的黑尾巴。村里家家开始忙起来:称米配米,淘洗,排队登记缴费领单子,等叫号安排打年糕。快的时候等个大半天,慢的要排到一两天后。
我们家通常逢周六日去打年糕,这样爸妈就多了两个小帮手。顺便还能给其他亲戚长辈家帮帮忙。称米配米是个技术活,也是人情的“算计”。自己家留多少做口粮,送爷爷奶奶家多少,还有姑妈姨妈舅舅家都要想着。一圈加起来,要打多少斤年糕才够,再算算需要备多少斤米,糯米粳米怎么配。每年爸爸端着杆秤,妈妈掰手指头算,俩人呱呱个半天。
爸爸把备好的米挑到河边,然后和妈妈一起淘洗。河边的石阶上都是人,站着蹲着,手不断地的在簸箕里翻搅——欢声笑语和被染白的河水久久不散。淘洗好的米被挑到年糕厂碎米蒸米的房子里排队,爸爸领到单子之后会让我和弟弟守在那里,特别叮嘱我们一定不要贪玩离开,等到有人叫他名字就赶紧回家通知他过来。不过好在我大伯大妈在蒸米房里做事,我们只要人不跑走了,就不用担心错过叫号。大妈会让我和弟弟蹲在门口的墙角,然后偷偷地塞给我们两大团米糕,浓浓的米香还冒着热气,让我们就在这里慢慢吃,等她叫我们回家喊爸爸。大人们进进出出的,不太能注意到蹲地上的俩小孩。我们手捧着米糕,吃进去的不仅是美味,还有其他小伙伴流出嘴角的羡慕。就是我家不打年糕的时候,我们也常在这里蹲点。
大米在碎米机器里转悠了半天后,变成细细的粉末,在出口下面的大瓷缸里慢慢的堆积成了高高的小雪山,淡淡的米香不断地往鼻孔里钻。每次妈妈都会用小扫帚尽可能的把细米粉末打扫干净,那是一年的辛苦和收获。之后,细米粉末被大木舀子小心翼翼地填满近半人高的木桶里,盖上纱布,在大锅里静静地被蒸成米糕。当时大妈就是负责这一道工序,她一整天就守在几个木桶旁,时不时翻开纱布看看蒸好没,哪个锅里水少了及时添水。哪个木桶里的米蒸好了,她会大声的叫喊几下“XXX家的打年糕咯,快去准备”,得到主人家的回应后,抱着木桶送到年糕机下面。
整个年糕机前低后高,造型有点怪,像个蝎子。低的那头是出年糕的小方口子,高的那头支个梯子靠着,有个人专门守在那里。他负责把大妈送过来的木桶倒扣在上面的大口子里,取走木桶后。用个大铲子把米糕切成小小的一块块。弄好后,大喊一声“XXX家的打年糕咯,开机子”。
几台老式皮带发动机同时发出的巨大响声立刻灌满了整个厂子,不一会儿小方口冒出一小团雪白,很快在一段光溜溜的铁皮通道上变长,像白娘子变成人之前的样子,一根专门用来降温的水管盯着它从头浇到尾。
这时候坐在旁边的女人用菜刀迅速把这条“白蛇”切成一个个小方块,它们顺势滑落进早已等在通道尽头下面大铁锅里的竹筐内,大铁锅里盛满了降温用的冷水……装的差不多了,会有人大喊一声“拿走,换筐子”,第一锅年糕就这么新鲜出炉了。
大人两手拎着框子的耳朵,赶紧小跑到晾干区,一股脑的扣在竹编床上。等候在此的大人小孩迅速的双手沾冷水把这堆年糕扒开,一个个的紧挨着摆放。有等不及的小孩事都没做,就抓一个往自己嘴里送,边吃边叫唤还跳脚“哎呀,哎呀,嚯嚯嚯……”年糕烫到嘴了。
那时候爸妈俩人一趟趟你来我往,转身总会撂下一句:赶紧的,后面的马上就来了。我和弟弟俩人手忙脚乱,根本得不到空偷吃。年糕必须要及时铺开晾干,不然黏在一起成坨坨了。最后一筐子弄完,我们一家站在竹床两边,慢悠悠地边吃边说边笑。冬天的气温低风也冷,忙活了大半天身体暖和了。嘴巴里嚼着热热的年糕,心里面暖和了。
等到向阳的一面结起了一层干干的皮,就要给年糕们翻个身继续风干。
为防止有的人家风干时间太长,会有人来回查看。 “这谁家的啊,能收了……”听到这声喊叫,就要麻溜地把年糕收起来了,腾出竹床给下家用。
爸妈担着两个稻箩,来回几趟挑完全部的年糕,重重的年糕压弯了扁担累得他们直不起腰。弄回来的年糕,铺在干净的袋子上。桌子上,地面上,地方不够几个板凳拼在一起放张簸箕空间又有了。
随便进到一户人家,一团团的雪白年糕像一个个雪球被搬到屋里。
第二天,妈妈随手从“雪团”上掰一些下来,弄点青菜放水煮熟。吃几个盛几个,用筷子挑一点猪油放在碗里,什么一休的年糕是美味,我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年糕。猪油的香味搭配年糕的软糯,加上青菜的清甜,最后碗里的汤水都被舔的一滴不剩。往后的两三天,晚饭后放下筷子。我和弟弟新的任务又开始了:挑回来的年糕还是黏在一起的“大雪团”,我们要把他们一个个的掰开,让它们彻底断了联系。全部弄完后,爸爸从河里担水装满大缸,把自家的口粮都倒进去泡水。定期换水,能保存较长时间。剩下的那些按照之前的“算计”,用干净的化肥袋子装起来称好,一家家地送过去。
上了高中后,路远住校,等到月尾可以回家了,都是吃现成的。再后来,妈说村里的年糕厂停了,是她和爸弄个小板车拖到乡里的年糕厂去打的。还问我是不是比村里的打出来的味道差些,我点点头:“嗯,没村子上打的口感好。”我转头回应她的时候,看见她眼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再到后来爸妈不去乡里打年糕了,说是年糕厂改了原来的经营方式。
现在是把打出来的年糕论斤称,直接用钱买。过年假期回老家的每顿早餐,满满一碗盛好的年糕端到我面前,冒着热气,里面有我从小到大喜欢的青菜,还有浓浓的猪油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