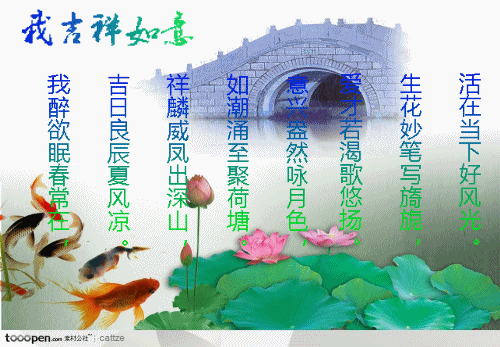【好韵】我命由我不由天(杂文)
【好韵】我命由我不由天(杂文)
中国文字学家王力教授曾写过一篇散文《溜达》,在文中,他对溜达、散步和逛街三个词汇进行了文学性的解读,所勾勒出的市井图景,总会让我忆起江南巷陌里的青石板路。老先生讲,溜达得往热闹处去,瞧那摩肩接踵的人流裹挟着油盐酱醋的气息翻涌,这话中蕴含着中国文人对市井烟火的深深眷恋。散步则要拣人少的地方走,比如松林小榭、曲径通幽之所。逛街则全然不同,重点不在脚上,而在耳听、眼看,如塑的圆腓等。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写过一篇散文《讲面子》,文中那只戴着花花绿绿面具的毛猴子,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耍戏,着实得意非凡。然而,一旦戏毕,锣鼓声止,终究露出毛脸的寓言,恰似一记晨钟,震醒了我们对“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沉醉。这可谓是五分钟的英雄美人,一辈子的禽兽。这两篇美文相隔二十年的时空,却在某个秋日的午后意外相逢,于书页之间碰撞出有关生存本相的璀璨火花。
王力教授凭借几个词汇成就一篇美文,将词语间的差异阐述得清晰明了,令人惊叹于他在语言学上的贡献以及文字表现的张力,其能精准描绘人的内心微妙世界,对绚烂宇宙进行艺术刻画与描摹,探寻发现语言未知之美。
哲学家艾思奇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巧妙地道出了人与禽兽本质的差异。人会装扮、会描绘、会抒情、会演绎。禽兽在同类间鲜少伪装,其逃生脱困的生存技能,像变色龙变色、壁虎掉尾巴、虫子装死等。有的在觅食时迷惑对方,比如漫步西湖孤山时,常见松鼠捧着松果端坐枝头,它们从不掩饰对食物的渴望;鹭鸟掠过水面捕鱼的刹那,翅膀划出的弧线永远遵循力学定律。动物界的伪装术皆是生存的利器。枯叶蝶化作飘零的秋意,章鱼用色素细胞编织迷彩,这些天赋的戏法只为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中延续血脉。而人类在进化中修炼出了更为精妙的幻术——在镜前描画的面具,既能化作社交场上的春风,亦可凝成谈判桌前的寒霜。
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唐代书生以诗文装点门楣;汴京虹桥畔的商贾,用珠玉锦绣包裹市侩。如今的互联网世界,九宫格里的生活被滤镜调成统一的暖色调,朋友圈中的笑容定格在嘴角上扬的黄金角度。我们在职场将情绪驯化为标准化的服务礼仪,在社交场把个性裁剪成合身的晚礼服,甚至面对至亲也要给真心套上丝绒手套。这种精心设计的表演,早已超越动物求生的本能,演变成文明社会的生存法则。就如哲学家艾思奇笔下的小毛猴,历经一定的世事,演绎过人类小丑的角色,在自己的族群中大显身手、独领风骚,就像人类获得某些荣誉、取得一些财富,便高人一等,变成了高人、仙人,继而追求长生不老,惧怕死亡不肯消亡,违背自然规律,逆天而行。
陶渊明辞官时解下的不单是印绶,更是层层叠叠的身份铠甲。他于南山种豆的拙朴之中,聆听着生命最本真的律动。庄子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这何尝不是对文明重负的警醒?当我们在名利场追逐金丝编织的面具时,是否还记得赤足踩在春泥里的沁凉?魏晋名士的广陵散早已消散在历史长河之中,但那些扪虱而谈、白眼向人的狂狷身影,依然在提醒着我们:生命不应是精雕细琢的工艺品。
电影哪吒2面对强势力,当莲藕重塑的身躯挣脱天命的束缚,那抹混天绫舞动的红光,照亮了多少被世俗绳索捆绑的灵魂。哪吒没有在各种压力和考验面前跪着求可怜,而是不畏生死站着战苍穹,大声高呼,“我命由我不由天”。做一次自己,活一次本真,为他人而活、为他人卖命,是一生最大的悲哀。
敦煌壁画上的飞天,褪去金粉后不过是质朴的泥土;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最动人的并非层峦叠嶂,而是画绢裂缝间渗出的时光包浆。真正的生命华彩,从来不在描金绣凤的戏袍之上,而在素履所往的山水之间。
暮色中的拙政园,荷瓣上的露珠正在坠落。这滴水历经云蒸霞蔚,穿越楼台烟雨,终究要回归大地。如同我们精心描绘的面具终将在时光中斑驳,那些用胭脂金粉堆砌的人设,终究难以抵挡白发秋风。不如学学终南山的云,聚散随心;效仿富春江的水,深浅自适。当我们在某个清晨摘下所有面具,或许会发觉:最本真的容颜,原是与青山对坐时,眉间舒展的那道浅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