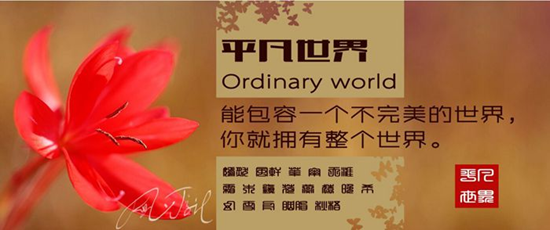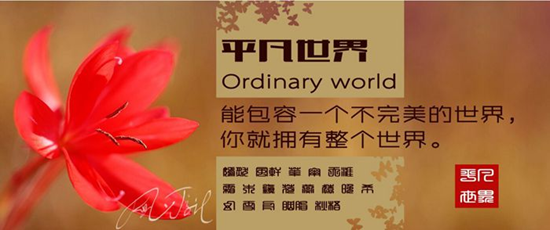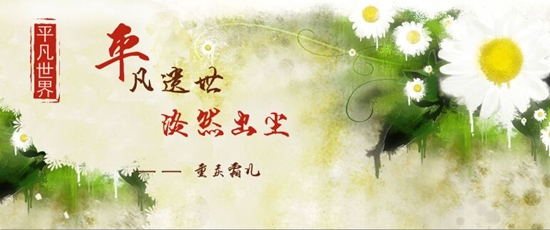【平凡】大长绠的平凡人生(散文)
【平凡】大长绠的平凡人生(散文)
![]() 春节前,回老家上坟,听说大长绠死了,属于寿终正寝。我便想,大长绠何德何能,竟然活了八十四岁,赶上了亚圣孟子,说“寿终”,那可真是“洪福齐天”了。还听说,大长绠从病发至心率衰竭、最终死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包括后事的料理,一直都是乡政府和敬老院一手操办的。当时也未通知其亲属,只是在火化后把骨灰转交给了他的侄儿,归葬到了老坟里。按照我们老家通常的说法,“正寝”是老式住宅的正房,叫做“堂屋”;一般人死后灵柩多安放于此。大长绠的老宅,“五保”后就归队里了,如今也另有其主,房屋早已荒废不在,大长绠的寿终明显不是“正寝”。可他安然而亡、遂心而去,是不是“正寝”,于人于己,又有何意义呢?谁也不会再过于认真了。不过,人们都说,大长绠是有福的。
春节前,回老家上坟,听说大长绠死了,属于寿终正寝。我便想,大长绠何德何能,竟然活了八十四岁,赶上了亚圣孟子,说“寿终”,那可真是“洪福齐天”了。还听说,大长绠从病发至心率衰竭、最终死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包括后事的料理,一直都是乡政府和敬老院一手操办的。当时也未通知其亲属,只是在火化后把骨灰转交给了他的侄儿,归葬到了老坟里。按照我们老家通常的说法,“正寝”是老式住宅的正房,叫做“堂屋”;一般人死后灵柩多安放于此。大长绠的老宅,“五保”后就归队里了,如今也另有其主,房屋早已荒废不在,大长绠的寿终明显不是“正寝”。可他安然而亡、遂心而去,是不是“正寝”,于人于己,又有何意义呢?谁也不会再过于认真了。不过,人们都说,大长绠是有福的。
大长绠,是我本家的一个“堂叔”。他的爷爷和我父亲的爷爷是亲兄弟。说是“叔”,其实,他比我父亲还大几个月。我父亲是农历十月生人,他是麦收之前。大长绠兄弟三人,老大叫做“收”,是“丰收”的“收”字;老二叫“茬”,也就是庄稼收割后剩余的部分。在我记事的时候,“收”老伯不到五十岁就被老天“收去”了,我根本没有什么印象;而“茬”二老伯整天弯着个腰,耳朵还有些背,人们都叫他“老茬子”。如果从老大“收”、老二“茬”来看,这老三该叫做“耕”,也就是“耕地”的“耕”才对。不过,在乡下农村,那时读书识字的人也不多,起名字只是图个叫做方便,只要有音也就够了,谁也不太在意具体的意思。“绠”是他的小名,在家他是“长”字辈的,按乡下的老规矩,大名也多是就地垒,所以就叫做“长绠”;由于“绠”有又长又粗的特点,人们多习惯于称他“大长绠”。
在我早年的印象中,大长绠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儿;紫红色脸膛,有一只眼凹陷,短短的头发又黑又亮;腰板挺直,看上去,很精神。最初,他的家就在中心老街的下坡处,紧靠路北,与“收”“茬”二位老伯的家并排。大长绠独自一人,整天默无声息地住在最东边。记得当时时,他住的是一间平房,坐北朝南。这间房不高,好像全部是用那种从地下刨出来的老式砖垒就的。房顶看不老清,只觉得蓬的有棍,上面厚厚地蒙着几层白色的塑料布。贴着房子,起半间小屋,是灶火。小屋比平房稍靠后,一边高一边低;靠房的一边高。这半间小屋好像也是用那种旧式砖砌的,只不过零碎砖多些,上面缮了些柴草。在柴草的上面,好像还摆八卦阵似的压着几块半截砖,砖与砖的空隙中生长着一些绿色的生命。在小屋的门口,时常放有一只黑色的铁皮桶,桶底和腰箍间锈迹斑斑。桶里有水,是极为清澈的那种。水里有一只瓢,歪斜地半掩半躺着。
大长绠的整个宅子没有围墙,南边邻街是几棵较大的桐树,春天开那种紫色的喇叭花。花落时,院里满地,时常有花公鸡和黎色母鸡在哪里自由自在地啄食。宅子的东南角,是一个用碎砖累的简易厕所。厕所门朝里,无影壁墙,敞开着。对着厕所,北面有一颗碗口粗的楝树。楝树长得很旺,树皮不是很涩,开一种星状的或白或紫的小花。楝树结实很多,一串一串的,像大个的樱桃。楝实成熟后,有麻雀或长尾巴马噶子在枝头蹦来蹦去,时常还可以听到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那时我们小朋友经常在楝树下玩,滚落的楝枣有时就砸在我们的头上,也感觉不到疼。每当这时,大家只是相视一笑而已。
大长绠是属于那种“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的人。他吃饭很靠实,一般比普通人家都早。在我们下学玩耍的时候,他已经开饭了。大长绠吃饭通常就坐在那间小屋的门前。有时见我们笑,他也笑。如果遇到好吃的,闻着香,有狡猾的孩子就会冲他说:“三叔,做的啥?真香!”他便会眯着眼,细声细语地说:“怎么,想吃?来吧,油炸花生米!”我们都围了上去。只听他说:“先洗洗手,每人三粒。”我们照办了,洗手就用铁皮桶里的那只瓢舀些清水。我们一个个地冲洗过,在各自身上一擦,就立等着三叔分香豆吃了。大长绠也很守信用,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可等我们各自分得香豆跑开时,他不大的那只碗里的豆豆也就所剩无几了。
模糊中,我还记得,白山结婚的时候,是大长绠赶的车。白山是大长绠大哥“收”老伯的大儿子,也就是大长绠的亲侄子。自我记事起,大长绠好像就没有老婆,只是一个人度日。但看得出来,他是很喜欢孩子的。听人说,“收”老伯身体不好,白山妈死得早,白山兄弟几乎就是大长绠接济大的。在大长绠看来,白山虽然是侄子,但他一直当儿子对待。白山结婚,他跑前跑后,借东借西,两眼熬得通红。我只记得白山结婚那天,快接近正午了,说是新媳妇到了,很多人都在跑,我也跟着跑。先见抬盒子、抬嫁妆的进院了,一个个穿戴一新,打扮得像过年似的。每人胸前的扣鼻上还都挽着一个红布条,一幅满脸笑容、意气风发的样子。
街两旁站满了人。我挤出人群,远远地看到从老街的尽头,一辆四轮木车缓缓地驶来。“近了!近了!”我似乎听到了有人吆喝。前面是几头牛,全是棕黄色的那种,在太阳的照耀下,远看好像是金色的绸缎。由于是上坡,一群牛都低头弓背地使劲拉着。隐隐约约地听到大车木轮的滚动声了,只见大长绠稳稳地站在车头,左右开弓,“唰”“唰”“唰”炸了几个响鞭,然后从木车上跳了下来,招呼着看热闹的男男女女。那架势像在导演一场古代的阵法,大长绠就是亲临战阵的将军。不过早有人摸过去,用事先准备好的烟灰给他膏了个花脸,看来这一回大长绠要唱包青天了。
听大人们说,大长绠先前也曾娶过老婆。大长绠命里苦,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了,只有他弟兄仨相依为命。那时候家里穷,没有父母操心,说媒的是很难找上门的。由于不够吃,作为老小的大长绠,有时还得去找活干或给人帮忙混碗饭吃。有一次天下大雨,大长绠外出一天没找到活,回来的路上又饥又饿,他病倒在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前。那家主人是个好心人,在熬粥救醒了大长绠后,看他是个实在人,有心可怜他,便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他。那女人姓孟,名字叫“兰英”,我父母都见过,说人长得又瘦又小,不过说话挺和蔼的。
后来发黄水,大长绠和孟兰英小两口都到南方逃荒去了。据说孟兰英身体本身就有些娇薄,逃荒的途中饥一顿饱一顿的,再加上她可怜大长绠,有时看大长绠吃不饱,她就把自己讨得的一点点饭食又都让给了大长绠。大长绠在南方颠沛流离,一定吃了不少苦。不过,这其间谁也不知道,大长绠也不说,至于遭了多少灾、受了多少难,谁也说不清。等他回来的时候,孟兰英终于没有熬住,连饥带病死在了南方,大长绠的一只眼也因病带痛无钱医治而瞎了。我们见他的时候,大长绠的那只眼似乎还管用,但远远看去,已经显得凹陷。据说,他的那只眼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大长绠和孟兰英结婚也有几年,但一直没有生育,大长绠没有孩子。孟兰英死后,大长绠也没有再找,一直是一个人过活。要说大长绠和孟兰英的那段感情经历是悲凉的、凄婉的,可在我还是一个光着肚子满地跑的小孩子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其间有着什么故事,甚至可以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啥狗屁都不懂。只是觉得好玩,喊着顺溜,远远见到大长绠,我便随着一群半大的孩子,一边跑着跳着,一边喊“大长绠,孟兰英”。有时看大长绠不吭声,喊的声调也越发高了起来。
每当这时,大长绠总是憋红着脸,老远脱下一只破鞋,一边骂:“小屁孩,爬一边去!”一边“咯噔”(一只腿快速地跳)着追赶。很多时候,看我们跑远了,他也就放下破鞋,骂骂咧咧地望着我们。有时候,一些孩子自以为大长绠撵不上,见他放下了鞋子,回头带有挑衅意味的又喊上了。这下好像逼得大长绠没有了退路,他便穿上鞋真的撵起来,结果总要抓住一两个跑得稍慢的。
记得当时我也被抓过。大长绠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在我屁股稍上光脊背稍下的凹处,打一个“响凹(wa)物”,并质问道:“大长绠是你喊得吗?你知道孟兰英是谁吗?”紧接着又绕上一句:“下次还喊不喊了?”说实话,我们当时都一脸的迷惘,这大长绠不是我们喊的,又是谁喊的呢?“孟兰英”这三字,我们还都以为是“梦兰英”呢?她到底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只是听到他说“下次还喊不喊了”,这次没跑掉,就说这次吧,谁还哪管下次呢?于是就学乖了,向他讨饶。每当这时,大长绠绛红的脸一下子就会变得缓和了。
有些时候,正好遇上孩子的家长,大长绠还会像个孩子似的向家长们抱屈:“你说这些孩子也真是的,我又没招谁惹谁,他喊我干嘛!”大人们便会说“欠揍!”有时,一些家长忍不住气,还动了真格,脱下破鞋真的打起自家的孩子来。这时候,破鞋打在身上,那力度和痛感都比大长绠的要重得多。每逢这个时候,大长绠便会拦住,急忙说:“都是些孩子,怎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别打了,别打了!”说着拉着,又给我们这些“犯了错”的孩子讲情。这个时候,他就好像是我们的另一位家长,也就是一直护着我们的那慈爱的母亲。
大约在我上学的第二年的秋天,大长绠搬了家。说是搬家,其实也就是由路北换到路南。大长绠家门前的这条路是本村的正街,由于当时雨水多,每逢雷雨季节,大街就像是一条河;加之街两旁的几个大坑,雨水汇集,一片汪洋。滔滔的水流顺着大街滚滚东去,注入了村东的大池塘。正对着大长绠和“茬”老伯家分界朝南的是一条巷子,也就是说,大长绠原来住处的前方是一个“丁”字路口。大街在这个路口处猛地下跌,形成了一个急下坡。雨水泄过,沟沟壑壑的,冲刷得很厉害。这或许正是大长绠搬家的一个原因。
大长绠搬到的这处宅子,原本是二良家的。二良跟我父亲和大长绠都是关系一样的堂兄弟。我曾祖弟兄五人,大长绠的爷爷是老大,二良的爷爷是老三,我父亲的爷爷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老五。二良的父亲死的早,二良和他的哥哥大良弟兄俩都是当年被抓壮丁抓走的,历经磨难,才走入了革命的队伍的,当上了共产党的战士。后来一个在陕西西安某机械厂安了家,一个在青海西宁干公安。他老家里没有什么人,当时的宅子一片荒芜。后来村东队在上面盖了两间车屋,车就是那种走动起来“呼隆隆”响的四轮木车,我们当时都叫它“太平车”。“太平车”不用了之后,那两间房除了木车单独在里面享受着“太平”之外,一直闲着。在一场大雷雨过后,大长绠就搬进了这车屋里。
大长绠入住以后,看得出他还是很爱干净的。他找人一起掀翻了太平车,将其挪到靠东山墙边,侧立着。大长绠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木板床靠后墙支着,锅碗瓢勺都摆放在了外间。两间房比着他那间炮楼似的旧平房,空间明显增加了许多。空闲的时候,他还找报纸把靠床和放炊具的墙壁贴了贴。尽管下雨屋内有些潮,大长绠却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料理好了这一切,他还在院子里栽了一些树,当然主要是桐树和榆树。桐树长得快好卖钱,榆树长的榆钱可以吃。至今我还记得,在房屋的东窗前,大长绠还植了一棵枣树。或许是地壮,或许是没有大树的遮罩,枣树长得很快,不几年便摇动了风,结了很多又大又红的枣子。每逢枣子成熟的时候,我和小朋友去打,他也不阻拦,有时还笑着帮我们摘,那笑容像秋后的阳光一样灿烂。
在大长绠新居的西面,也就是“收”“茬”二位老伯家隔街相对的地方,是一片空地,这片空地是新建村庄搬走户留下的。我们村是一个老庄子,村里像这样的空地在当时就有很多。在这块空地的东北角,也就是“丁”字路口的西南角,有一口老井。井口方不方圆不圆的,井壁的凹凸处长着青苔和杂草。井并不是很深,但水很清澈。井的台面是用青砖砌成的八卦状的图案,周围四个角分别栽有泡桐。泡桐树有碗口粗,个个枝繁叶茂的。靠东南角的那棵桐树下,放着一条红色的旧石槽。麦忙季节,人们在上面磨镰刀;平时,妇女们用它洗衣服。总之,石槽里经常有水。有时,行路人热了,也在这里洗把脸。当然,暑热天气,也有端着饭碗围着老井吃饭的,那些人就常常坐在石槽上。这石槽里的水,大家都知道是大长绠用他那只黑色的铁皮桶从井里汲水倒进里面的,有人还见他有事无事经常把石槽里的水换一换。
大长绠虽然独自一人,可经常有说书的、卖唱的、补漏锅的、修伞的等艺人在他这里歇脚。大长绠从不吝啬,他总是拿出自己最好吃的。可那年月,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最好吃的,反正是他有什么就拿出什么,让这些艺人们吃。当然,那些艺人们也都说大长绠的好。大长绠听了,常常是笑笑说:“出门在外,人谁没有个难处,有了难处帮个忙,那不是应该的吗?再说,想当年,发黄水,咱不也……”有时说着说着,他就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了。人们都以为他又在想他的那个“孟兰英”了。
岁月如烟花,美丽灿烂的总是空中那短暂的一闪,落下的却是黑色的灰烬。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黑夜来得早,也来得快。当人们还在吃晚饭的时候,大长绠的院子里就传来了“咚咚咚”“咚咚咚”的鞭鼓声。这声音是乡村孩子都非常熟悉的声音,这是说大鼓书的。一听到这声音,我没等吃完饭便跑了出去。记得当天晚上说书的是一位瞎子,说的内容是《三侠五义》,情节曲折生动。它主要讲的是包拯手下的南侠展昭因为擒盗有功,被大宋皇帝封为“御猫”,一下子惹怒了锦毛鼠白玉堂,他要和展昭一比高低,于是在开封府闹出了惊天大案。那晚书说到三更半夜才结束,瞎子艺人又饥又饿,大长绠便端上了自己晚上刚蒸的新鲜红薯,老艺人一连吃了好几块,虽然觉得哪儿有些不对劲,但也没有太在意,吃过他也就睡了。
这么长的文字需要慢慢欣赏,先来留个脚印。问候老师,写文辛苦了,感谢赐稿平凡。
您的文字印象深刻,写作功底深厚不凡,关键是您有很好的看待事物正确的观点。烈日炎夏,祝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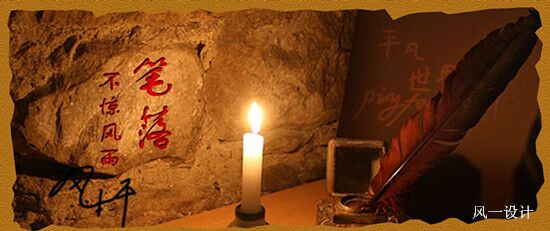
我们的公众微信号:Pingfanshijieshetuan,您可以搜索到以后点击“查看历史消息”就能看到您的美文了,另外您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号,以便以后更加方便地欣赏到您和朋友们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