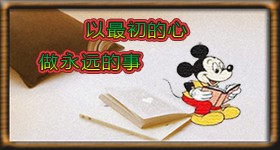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失常者(散文)
【流年】失常者(散文)
![]() 夜幕低垂,环山四合,将村庄掬进灰暗。多年前,我尚不知深夜里的人间会有鬼魅精灵觊觎,稚嫩的脑袋里装满了许多奇思妙想,十分喜欢每一个稠密的夜色。天河,挂在高处的街市,飘荡着世间鲜见的美食气息,许多人打着灯笼行走,晶亮的光影把影子漫过鹊桥。或许,只有栖息在大树上的鸟雀能听得见来自天空的纷沓脚步,便扑楞几下翅膀。草丛里,半山腰,几只田鼠和狐狸悄然蹿过,兔子们四散而去。
夜幕低垂,环山四合,将村庄掬进灰暗。多年前,我尚不知深夜里的人间会有鬼魅精灵觊觎,稚嫩的脑袋里装满了许多奇思妙想,十分喜欢每一个稠密的夜色。天河,挂在高处的街市,飘荡着世间鲜见的美食气息,许多人打着灯笼行走,晶亮的光影把影子漫过鹊桥。或许,只有栖息在大树上的鸟雀能听得见来自天空的纷沓脚步,便扑楞几下翅膀。草丛里,半山腰,几只田鼠和狐狸悄然蹿过,兔子们四散而去。
世事的纷繁和阴晦,不断给我们讲述着的如何处世的人生课。成年之后,眼睛和大脑便装下了许许多多世俗成见。如今,村庄夜晚的美好已然成为回忆,渐次燃亮的灯光,如散布的院落一样零乱。而灯光正好使灯光之外更显漆黑,团团浓墨涂抹了一般。星辰的力量不能抵达黑的内部,村庄陷入神秘之境。此时,我相信许多院落已经反锁了大门。
那天送走前来聊天的最后一拨童年玩伴,已经是深夜。其实,从主屋里走出来到合上院门,我的脑袋里装满了我们刚才聊过的诡异故事。他们说,村庄不比从前安详。近三十年前,年轻人丢下老人和娃娃,蜂一般外出打工后,村庄便失去了原有的平静。一些挣上钱的人回家修建了新房子,令人们刮目相看;可有的人钱没有挣上,却意外失去了性命。这些灵魂从远处运了回来,埋葬在老家的土地里,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不太甘心和不安心于现状,在村庄里弄出许多骇人的动静。他们说,不得不相信啊,这些离开人世者,经常出没在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偷窥着他们生前十分在意的人。
真的是这样吗?我的内心充满疑惑。
但是,如同寒风呼啸着袭来,这些故事在黑暗包围的夜里,让人周身发冷发麻。我赶紧关上大门,朝屋里小步跑去。我相信院落里是安全的,那高高的土墙将一个大空间分割成小空间,如果进了屋,屋墙又将小空间隔成更狭窄的空间,人好像躲进壳里似的。我只是不经意地抬了下头,星光下,千真万确,看见东边的院墙外一只黑黝黝的影子迅速闪过。
我没敢声张,跳进了屋里。兄长肯定看见我脸色不对,说,肯定又是土生。
不是鬼怪精灵?我深深地舒了口长气。顺着兄长的话想下去,土生在院墙外偷窥应该已经不止一次了吧。
我的记忆库中,立即翻腾出了许多与他有关的事情。有些尽管是道听途说,但我相信乡亲们不会无故编排故事撒谎或者恶意中伤邻里。
与饥馑年代出生的同龄人相比,土生自小看上去身体壮实。到他快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一副成熟并且有力气的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村庄开始泛起打工热潮时,土生应该算是较早出门闯荡者之一。那应该是初夏,六盘山下的小麦才灌浆时,八百里秦川的小麦已经进入收割时节。他最初跟着他的兄长,和村庄的其他大人一道去赶“麦场”。割麦是一件技术含量不高的体力活,能干者据说每天可以收割两三亩小麦。但土生不行,尽管看上去似乎是个好劳力,但收割小麦还是体力不支,不一会儿就腰酸腿疼,只能帮其他人打下手。主人可不喜欢这样的麦客,他需要能吃饭能干活的,像土生能吃不能干的,很快被打发了回去。
有了第一次出门的经历,土生的勇气和胆量大了起来。第二年春种结束后,他的大哥刚出门打工,他便相约了与他年龄相仿的大宏,趁天擦黑时出门而去。说的是去内蒙古打工,但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何方。
村庄习惯了一个或者几个人的失联,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习惯了静寂。那时,土生的父亲年事已高,老伴去世后,他的背又驼了许多,儿子们出门后,他既要料理家务,又要照顾自己,他的头低下去了许多,以至于看不清他额头上新刻上去的皱纹。有人会问他:“饭吃了?”他说:“嗯。”“娃娃没有来信?”“没有。大概快回来了。”这一问一答间,让我想起他家门前的一道土坡上慢慢晃动的黑色瓜瓣帽子---老人常年帽子不离头顶,走路和不走路时,都不由自主地摇动着头颅。
没有谁会像电影电视剧里那样,站在村头大喊几声“我回来了!”哪怕是衣锦还乡。土生和大宏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们不说,但逃不脱路人的眼睛。这是第二年深秋,粮食上场,颗粒归仓,大地因空旷而清爽了许多。秋风开始瑟瑟,树叶借机飘落。村北的山坡上,有片不大的土地略显平整,那是人们取土形成的洼地。清晨,有人挑粪上山经过这里时,听见里面偶有人声传出。据说,山坡上经常会有白衣白袍的神仙出没,那人便悄无声息地靠近,想看个究竟。他没有看到神仙,却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他们,就是土生和大宏。那人没有声张,转身离开时想,这两个年轻人在练武术罢。
又是土生家门前的土坡上,土生的父亲晃动着黑色的帽子缓慢前行。有人好奇而关切地问:“娃娃学武术了?”土生的父亲好像没有听见,朝院门走去。他这个年龄,耳朵失听显得十分正常,并且比较普遍。而这似乎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一天傍晚,一位老者去找土生的父亲聊天,基本探明了情况。他进门后,见土生的父亲立在土生居住的房间门前,好像在偷窥,好像在偷听。见有人进来,赶紧摇摇手,然后告诉他,好多天里,土生和大宏钻在黑乎乎的屋子里,有时连饭也不吃,说是专心练习什么功法。
土生与大宏诡异的行动迅速传进了留守在村庄里的人们的耳朵。
忙于家务和土地的人们,虽然对他俩议论不断,可谁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他们的异常举动呢?
又是一个春天。当人们播种结束,年轻人又出门打工时,土生和大宏十分例外地没有去。他们从昏暗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先是土生的父亲,然后是留守在村庄的人们,发现他们二位见人后眼神漂移,好像面前舞动着莫名的精灵,充满恐怖和慌乱。而又说话时语无伦次,时笑时呆。开始,人们觉得他们俩中邪了。
据说,以前安静老实的他们,竟然出人意料地使用暴力。暴力的对象当然是与他们最亲近的家人。我似乎不难想像得到他们目光的恶毒和下手的凶狠。此后,当他们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村庄的每一块地方时,那种异常的神情比传说中的鬼怪精灵更可怕。孩子们赶紧跑回家,关闭了院门,孩子的家长抑或监护人把警惕地目光投向院门。“绕着走”,一度成为村庄的又一习惯。
时光一晃,就是数十年。
沿我家门前的土路朝南走去,有一排相连的院落。大宏家就夹居其中。
大宏自小听话,胆小,家境也好,虽然想不起在饥寒年代他与我有过多少交往,但记忆中的他似乎与村庄所有同龄者关系不错。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家,在县城一工厂打工时,偶尔碰到过一会。那时的西关贸易市场还没有整体规划,各类、各种商品互相抢占着地盘,一副繁荣昌盛的万千气象。我去市场买上木胶和铁钉,一转眼看见了大宏,不,确切的说是他先看到了我。本来都要握一下手的,但我手里提着东西,只好作罢。我们站在一排等待出售的高低柜前交谈,他告诉我的,正是我想知道的。他说他在一家浙江人开办的木器厂做小工,学习家具油漆技术。他指了一下旁边的家具,我便知道那都是他油漆的,条纹清晰,显然已经不错。我那时在学习往玻璃上画画,很有一种同行的感觉。记得我说,不错,至少这是一门正经的手艺,将来可以养家糊口。
可是,我实在没有弄明白,更没有理清楚他为什么没有继续把手艺学下去,学到手。
与大宏相比,我则更熟悉土生。上小学时,尽管土生家住在我家的院落上方,相距不远这,但为了不迟到,土生有一段时间住在有闹钟的我家,与我和兄长挤在一盘土炕上,对此我们毫无怨言。原由是我的母亲和他的母亲因娘家关系,沾有一点亲戚。几乎大多个傍晚,如果天气晴朗,土生的母亲总会站在我家后院墙外,喊我的母亲出来聊天。聊天的内容十分单调枯燥,无非是做布鞋、缝衣服等话题,但很少聊到土生与上学。可惜,这位记忆中脸色苍白的老者在我离开老家不久,就驾鹤西归。
想必,土生应该对我家的院子也是十分熟悉的。
恰好,父亲去世那一年,土生出入于我家,前来帮忙。而没有帮忙的大宏,我们在院门外的路上鬼使神差地相遇。
我一直低着头。我到村北的坟地里给打坟的人送完饭下来,快到我空门前时,突然有人挡住了去路。他好像刚从麦草堆里钻出来,头发长且散乱,其中插着着几根草节。眼窝深陷了下去,顺着眉毛看过去,耳朵背上夹着一支香烟。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他是大宏,还真一下子认不出来。听说,他练那个功走火入魔后,每天不是嘻笑哀哭,就是打砸大闹,起初家里请了阴阳先生来为他“整治”,但收效不大,最后送到某精神病院治疗,才有了现在这个虽然痴傻却不太打闹的状态。他在学习油漆手艺时成了家,养有一女,自他变疯变傻后,妻子无法忍受眼下生活,便离他而去。
“他经常吃药,如果不受大的刺激,病情就算平稳”。有人对我说。
看到他这样子,我心里一疼。
大宏显然不认识我了,朝我说:“烟!”
我叫着他的名字,赶紧给他掏烟。他好奇地看着我说话的嘴,伸手拿我递过去的香烟——他的手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洗过了,尤其是指甲,长得跟粘上去一截似的。而没有等我问完话,他拿了香烟后,转身扬长而去。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回头看看他跌跌撞撞而去的背影。
可是,土生的情况与大宏比较却是大不同。前来帮忙的土生一直守着茶炉,保证开水供应,这是总管分配给他的任务。茶炉就摆在我们小时曾经居住过的屋门前,如果来客少时,他有足够的时间搁上茶杯粗细的铁罐铁炖茶喝。茶叶下的很多,茶水稠黑,可他不嫌味苦,一杯接一杯地喝。不想喝了,就去屋里坐一会儿,听见有人喊他时,赶紧又走了出来,正常人一般。更令我不解的是,他的父亲三年前去世,他大哥又招亲远方,他一个人居住在一坐大院里,竟然会把一身衣服清洗的干净如新,他怎么会是一个神经失常的病人呢?
他朝我笑,牙齿因吸烟喝茶太久而显得发黑。我对他说:“你胖了。”和大宏相比,土生的脸庞又白又圆,好像发酵恰到好处的大馒头。
土生却说:“唉,不是胖了。是经常吃激素药物的结果。”是的,他以前也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回来后,和大宏一样服用着神经抑制类药物。
借着话题机会,我又问他平时怎么解决吃饭问题,他有些沮丧地说,自己做,还能怎样。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不得不问:“你身体不好,听说你没有种庄稼。这米面油从哪里来?”
他轻描淡写地说:“乡上取。”
我肯定缺少对这一环节或者政策的了解,所以没有听懂土生所回答的意思。好在有人用调侃的口气补充说,土生现在享福哩,按时领用低保金,和乡政府的脱产干部一样。如果钱花光而又没米没面了,乡上会免费送给他。
原来如此!我又问:“假如乡上不给你呢?”
“我是病人,他们不给怎行!”土生不高兴了,拧着脖子说。
我担心问的太多刺激了他,没有再问。仍然有人解释,不知什么人给土生出了主意,没钱花、没米面时去找乡上要。乡上如果不解决他的要求,他就哭闹,乃至跌倒在地,人事不醒。据说,此招十分管用,他闹腾了一次两次后,乡上都知道他是精神异常者,不愿意招惹是非麻烦和承担责任,最后不仅解决了他提出的要求,而且还会送上香烟茶叶好言打发他回家。我不敢面对乡亲说出“一种病衍生出另一种病”之类的话,只是觉得不止土生,其他人也病了一般。
而此后几天,烧水炖茶的换了人。听说,土生去乡上了。
一次回家的班车上,听见几个妇女在议论,现在好多村庄里有人在练习那个功法。言谈里,我已经知道她们中也有人练习此功,并且,练习者在用神奇的事例动员未练习者加入她们的行列。由此我了解到,练习此功法者,冥冥一念间,想要什么就可得到什么,过上柴米油盐不缺的生活。但必须达到一定境界……所谓“一定境界”,并无时限,全在于坚持修行。可见,不劳而获也是需要巨大付出的。
真有不劳而获的好事吗?这个认识的曼延,如同癌症细胞般致命。
假如我愿意把以前的村庄比作阳光普照,此时,村庄已是布满阴霾,那是一种堵,堵的人心慌意乱,好像许多村庄的美好被遮掩,找不到突围的出口。村庄里练此功的不止土生和大宏,人群的分布中,有老人,有青年,有孩子,甚至,有的是全家参与。早晨,中午,晚上,只要有时间,他们会紧闭大门,在各自的家中虔诚跪地,口中念念有词,祈求虚无缥缈的神灵赐予更多的财富以及长寿健康。而赖于我们生存的一些土地,也就因此而荒废。
所有的路通向另一个村庄,既方便了人们和货物出行,也为他们互相走访和消息的传播提供途径。一位中年妇女病倒了,手机发出信息后,她的许多同伴知道了这个信息。人们看到,许多陌生人进入她那个村庄,聚集在她家的院子里,跪倒了一大片。她们默默地念叨着什么,从早上一直到天黑。而且,不时有人加入到这个行列。听说,这位中年妇女应该算是他们的小头目,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祷告。听说,只有通过这个仪式,中年妇女完全不用送到医院打针吃药,会自动康复。他们对他们消灾祛难的方法充满了无比的自信。
不幸的是,几天过后,中年妇女并没有如他们所愿。据说,她因耽误治疗而失去了性命。
这位中年妇女的院落已经破败,家具也十分简陋。她执著于练功,他的丈夫的孩子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一气搬走。那么,她的后事谁来承办呢?。据说,闻讯赶来的社长知道此事的过程后,执意要向公安机关报案,中年妇女的那些同伙知道后,立即作鸟兽散。而她的娘家人也不愿意把事情闹复杂,加上有人拦劝社长息事宁人,最后,案是没有报成,中年妇女的后事却留给了族人和村庄。
我无法证实这个事件的真实性,我只是想说事情的严重性和危害程度。可惜的是,执迷的人们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去年父亲三年祭日时,我再次与村庄亲密接触。感觉中,村庄突然多了些明朗和安详。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来自于对村庄的情感效应,应该只是一种对村庄环境的体验罢。
照例,家里来了不少帮忙办理祭日活动的人,他们,每张面孔我熟悉并且能叫得上姓名。我穿梭于大家之间打着招呼时,几位比我小许多的年轻人趁着端茶倒水的间隙,互相开着玩笑。他们对一位叫小民的说:“今天累不累?”另一位对小民说,“小民肯定不累,人家有神功罩着。”“你给咱们念叨几句,来包中华抽抽”。
小民竟然不生气,朝他们挥挥手,说:“丢人现眼的事情,再不提了。”
原来,小民也是此功的练习者。听他们讲,半个月前,派出所在取缔和打击非法及反动邪教门行动中,就像早已对情况了如指掌似的,光本村一下子带走了十一个男女。令人欣慰的是,几天后,他们全部回家,再次拿起了农具,和土地、牲畜再度亲近了起来。山野上忙碌的身影,让野兔和田鼠一时惊诧,片刻后马上安静了下来。它们也觉得,这一群人是原来它们熟悉的人群,现在的村庄才更像村庄。
我依然关心与我同龄的土生。他们说,土生是派出所这次行动中唯一没有被带走的。“土生早就不练功法了,他属于精神失常者。”
我不由得环视了一下所有出进于我家的人们。是的,怎么没有看见他的身影?如果他在,一定在那间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屋前烧水炖茶。
有人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一大早还看见他在他家门前的土坡上晃荡呢。可能,他去乡上了吧。
这是农历三月的天气,温暖中还有些微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