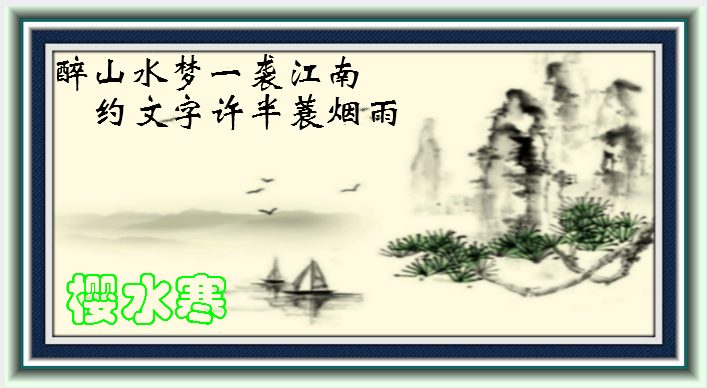【江南少年】厂矿是回不去的记忆(散文)
【江南少年】厂矿是回不去的记忆(散文)
沾益自古就是入滇的咽喉,1938年美军建沾益机场,此地成为驼峰航线的重要物资转运站。
沾益总站成立于60年代初期,前身应该是组建在50年代的一支车队,不过随着老职工逐渐离开人世,这段历史已经无从寻找了。
我很小的时候,旁听老工人聊光荣史,说当时建厂矿不允许占用农田,政府给了一个山包。靠炸平山包,又靠他们汽车拉,小车推,用一车车土填平所在地的低谷,才弄出一整片的大平地。
直到80年代中期,沾益总站一直是滇东地区货物运输的总枢纽,底下两个大的分支是宣威和曲靖的两个车队,最主要的货运物资,是宣威的煤,还有滇中的黄磷矿。
改革开放前的沾益总站,是省属国企,人员最多时,连同家属,有三千多人。因为运输垄断,一度总站的创利能力非常强。
这里有自己的医院,有从幼儿园直到高中的子弟学校,有自己的小卖部,浴室,食堂,加油站。每天还有附近的农民担菜来卖,故总站的人不怎么需要到县城里,虽然县城也就隔着贵昆铁路线,直线距离不到300米。但总站自成一个独立的王国。
大家都互相认识知根知底,吵架的时候,可以扒开对方三世的底细。我的高中同学几乎都是从幼儿园就开始认识的。
大家的话题总是比较单一,比如早先,还得去县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逢到上新电影,县电影院里都是平时厂区熟悉的面孔,几乎就是总站包场。大家彼此大声喧哗着打招呼,男职工们进进出出买瓜子买汽水,还忙着上厕所,女职工互相拉着家常,毫不理会自家的孩子上蹿下跳奔驰在银幕前的台子上。要是哪部新上的片子谁错过了,谁就直接被孤立在大家的话语圈外。
小卖部到了什么新鲜的食品,全厂的人都伙同起来买,然后将这些新鲜感融入大家的谈资,如同电影的话题一样,要是有谁有意无意地错过,谁就变成没有集体语境的孤立者。因此我觉得总站的人只敢从众,缺乏成为个体的勇气。
邻居的鸡零狗碎,都是大家茶余饭后的共同谈资。各宿舍门口,总围坐着几个悠闲的家属。每次走过她们面前,就可以听见说长道短议论自己的声音。走路姿势,衣着打扮直到父母弟兄性格脾气,都会被她们当着你的背影扒个遍。要是被议论者有什么背景或者优势,大家就边议论,边投之以嫉妒的目光,还带着点希望他倒霉的阴暗。
总站非常保守封闭,甚至于口音也不同于县上,县上的人都说“黑桥话”。总站的人说话的发音方式,感觉总是在努力学习昆明腔,大家都公开崇拜省城昆明,一些昆明有亲戚的家庭,暑假里带了自己的孩子去住几天,回来后,说话的底气都明显足过其他人。要是在动物园翠湖逛过,在昆明百货大楼买过东西,此家庭的每个成员就可以直接藐视厂里其他群众了。
总站的腔调里面除了大量本地土话和部分硬憋成的昆明腔,又混杂了个别外地的词汇,尤其是上海词语,究其原因,是总站混杂了本地人,昆明人,文山人,大理人,楚雄人,甚至四川人,山东人,上海人。上海人包含着少量第一代职工,他们是为援建来的技工,后来招进来一些知识青年,虽只有二十多人,但凭借他们亲戚寄过来的,大家都没有见过的奶糖,饼干,泡泡糖,和一些非常漂亮市面上见不到的头巾,发带,稳当当成了一个心理优势很强的小团体。这批上海人努力学着本地方言和我们沟通,但他们聚在一起时,又都只说自己的方言,骂人的时候,也用自己的方言,这些骂人的上海方言被本地人学了去,马上又变成总站的时髦话。
小时候遇到委屈,家长总爱问:“那个人说什么话?”小孩如果说:“黑桥话”,家长就会说:“那还知道是谁家的?”。意思是,说话腔调要是总站腔,总还是找得到说理的地方。
职工宿舍按数字划分,每个宿舍的人际关系各自又成体系,孩子们最护着自己宿舍的人,冬天打雪仗,大孩子说:“走,一宿舍的都去打三宿舍。”我们会饭都不吃,操起搪瓷口杯就去舀雪捏雪球。
总站最正式的全民社交场所,是总站篮球场。对于总站的光荣变迁史,大概也只有篮球场最能说清楚了。
篮球场四面砖墙围好,正东面高出很多,中间部分像黑板似地抹平,用厚厚的白漆刷好,恰好是一个电影幕布大小。正西面是一排两层高的筒子楼,最早的医务室就建在这里。
球场是平整的水泥地,用黄色油漆界线出两块标准篮球场,架着四个篮球架。
遇到重要的活动,墙东面会挂出布标,其余时候空着,放电影的时候,会悬挂出白幕布,死人的时候,会挂上逝者的黑白放大照片。
每年按时间排,正月初三,游园会在篮球场举办,每年活动内容都不一样,但总有小礼品发放。
正月十五看花灯,花灯每年总是那几盏,但不影响大家挤成一堆的热闹劲。
儿童节,幼儿园和小学在篮球场办表演,我父母是第二代进总站的职工,父亲因为读书分配,母亲因为和父亲的婚姻关系进厂,因此人际关系从零开始。我幼儿园眼巴巴看着第一代职工的孙辈上去表演,而自己从来都选不上去。
夏天周末的晚上,青工们会组织交谊舞会。大家都很羞涩,音乐开始时,蠢蠢欲动的积极分子总怂恿同伴先跳,而同伴总会推搡回避,大家拉拉扯扯地笑闹着,连放两曲没人跳舞,团委书记就出面说:“现在由我们团员首先做个表率,带头先跳,大家鼓掌欢迎。”最终在青年团员的带动下,起初害羞的立即就组队起舞。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青年真是有套路呀。
但那时没有人敢男女合跳,这仿佛是碰触不得的底线。偶尔会有县上的青年结对来参加舞会,却总是会被总站的孩子挤兑走,因此举办的交谊舞会也只是内部娱乐的项目。
国庆前后,全厂的大合唱在篮球场举办。东面的白墙上挂起丝绒幕布,上面别着庆祝国庆职工合唱大赛的字样,然后架起铁架子焊接的三层台子。这种三层的铁架子专门存放在总务办,每年合唱比赛都领出来用一下。比赛按车间和车队组队,大家清一色穿着蓝灰的劳保工作服,职工歌手不分男女,统一画着圆圆的腮红,一排排依次站上去。
秋天总分桔子,一卡车桔子停在球场上,大家早早就焦急地挤在卡车下,总务处的负责人每次都姗姗迟来,每次迟到都说“抱歉抱歉,具体名单才出来”,大家就宽容地笑:“没得事没得事,你们辛苦啦。”谁都不肯表现出着急的样子,以免显出自己的小家子气。报到名字的户主,欢天喜地用布兜装了桔子挤出去。
过年前分昭通苹果,我父母虽是双职工,但分到的苹果总量并不多,分回的苹果舍不得吃,我妈就挑出没有碰伤的优等品,用草纸一个个包好,放在米桶里,说等过年的时候才吃。不过我家的苹果总等不到过年,就被我和两个哥哥偷偷地偷出来吃掉了。妈妈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并不责打我们。
十一月以后,举办职工运动会,跳绳拔河缺不了,压轴重戏每年都是篮球赛。
平日里下午下班后,青工就自发组成篮球队比赛,男职工们围着喝彩,女职工照例是忙着回家烧饭洗衣服,一场球打完,刚好是晚饭时候,男职工都纷纷散回去咪口小酒。晚饭吃过,篮球场就成了小屁孩玩打仗游戏的地方和自行车骑练场,有自行车骑的人哪怕摔着了,也是脸上放光。
80年代早期,工会的女职工专门去省交通局学健身舞,回来后带着厂里的其他女职工跳,有时候跳扇子舞,有时候练健身球,一度还有人带着练气功。
天气好的某天,篮球场上会拉开白色的布,放露天电影,每个月总要放一场。我们这种年纪的小孩,最耐不住兴奋,下午四点就搬出家里的板凳去抢位置。小板凳排在那,吃个晚饭回来,就被别人挪了窝,找人家理论,免不了吵架打架,打输就得认怂,大人也并不认真来管。
东面白墙的底下,是总站最早停灵的地方。总站的职工宿舍太拥挤,没法停灵,人死后的最先中转处,就是开阔且公用的篮球场。哪家死了人,就到车队里借出蒙货用的绿色军用大帆布,搭个棚子。尸体在棚子的暗处,里面摇曳着蜡烛的光,棚子外是一盆的纸灰。小孩子这几天都吓得不敢上球场玩。出殡那天,就在篮球场开追悼会,单位领导主持,大家对悬挂在正东面的逝者头像三鞠躬,然后鞭炮哭声混成一片,逝者被放进黑漆棺材,由车间里抽出来的男职工挑起来送到总站的公用墓地埋掉。
球场接着又成了欢乐的社交场所。
春节前两个月,工会就开始组织排练春节的游行队,起初是下午三,四点钟,游行队成员在组织者的带动下,在篮球场排练队列和姿势,快到春节,游行的服装下来后,就一整天一整天的彩排。
女孩最喜欢大头宝宝和蚌壳精,大头宝宝憨态可掬,总是同手同脚走路,冷不丁会冲到人群中拽一下女孩的发辫,捏一下男孩的鼻头,惹得小屁孩们围着他们跑;蚌壳精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老头带着媳妇划船回家,不小心遇到蚌壳精,于是双方打架,总是蚌壳精败北。因为服装是古装戏服,水袖特别好看,蚌壳精每年都是厂花在扮演。
男孩子们喜欢踩高跷和狮子舞,喜欢踩高跷,是因为男孩子时刻都在想,用什么方法把踩高跷的人绊倒,然后看他们怎么爬起来;狮子是两个人扮演一只,统共一对,分走在游行队伍中间,在训狮人带领下,抢绣球,或者做花式穿插。后面那人弯身抱着前者的腰。据后面的人说,穿上戏服后,他完全看不见情况,运动全凭感觉前面的人的肌肉动作和观察地面的状况。锣鼓队鼓点急促的时候,狮子后面的人会将前面的人托举起来,真的像狮子立了起来,大家就纷纷鼓掌喝彩,压轴戏是狮子颤颤巍巍爬上垒起的办公桌,再立起来抢绣球,不穿戏服的时候倒还好,后面的人视线的范围广,但戏服穿上,爬桌子的时候,后面抱腰那个人因为看不清,常会失脚摔跤,这时候更会赢来大家的喝彩。
大人们说总站的舞龙队哪怕是整个县城所有的舞龙队也赶超不过。龙头很重,自然是体力最好的男人把着,左右上下挥舞。可怜耍龙尾的职工,每当龙因抢龙珠而做翻腾状时,龙尾要左右奔跑,有时候跑不动了,就被围观群众问是不是肾虚,龙尾职工呵呵傻笑不敢接腔,接着大家都哄笑开。
过年了,厂里专门派车带领游行队到县上,到曲靖和宣威表演。游行队伍回厂后,表演者自豪地表示,又是我们总站技压全县,然后从职工到小孩,无一不是展露出自豪又会心的微笑。
大年里,总站的游行队伍到哪里,都有一堆一堆的人追着看,从厂区领导到普通工人,大家一致重视这支春节游行的队伍,这支队伍代表了整个总站的脸面。那时滇中还没有哪个单位,甚至是县政府,有这么大的财力来置办这些表演用的行头。且总站的表演要故事有故事,要看点有看点,充分说明了总站不缺编导、表演人才,还能有组织有纪律地将这些要件整合起来。这就是一种综合优势。
到了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开始高速发展起来,因为运输垄断,总站也空前有钱。
篮球场对面隔了一条街,建起职工电影院,我们不用再走到县电影院看电影。要知道雨季的晚上,先穿过火车站的铁轨和碎石,再穿过县上泥泞的街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也不用看露天电影,不用占位置打架了,职工的文艺汇演也移到新电影院里举办。
在子弟学校后面,特别买了一块农田,建起配套完整,能做手术的职工医院,还特别准备了停尸房。已经实行火葬,出殡都由火葬场开车来接,追悼会也在火葬场开。谁家死了人,除要好的朋友知道,其他人不再直接通消息。
篮球场的功用单一起来,厂领导是一个篮球爱好者,特别将篮球场进行了改建,篮球场变成类似于罗马角斗场那种,有着由高到低环形看台围着的,只有一块标准比赛场地的时髦建筑。青工的交谊舞会还在篮球场举办,不同的是,大家已经开始接纳周边厂矿的青年男女来总站跳舞,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都主动起来,团委书记再不用出面说套话了。
再接着,建好整套闭路电视系统,晚饭后,大家都忙着收看工会组织播放的香港片,麻将开始如火如荼地时兴起来,社交场所已经逐渐变成麻将桌。青年人已经不再热衷晚饭后到篮球场聚一下,篮球场只成了女职工跳健身舞和小孩子撒野的地方。
随着改革的深入,私人开始被允许揽货跑运输,运费经历市场化的残酷竞争。有着过重社会包袱的运输总站,缺乏竞争能力,货源急速萎缩,亏损日益严重。车队开始承包制,自己揽货,修理费自付,汽油挂在各车的账上,年终统一结算。但承包出去的车总收不回承包费,油钱更无踪影。下属的修理厂也因为修理费用太高,揽不到生意,他们也开始承包,自负盈亏,工人自苦自食。有本事有想法的技工们纷纷走出总站,在国道上摆修理摊,大部分职工分流,或内退,或买断工龄。
沾益总站一会儿合并到宣威,归宣威管,一会儿合并到曲靖,归曲靖管。管理层都按照自己的能耐,到不同的地方扎根去了。到90年代初期,厂里已经没有多少在职职工,也再没有能力组织篮球赛,更不要提组建春节的游行队伍。
总站日益中空下去,剩下职工宿舍,被一些没有太多竞争力的职工子女继续住着,白天分散在曲靖或者县上忙着各自生计,晚上回家匆匆吃过晚饭,就混在麻将桌上赢点小钱贴补家用。
总站的篮球场,不再有人使用,它常年空置,只有春节回家的我们,三三两两,带领我们的子女在这块空地放烟花,这块空旷的地方放烟花最安全。
最终总站变成了退休工人聚集的养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