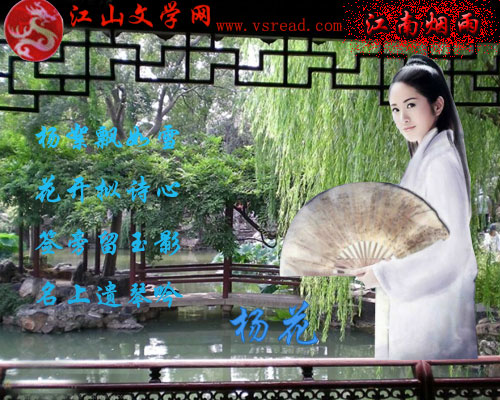【江南风骨】小苦(小说)
【江南风骨】小苦(小说)
一
小苦出生的时候,正赶上缺吃少穿的年代,母亲连肚子都填不饱,根本没有奶水喂养他,以至到后来,小苦只有一米六五的身高,这身高如放到女人身上还说得过去,换成男人就有点稍矮了,充其量只能算个中等个头。
小苦的大名叫什么?忘记了,因为不常用,所以没有印象。有人曾经叫过一次,当时听到感觉挺新奇、挺文雅,觉得小苦的形象与大名不相配,有些玄乎,觉得他不应该是这个名字或者说这个名字不应该属于他。后来再也没人叫过他的大名,就直呼他小苦,这样叫着顺口。队里分东西或工分公布榜也写着小苦二字。
小苦住在我家南院偏西一点,准确地说在我家西邻他大哥家的前头,与他大哥是前后邻居,仅一路之隔。小苦的家有三间草房,墙体的根基是砖,砖的上面就是土坯墙。三间房里打了一堵墙,隔开三分之一归小苦住,剩下的两间归他爷爷和母亲住。厨房就在东边,也是草房。
印象中的那位他爷爷已经八十多岁,满头白发,胡子和眉毛也全白了。两眼混浊,经常拄着一根木棍蹒跚行走。
小苦的父亲因为饥饿爬到树上捋榆钱儿,不小心从树上栽下来磕破了脑袋,人没拉到医院便气绝身亡了,剩下祖孙三代五口人,后来两个哥哥相继结婚便分开另住了。
小苦与我家算近枝,论起辈份来我得叫他叔叔,可我从来没叫过他,都直呼他的小名。小苦比我大七八岁,他那年龄段的人很少,想玩也没个伴,没事的时候,他就来我家玩。
有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吃饭,听见外面有咳嗽声,从走路的脚步声判断是小苦。我赶忙藏在门后,当时的门不是木板门,是父亲用荊条子编成的,留有好多缝隙,从里边能瞧见外面。小苦一看全家人都在吃饭,只不见我的身影便知道我藏在门后,便拿起煤铲子往里一戳,刚好戳在眼皮上,煤铲是父亲烧锅时刚用过的,还很热,烫得我哭叫起来,我捂住眼睛从门后出来。
父亲赶忙把饭碗放到案板上,拉住我到煤油灯跟前一看,只见我右上眼皮沾有煤灰,没伤到眼珠。父亲脾气也怪,只见他上去从小苦手中夺煤铲嘭地一下摔在地上,然后怒气冲冲地推了小苦一下,“滚蛋去!”
小苦窘得脸色发红,干笑道:“我是跟他玩哩!”
“有这样玩的吗?这是戳在眼皮上,要是戳在眼珠上咋办?一辈子不是完了!走,走,以后不要来俺家玩。”父亲把小苦推到门外边,回到屋里父亲还嘟囔道:“二球货,没轻没重的。”
二
小苦没上过学,恐怕连自已的名字都不认识。队里分东西还得请人帮他找名字,没人帮忙恐怕他趴在名字面前也不认识。每到月底,会计会把全队社员的出勤情况公布出来张贴在山墙上,小苦也像模像样地站在那里张望,谁知道他是不是看清楚了。
小苦的大哥一家分开另住后,他大嫂总是隔三差五地蒸几个白馍贴补他爷爷,有时他爷爷没吃完的白馍都被小苦给偷吃掉。
有一次,他趁家里没人偷偷地把大嫂家的堂屋的门槛摘掉,从下面钻进去,掀开锅盖从篦子上拿了两个白馍揣进衣兜,然后钻出来把门槛安好,躲进角落里偷偷地吃起来。
等到中午他大嫂回来发现锅里少了两个白馍,便怀疑小苦,可他大嫂问他时,他矢口否认。因为没有证据只是猜测,他大嫂还是对他不放心,每次给爷爷送白馍时,直看到他爷爷把白馍全咽进肚里才离开,让啃着黑窝头的小苦直流口水。
小苦虽然年轻,但他不算棒劳力,这跟他身体强弱有点关系。评工分时大伙只给他八分,这与妇女的工分平等。
每天的上工铃声敲响,小苦便披着衣裳,右手攥着铁锨,铁锨头朝前,木把在后朝上斜着,把他的衣裳的后摆挑起老高,像小燕翘起的尾巴。他走路拖拖踏踏,好像抬不起脚一样,整个鞋底早早就磨穿了,给人一种不麻利的感觉。看见路边有瓦片便弯腰捡起来,在铁锨头“哧啦哧啦”地磨起来。凡是不干活的时候,他都找东西磨擦自已的铁锨,把上面的粪土和铁锈刮掉,最后再用袄袖抹一下。他的铁锨总是明光锃亮,可以说是纤尘不染。小苦的铁锨一般是不借人的,除非关系特别好,他才不情愿地把铁锨借给你,一般的人你就别想。
小苦爱看电影,因为不识字,里面的故事情节看不懂,只看见里面打打杀杀的场面挺热闹。看过电影后也跟别人一起评论:那个坏蛋怎么样,或那个好人怎么样。
那时候,农村演场电影跟过年一样,大人和孩子都欢天喜地的。由于我村离公社较远,放映队的人员不愿意来。只要听说村里要放电影,小苦便自告奋勇去把电影机拉回来。
我村东头路口地势较低,每次雨天过后那里便存有积水,两边只剩下很窄的路。有一次,小苦用架子车拉着电影机和一些器材,在经过东头路口时把车子拉到墙上去,车子的一个轮子高一个轮子低,架子车上的东西全都翻到稀泥里。
两个跟在后面的放映员顿时慌了神,嗔怒小苦道:“路中央有水你也不能把车子拉上墻,这一下可好全弄湿了。”继而又觉得人家小苦是义务劳动,啥都不图,还想说些更难听的话便也咽回肚子里。
于是小苦和两个放映员便把东西从泥窝里捞出来。到大队后,用湿手巾把泥巴擦净。再让小苦找些柴禾燃起一堆大火,把幕布和其它物件烤干。
小孩子们看见电影机都好奇,很想看看或摸摸,小苦不愿意就打骂人家,他尽职尽责地守护着,不许别人碰一指头,好像那是他自家的东西。
桌子旁边竖一棍木棍,上边吊挂着一盏明晃晃的大灯泡,有许多昆虫围着灯光乱飞。小苦站在灯光下,他的影子拉的很长很长。
电影开始放映了,场地上黑暗下来,不知是哪个调皮鬼朝小苦后背上用土块砸了一下。小苦扭回头骂了一句:“谁家的龟孙砸老子哩!”
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影,回头惊异地看着他,有的偷偷地笑,有的埋怨小苦声音大影响了他看电影。
停了一会,不知是谁用根木棍朝小苦后背上捣了一下,小苦一回头只看见棍落在地上,却看不见人是谁,因为人人都在专心看电影。如此又被人捣了几棍后,气得小苦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站在那里了。
三
小苦的头发黑而密,最近又买瓶劣质头油洒在头上,用木梳把头发梳得溜光,时不时地用手抹一下头发。小苦也到该说媳妇的年龄了,也很注意自己的形象。
小苦也学会了抽烟,刚开始用纸卷碎烟叶,后来用大片的烟叶卷起来,用剪刀绞成细丝,然后再用纸卷起来,像模像样地如洋烟卷。
小苦家有一头山羊,是母亲买的,小苦喂养着。小山羊长大了,小苦把它卖了三十元,从集市上买回来一台黄河牌收音机,收音机外边罩了个皮革套,上边还有个背带。
收音机在当年是洋玩艺,很稀罕,全村也没几台。小苦的母亲也管不住他,就让他爷爷教训他,八十多岁的老爷爷走路都不安稳怎么能教训得了他,手拿拐杖要敲他,小苦就跟他爷爷转圈圈,他爷爷的拐杖怎么也敲不到他,气得他爷爷直瞪眼。其实他爷爷也不知道小苦犯了啥错,只听得小苦的母亲告状,他那时脑子己糊里糊涂的。
有了收音机,小苦便经常挎在肩上,去挑水时也挎着,他甩动着双手,收音机也随着悠晃着,收音机里播出的音乐也变成忽远忽近的颤音。
《卷席筒》是著名曲剧演员海连池的拿手戏,真是百听不厌,尤其是最后一段,曹张苍向哥哥哭诉那一段戏,让人像喝酒一样如痴如醉。“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起往外端……”再配上大弦子委婉的旋律,分外悦耳了动听了。
这出戏在收音机里经常播放。小苦的收音机便成了大家的宝贝。树荫下围坐了一圈人,收音机被放在中间凳子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没人言语,戏唱完了,人们不由地赞叹道:真过癮!
有一次,大家听得正入神,他的侄儿小军从旁边经过不小心碰倒了凳子,收音机也随着摔在了地上,正在唱戏的收音机嗄然而止。小苦赶忙捡起来,用袖子擦掉上面的土,再怎么摆弄收音机就是不出音。小苦拉住小军的手说:“摔坏了,你得赔我!”
旁边有人劝道:“傻小苦,那是你亲侄儿哩!也叫他赔呀。”
“谁也不行,这是我用一只羊换的!”小苦拿着收音机往小军手里一塞说:“拿回去叫你妈给我买一台新的!”
小军红着脸,撅着嘴一声不吭。当小苦把收音机再往他手里塞时竟哇地一声哭起来,而且哭声越来越大。哭叫声惊动得他大嫂慌里慌张跑出来,忙问咋回事?
小军哭哭啼啼地也说不清楚,旁边人把事情的经过叙说了一遍,他大嫂顿时大怒道:“想叫赔你,你等着吧,想瞎你的眼!”
“不赔还就是不中哩!这是我用一只羊换的!不赔我去牵你的羊!”小苦说。
“看看你那熊样儿,牵我的羊,哼!你去牵呀,不是小看你哩,摸摸我的羊就把鳖爪子给剁掉!”他大嫂越说越气。
“我的收音机刚买还没半月哩,就给我捣鼓坏。”小苦还不依不饶。
“活该!谁让你买哩?再说那只羊是咱妈喂养的,卖了钱也有我一份,卖三十块钱,兄弟三个一人十元,那你拿十块钱吧!”他大嫂伸出手掌向小苦要钱。
小苦一下子语塞了,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从地上捡起收音机,把背带往肩膀上一挎悻悻地走了……
四
麦子成熟后,用镰刀收割后再用车子拉进场里,全部堆起来打成麦垛。麦忙时节注重一个“抢”字,主要是怕刮风和连阴天,还要播种玉米和大豆,还要管理棉花和其它秋庄稼。
麦收过后,男劳力主要在场里干活,女劳力全部去地里劳作。每当这时候,凡是能干活的人都到麦场里帮忙,包括老师和学生。我们一帮子“小不点”也放下书包去生产队参加劳动。
清晨,太阳刚一露头,社员们便来到麦场里拿起大扫帚,把场地里的浮土和树叶打扫一遍。麦场很大,足有十亩多地,十多个人打扫一遍也得一个多小时,还要扫成堆,再铲进车子上拉到场外边。早上时间较短,社员们把麦场打扫干净后便回家吃饭。
农村的早饭就是窝头、萝卜和糊涂汤(稀饭),社员们简单地填饱肚子,听到铃声便推掉饭碗朝场里奔去。
队长站在场里给社员分配活,几个社员有推麦的,有摊麦的,最后让长贵上麦垛往下搂麦。长贵是有名的滑头,他一看这活重便推脱说:“我不上!”
“为啥不上?”队长瞪着他。
“太高,我害怕掉下来,摔坏了身子老婆孩子谁来管!”长贵嘟囔道。
队长又扫了一下众人,“大柱你上。”
“我不上!”大柱拧了一下脖子。
“我是队长,我说的话你不听吗?”队长有些窘态。
“人家不上都中,偏要让我上,你这不是拣软柿子捏吗?”大柱也不是好惹的茬。
队长一下子为难起来,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最后落在小苦身上。“小苦,没人上你上,我看能累死人不能!”
小苦从人群中蹿出来,二话不说,甩掉布衫只穿母亲做的粗布短褂子,手里掂着三个铁齿的爪钩来到麦垛前,噌噌噌地往上爬,可因为麦杆光滑和麦垛又陡,爬了几次都滑下来。几个社员忙用槡木杈扎在麦垛上,小苦便左脚踩着下面的木杈,右脚蹬着上面的木杈拾级而上。
小苦站在顶端,用爪钩使劲扎进麦垛,搂起一大堆推下去,下边的社员用木杈把它推到场地的各个角落,另外几名社员便把成沓子的麦杆挑散,再把它竖起来。由于麦杆还未干透,要让麦杆留有空隙,既通风又透光,这样麦杆容易晒干。但又不能摊的太薄,太薄了几亩大的场地晒不了多少麦子,这些活都是有经验的庄稼老把式干。
小苦使出吃奶的力气把一堆堆麦杆推下去,不大一会功夫便搂完,不等队长吆喝便又爬上另一堆麦垛,又用同样的方法接连搂完五个麦垛。小苦满头大汗,粗布褂子已全部湿透。
队长看看小苦露出赞许的笑容,他在小苦的肩上拍了一下说:“去场外边的净地里抽棵烟去!”
麦场摊完以后,社员们稍事休息一会,大多数社员也饿了,便回家垫补一下,拿着窝头就着大葱边走边吃又来到场里。
场地里的麦杆在毒日头的烘烤和热风的吹拂下发出哔剥的声响,麦杆的空隙里塞进了阳光,灌进了热风,半天功夫上面的麦杆便干焦如麻叶了。上面的干焦那地下的还湿漉漉的,还必须把场地的麦杆再翻腾一遍。
等到中午麦子基本上全干透了。队长让社员回家吃午饭,临走时队长又高喊道:“吃过饭可别睡午觉,也该起场了。”
那时大队有台大型胶轮拖拉机,四个生产队轮流用。拖拉机就是比骡马碾场快得多,又有力气。三匹牲口只拉一个石磙,而拖拉机后面竟挂前后两排四个石磙。碾头一遍时速度较慢,石磙埋在麦杆里上下起伏像小船航行在浪尖里一样起伏不定,石磙碾过之后刚才还枝枝杈杈翘起的麦杆此刻全都平展展地躺在场地上。
碾第二遍时,拖拉机围着场地旋转得飞快,拖拉机在前边突突突地飞跑,四个石磙吱吱吜吜忙不停地跟着,石磙后面腾起一阵阵灰尘。不到一小时,偌大的麦场便碾压一遍。
五
吃过饭的社员此刻都在路边桐树下乘凉,有的在抽烟,有的在用草帽扇风。队长吆喝一声:“起场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