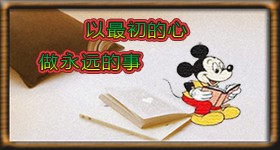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尘世(散文)
【流年】尘世(散文)
一
我看到庞大的鲜血,腥味扑鼻,满世界汹涌,再后来,一盏煤油灯照亮世界一隅,窄小的房屋里灰尘飞扬,在微小光中,蝴蝶一样翩翩起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觉得呼吸有些阻隔,身体越来越重——再后来,我看到了整个村庄,四周的高耸连绵的山峰是最好的遮挡,天空可以远到无际,而身体和灵魂必须跟随父母和整个家族。
四岁那年初秋,一个老人死了,从她离开人世那一天算起,距今大致三十年了,在深深的地下,骨肉早就成泥,甚至连最难以消失的头发和骨头都不复存在,然而我还记得她——初秋的上午,阳光穿过黑洞洞的门扉,从东边山岭的杨槐树顶上进来——我跟在母亲身后,踏上磨得光滑的石头台阶——进门,蛋黄的阳光正照在正墙下的黑木桌子上,上面摆放着鸡蛋、饼干、刚出锅的馒头,还有一包好看的糖块。西面的炕上,一个老人仰躺着,白发披在黑漆漆的枣木炕沿上,不断发出哼哼的声音——疾病在她身体里进行着致命的战争。母亲上前说了几句话。老人止住呻吟,对身边另一个中年妇女说:给孩子拿点吃的!
我不吃,母亲替我接住了。我看着诱人的糖块和有一层焦糊的饼干,想吃又不想吃——在我的潜意识里,总觉得那些吃的里面爬满了看不到的虫子,它们在窄小的空间里,纷纭翻滚,异常强大——我吃了,也会像那个老人,被无形的虫子们围困。没过多少天,早上起来,我看到麦场上搭起了一座黑色的布棚子,一口红漆棺材放在正中,很多的人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跪在前面哭哭啼啼;还有一些人,在哭的人后面走来走去,青黑相间的衣服看起来就像是黑色的蚂蚁。
母亲也在其中,她告诉我,你老(曾)奶奶死了,你就在院子里待着,千万不要去灵棚跟前。我不知道为什么,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切在明晃晃的日光中进行,人脚掀起的灰尘无孔不入,在阳光下灿烂明亮,一直到被庞大的黑暗迅速淹没。第二天一大早,阳光又照在了麦场的灵棚上,一些人又像蚂蚁一样蠕动,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中午时分,中秋的阳光照得地面上的甲虫总是寻着阴凉跑——很多人抬了棺材,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在大片哭声的簇拥下,消失在长着三棵柏树的老坟地里。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亡和出殡事件,一个活了八十多岁的老人,从十九世纪末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个人的生命跨度已经涵盖了庞大的王朝和历史——只是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姓氏乃至娘家在哪里,只是记得一个人在我生命的最初,以消失的方式在另一个人的内心留下痕迹。半年后,原先住在另一个村子的爷爷奶奶搬了进来——换了炕席和一些新的被褥,两个活生生的人,就睡在了死者生前的炕上。
我想这是奇特的一种因袭,人不断被自己创造的人所替代,肉体之外,还有灵魂,灵魂之外,还有世俗——如此,我觉得了蹊跷、伟大乃至不可思议与理所当然。他们说,曾奶奶和曾爷爷在自家墙缝当中塞了好多银元,还有清朝的铜钱。那时候的人,没处藏钱,就在家居内外的墙壁和地下打主意、想办法。我想,所谓“摇钱树”和“聚宝盆”之类的民间财富梦想大致与此有关。
对于传说中藏匿的银元和铜钱,我不知道那些东西在现在有什么价值,只是觉得,爷爷奶奶睡在曾奶奶的炕上,肯定有很多挥之不去的东西被他们重复了,比如生命的活跃和安静,时光的冲洗和命运的包裹,甚至还有曾奶奶所患的疾病。我从来没见过和曾奶奶一起生活多年,生养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曾爷爷。很多时候,我总是在想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兵荒马乱,到处杀戮和焚烧的年代,他和曾奶奶经历了什么,看到和做了一些什么?
二
再伟大的经历也是小民的历史,再伟大的时代也只是属于他们之外的大人物,比如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难和启蒙、鲜血和烈士、文化和文明、民主和思想,这些都与具体生活在南太行的小民们毫无关系。较为幸运的是,曾奶奶在我这个隔代人的内心留下了上述记忆——当她骨肉消匿,灵魂不再,还有一个活在世上的人用文字复述。而曾爷爷却没什么也没有留下,就连那座建筑粗糙的老房子,在时间之水一遍遍冲洗后,也已经找不到一点痕迹了。
爷爷奶奶一直在曾奶奶的房子里住着,到我8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在烟熏火燎的日常生活当中,将死亡和旧人的气息打磨得不见踪影。我也浑然忘却了幼时的记忆,每天晚上,早早吃过饭,就到爷爷奶奶家里去睡觉。爷爷是村里少数识字的人之一,看了好多古书。要不是“破四旧”,他的那些线装书我还可以看到——爷爷总是说那些神鬼狐妖,僵尸之类的故事。又一年秋天,村里辈分最大,年龄也最大的另一个曾爷爷也去世了。当晚,我和爷爷奶奶躺在炕上,在黑暗中张着眼睛,在黑夜铁粉一样漂浮的颗粒当中,总是看到墙壁上蠕动着一些人,豪华车辕,冠盖华丽,沿着曲折的山道,一路蜿蜒,向上攀行。
后来,我看到了死者的脸庞,活动的,微笑的,就连唇上那些发白的胡子也还泛着油脂的光泽——他的脸庞很大,像是一张阔大的遗像,在黑夜的墙壁上,表情丰富——我觉得了惊惧,我转身,把手掌伸进爷爷被窝,抓住他结实的手腕,身体在黑暗中不停颤抖。半夜,我被尿憋醒了,可是不敢下炕去尿,爷爷转身,从炕的一边,把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递过来——爷爷总是把它塞进被窝,过一会儿又拿出来,圆圆的壶口热气腾腾,腥臊之气氤氲不散。
我也学着爷爷的样子,把自己尚未发育的生殖器伸进壶口,然后撒尿,飞溅的尿液在瓷壶内发出清脆的响声——声音慢慢减小,尿液越来越多,体积越来越重——我再转身递给爷爷,他原样放好。如此很多年,我和爷爷共用一只夜壶——尤其是在北风掠地刮骨的北方乡村黑夜,夜壶的存在,绝对是一件令人心安的事。
还没等我长大,爷爷奶奶就搬进了我出生的房屋——那是当年他们为父亲娶媳妇修建的——也很粗糙简陋,外墙缝都没有用白灰粘贴,细细深深的墙缝不但进风,而且还吹进日月星光、大地的露水和寒霜、上天的命运和人间的困苦、欢乐和忧伤。我就是在那座房屋出生的。它的后面是我们家的猪圈,圈外有一片空地,下面是茅厕,一边长着一棵或两棵比房子还要高的蟠桃树。每年秋天,劁猪的人会抓起我们家刚买的猪娃子,用锋利的刀片割掉公猪的睾丸,像丢石头一样,扔进茅厕或者就地挖坑埋掉。
蟠桃,夏天就可以吃了,圆圆的,脆而且硬。我从小就喜欢软软的吃的东西——每次都要熟透了才好好吃上几颗。房子另一侧长着巨大的梧桐树,丰硕的叶子在夏天撑起阴凉,也不断有昆虫粪便落下来,春天的梧桐花经过蜜蜂之后,根部特别甜——我老摘掉后面的硬壳,用舌头使劲舔。这些都是爷爷和父亲栽种的,树木长高了,爷爷也老了,十三岁就能当成年劳力使用的父亲,胡子也一天天增多,皱纹在眼角像是荡着涟漪的水潭。母亲也是的——带着我一起下地,跟着许多人在一起干活,妇女孩子一大群,满山遍野的哭声喊声和铁器与石头碰撞的声音——我记得吃了一次大锅饭,稠稠的小米里夹了不少红薯——我吃得香甜,坐在母亲一边石块上,像一头饿极了的小猪。
三
春天,东风扶起万千植物,绿荫铺盖大地。父母亲辛苦了几个冬天,从大雪中挖出石头,用肩膀和手掌修整了房地基——请了许多人帮忙,其中,有我大姨家的几个表哥。那时候我还小,一块30斤重的石头都能把压趴下。而表哥们都大了,有两个先后结了婚。他们和我的父母一起,将房子凭空竖起。直到现在,母亲总是说:要不是你几个表哥,咱这房子盖不起来。
我们搬出了旧房子——我竟然没有一点留恋。新房子还没有粉刷完毕,我就带着懵懂的弟弟,一遍一遍往那里跑,一遍一遍问母亲啥时候我们才能搬过来。这样的一种心态是无意的,只涉及本性,不带有文化和传统色彩。等我们走了,随后,爷爷奶奶也告别了曾奶奶的房子,搬到我们先前的房子里居住——这在当时让我觉得了新鲜,意识到了,但不知怎么说——我想:人在获得新的物质,舍弃旧物的时候,是不会有一点留恋之情的,哪怕与个己生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新房子四周,母亲栽种的梧桐、椿树、苹果树很快茁壮起来,大片的绿叶在阳光中泛着大地泥土的光泽——芬芳的花朵引来了好多黄色的蜜蜂,像是善于群攻的军队,迅速击败了花朵。大雪下来了的时候,光秃的树枝上挽留了好多——一堆堆的雪,盛开在冬天的枝头,像凝固的舞姿,又像是一堆天堂的泄露物,在人间的北风中,凭空扎根。我和弟弟沉浸在新房子带来的喜悦氛围之内,就连弥散了好多天的浓重土腥味,都觉得新鲜无比。
春节,踏着积雪去给爷爷奶奶拜年,忽然觉得以前住过的老房子真是丑陋无比,到处都是灰尘,尤其是晴朗的冬天,阳光照射进来,飞舞的灰尘如同庞大的军团,从地面或者从空中,飞旋而下又飞旋而上——我觉得讨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灰尘?它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清扫不尽呢?夏天一如既往,只是蟠桃树生病了,不再结果实,父亲就把它们伐掉了。干了的桃树躯干让奶奶烧了好几年。长大的梧桐树一如既往,根部被孩子们刀子割的伤口越来越大,逐渐向内凹陷。只是它的冠盖依旧庞大,枝叶茂密,间或有枯了的树枝被大风打断了,落地的声音在午夜清脆响亮。
我们的新房子在村子之外,中间隔了一道山岭和一条河沟,与爷爷奶奶隔山隔河相望。我没事的时候,就到爷爷奶奶家去,坐一会儿,说淡话,身上有钱,就给他们买香烟抽。那时候流行张家口生产的官厅牌香烟,开始一盒两角钱,后来涨成三毛五分。爷爷奶奶都抽烟,极其喜欢。有时候他们感冒或者腰酸背疼,我会买药给他们送去。爷爷奶奶见人就说我是个好孩子,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等俺闭眼的时候,谁不在身边都行,俺平子一定要在!我嗯嗯着答应。
那时候,他们都很健康,尤其爷爷,脸膛黑红,膀大腰圆,要不是早年眼盲,也还是一个壮劳力。奶奶虽然裹着小脚,但牙齿特别好,吃饭的时候,隔壁邻居都还能听到她啃干饼子的声音。可能是有人居住的缘故,我们的老房子并没有像曾奶奶的房子一样,充满腐朽和诡秘之气。有几次,爷爷让我到闲置多年的老房子去拿东西,即使阳光耀眼的白昼,也觉得有一股说不清楚的气息,冰冷的手掌一样抚摸我的脊梁。而爷爷奶奶当时居住的老房子,到处都是人的痕迹,身体磨光的炕沿和门槛,还有椅子和窗台,就连木窗上的马头纸都没有漏洞。
站在山顶上,看到旧年的房屋,爷爷奶奶居住的,每天都有青色的柴烟喷吐出来,绕过阔大的梧桐树,与相邻的炊烟一起,消失在幽深如井的天空。秋天,旧了的石板房顶上还晒满了金黄的玉米和红色的柿块——成群的白肚皮的喜鹊、比煤炭还黑的乌鸦和怎么也飞不过屋顶的灰麻雀落在上面叽叽喳喳,慌乱啄食。我想,时间就是这样,被携带的日光和黑暗轮番照耀和覆盖。在房屋进进出出,吃饭和睡眠的人是我与生俱来最亲近的人之一,我的相当一部分血液来自他们,再由父亲和母亲传给了我——这种无形的联系,使得我时常有一种宗教的归属感——我最初的根。透过他们,我看到了这个家族庞大和绵长的光亮,从远古穿越迷雾,跟随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英雄流寇的王朝历史,一直流转到我所在的这个时代。
四
缓慢的铡刀起落之间,冬日的阳光显得灼热,干了的玉米秸秆纷纷拦腰而断。爷爷双手紧握铡刀,奶奶不断预进秸秆,灰尘从明亮的铡口飞扬而起。它们大部分来自田地,或者在堆放过程中,由风灌满。又经过锋利的铡刀,一粒粒飞扬而起,笼罩在爷爷的裤腿和奶奶的脸庞周围,像是一堆气急败坏的逃跑者。
中午时分,奶奶做了我最爱吃的饭——其实就是一小碟辣椒,吃得我满头大汗。吃完后,我回家睡觉了,奶奶收拾了碗筷,去一岭之隔的姑妈家。躺在自己的房间,没过多久,我就睡着了——梦见一只大雁,从高空落在一片芦苇丛中,水潭里好像有鱼,大雁扑腾着翅膀,怎么也捉不到……再后来,是父亲痛苦的嚎啕声,像是一把尖利的刀子,一下子就穿透了我的梦境。
爷爷死了!正在发愣的母亲忽然冒出这句话。我也怔了,站在新房院子内的椿树下,扭曲的阴影在地面上画得杂乱无章。快步跑到爷爷家,姑妈和父亲母亲都在,一个个哭声放肆,鼻子眼泪流满上衣。我看着,想哭却哭不出来,想使劲挤出几滴眼泪,可就是没有一点悲伤。很多年后,对此,我有三点解释:一是年幼,对死亡没有确切概念;二是完全惊呆了。爷爷,刚才还好好的,一顿饭功夫,就死了。三是我对爷爷的感情不够深厚。
不知道爷爷会不会知道,并因此怨恨我?很快地,爷爷也像我幼年看到的曾奶奶出殡一样,灵柩停放在我们家院子下面的荒地里——姑妈姑夫和表弟表妹都来了,还有爷爷的外甥,侄女儿,围在他的棺材前,真心假意地哭。我头戴白色的孝帽,上衣外穿了一件白布做成的褂子,跪在满是尘埃的灵前。我们家屋里屋外,院子上下都是脚步,每一个脚步走过之后,都扬起一大片灰土。父亲的嗓子哑了,沉重的孝服使他有了一些遗世独立的感觉,姑妈也是——他们兄妹两个是爷爷留在这个世上另一个自己,他们又分别繁衍出了另一些爷爷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