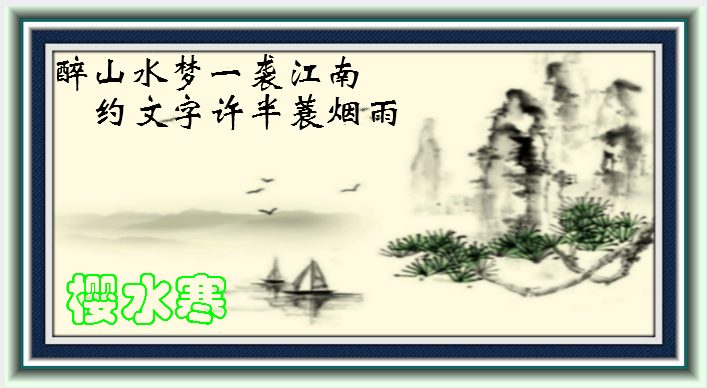【江南往事】城市,收割了农村的孩子(散文)
【江南往事】城市,收割了农村的孩子(散文)
我在小镇当老师时,在学区,也就是中心小学,学生有四百多。学前班一个,一到四年级,各两个。每个班四十个学生左右。前段时间跟另一个老师说起,现在中心小学只有二百来学生了。或许有一天,就没有了。他瞅着远处莽莽青山,说,没有了,我们该咋办?我说,没有了,你们都就进城当老师了。我们都笑了。这笑,五味杂陈。
不是孩子没有了,是都进城了。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来小镇参加统考,那时候,光中心小学就上千人,一下课,波涛汹涌的人就冲出了教室,瞬间把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塞满。而后来,下课,校园里总是稀稀拉拉的。曾经震耳欲聋的喊闹声消失了,曾经做早操时密密麻麻的阵势消失了,曾经繁忙并快乐的日子消失了。曾经嫌学生多,太吵,太闹,太烦,要是少点,多好。如今,真少了,满眼望去,像秋天的庄稼,这搭一颗,那搭一株,心中便生满了无限的伤感和失落。
孩子们一个个跟着父母进城上学了。这些年,尤其是近几年。农村的所有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他们带着孩子,来到城里,在城中村租一间房,每个月二三百元的房租。屋里留下女人,给孩子做饭,早晚接送。男人早出晚归,在市场上找零活干。
我有两个侄子,大的在中心小学上到四年级,小的刚在村小上了半年学前班。学生放暑假前,我的表哥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两个孩子在城里找一所学校。我托人,找了所。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民房。女人负责摊子的一摊子,表哥外面搞粉刷挣钱。
我在小镇当班主任的那学期。第一天报名,三十八个,过了两天,少了两个,又过了一天,又少了两个。他们的父母来取课本,才知道转学到城里了。我跟一只老母鸡一样,领着自己的一群小鸡,越领越少。最后只有可怜兮兮的不多几只跟着我。
其实,在小镇,至少还有二百来学生,更惨的,在村学。比如我们村子,我上学时,算是后鼎盛时期,五六十个。接着就越来越少,主要是计划生育,原先生三五个,现在大多生两个,原先生一堆姑娘等个儿子的,也是两个。后来,两个孩子长大到了生儿育女的年龄,一个姑娘嫁出去,儿子生两个,村里的孩子又减少一茬。村小的三四年级只有两三个孩子,合并到邻村了。没有学前班,只有一二年级,不足十个。两千年时,还没有进城上学的风气。打工的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没有孩子。五到后,在外打工的八零后娶妻生子,十年后,孩子开始上学。这时候,大规模的孩子大军开始涌进城市,在城里接受教育。现在,我们村的小学彻底倒闭了,没有一个学生,一个老师。站在梁上,朝下面,黄泥土夯起的教室摇摇欲坠,地震后搭起的活动房蓝色的屋顶开始掉色,满院荒草丛生,山鸟、老鼠、野兔,在教室里的破课桌里安家落户了。
在乡下,本来教学条件就简陋,师资力量有限,没法跟城市相提并论,一些家长在外打工,思想观念变得活泛起来,也看重了孩子的教育,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便选择进城。学生一进城,学校人数越来越少,老师也就慢慢失去心劲,不再好好上课,开始打逛,心不在焉。老师教不好,家长有意见,便给孩子转了学。学生越少,老师越没有动力。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慢慢的,能转学的基本全转学了。
有些村小,还剩一两个学生,一个老师带着。感觉实在是可怜兮兮的。去学校吧,偌大的校园,野雀乱飞,不见人影。老师只好把学生带回自己家上课。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教学了。但只有一个学生不转学,附近又没有村小,无法合并,就只能这样存在着。不能因为人少就放弃了这个学生。正常的课还得上,学区要的各种资料还得报送填写。麻雀虽小,五脏还得俱全。在乡村,这样的学校大量存在着,显得怪异和尴尬。
曾另一头的城市,因为农村学生的进城,各个学校爆满,一个班八十个学生,严重超负荷运转着。而介绍农村学生进城里的小学,每个学生因学校优劣的不等,收费从两千到一万,成了一种众人皆知、熟视无睹的资本产业了。
为了缓解城市教学压力,也为了调配闲置的农村教师,这两年,政府举办了教师进城的考试,五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农村老师考进了城。这是解决这种现状眼前看着还可以的一种办法了。
我跟那个老师坐在山顶上,说起这些事。他可是当了一辈子老师的人了,看着日渐稀少起来的学生,就像看到了日渐凋零枯萎的果园,他内心翻滚的失落是我难以理解的。他说,按照这样的速度,三五年,这二百人也就没有了。我不是一个思考者,我只是凭着感情模糊的判断着事物的走向。我想,在城市化的浪涛中冲击中,乡村小学终会淹没于滚滚潮水中,消亡掉,成为回忆。
我说,到那时,乡村老师就全部进了城,再也不用费尽周折花钱求人调动了。
他说,那时候,进城是年轻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了。
而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
我问,农村会消失吗?
他说,到消失的那一天,我就早死了。
夜幕降了下来,青山暗淡,森林迷蒙,像有人从远处拉上了天和地的拉链,黑夜卷来,染黑了他粉笔末浸泡了一辈子的白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