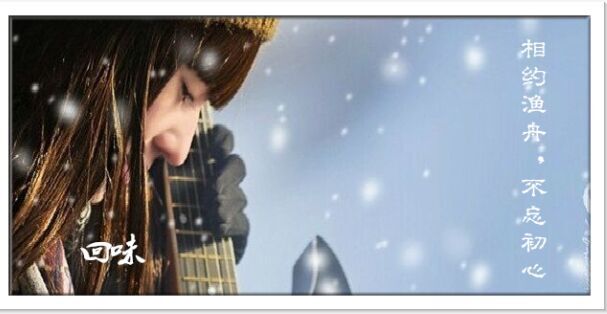【渔舟】塞外木塔(散文)
【渔舟】塞外木塔(散文)
![]() 山西有一个应县,应县有一座木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和巴黎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座木架结构的塔,建于辽清宁二年。
山西有一个应县,应县有一座木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和巴黎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座木架结构的塔,建于辽清宁二年。
很荣幸,我就是应县人。
小时候,上木塔只要五块钱,可我不止一次徘徊在院墙之外,仰视着高耸入云的塔,心里清楚地知道那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只能看着塔层上攒动的人流,心里充满了向往。等到现在,挥挥手轻易拿出了六十元钱进去,却依然无缘登顶,工作人员说木塔已经倾斜,只能在底层参观。
年幼时的思想所存留的只是木塔很好看,很神奇,也很出名,这一个高大上的概念完全来自于身边的老辈们,他们津津乐道地传说着,眼里闪现着明亮的光芒,完全陶醉其中。
我很清楚记得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在木塔下照了一张全家照,那是至今唯一一张我们一家五口人的合照。父亲和母亲坐在中间的板凳上,大哥就站在父母的身后,我和二哥一左一右在父母两侧。当时大哥二哥都是刚剃完光头不久,头皮生出很短很短的茬子,二哥的左衣角还被掀在了母亲身后,而我穿着红色上衣,粉色裤子,低垂的马尾搭在肩上。一家人的脸上都有着淡淡的惆怅。那时,我们很穷,没有钱登上木塔,只能在靠近它的地方留下定格的影像,用以填补内心的缺憾。
木塔,像一个神秘的梦,一直滞留在我长长短短的岁月之中。
说起木塔,必须要说辽。
后晋高祖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于契丹,并以父事契丹而换来自己所谓的大晋王朝,它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应县,当时叫应州,也在被割让之列。虽然石敬瑭的锦绣江山不过经营了六年而已,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他这么一个短命的朝代,但他却对中原王朝的遗害长达四百多年。至此,中原王朝一直不曾停止修复江山的残缺。
雍熙三年,宋太宗赵光义发动第二次攻辽战役,兵败之后,他抱定一种鱼死网破的念头,意图给敌人只留下一片又一片空城,他下诏杨业以及潘美等人带云朔(云州、朔州、应州、寰州)四州民众全部南迁。而就在这场南迁战役中,像历史上太多雷同的忠将与奸臣的对手戏一样,杨业被害而亡。随之,那一次浩浩荡荡的归家之途,有太多来不及迁走的人只能继续归属于辽,在异族的统领下,倔强地生存着,他们被称作云朔遗民。一生渴望南归,却和脚下的土地一直被轮番倾轧。
在那时,应县的土地上竖起一座辽人的塔,并不稀奇,那是他们的疆土,是战利品。
传说,辽的几代统治者大多信奉佛教。再者,五代以来建立家寺之俗盛于辽境,亦影响于当时的上层。应县木塔就是辽兴宗耶律宗真的仁懿皇后萧挞里申请所建的家庙。萧皇后的父亲萧孝穆是当时朝野的重要人物,他去世之后,萧皇后便申请为其祈福而建寺。在现今木塔的后院确有一座寺庙,全是辽代风格,只不过现在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而成,但足可说明家庙一说的存在性。连木塔底层供奉的佛像也是遵从辽风格,留着长须,有耳洞,还戴着耳环。照壁板上,有六幅供养人画像。契丹史学者张畅耕先生从衣饰等各方面考证,此六个供养人全系萧氏家族代表人物。南面三女像为圣宗皇后萧耨斤、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道宗皇后宣懿皇后萧观音;北面的三男像为萧挞里的父亲及其长子、次子。
萧挞里系应县人。《契丹国志.后妃传》中有记载:“兴宗皇后应州人,法天皇后弟,枢密使,楚王萧孝穆之女也。”而画上其她两位皇后正是她的姑母以及表妹,也是她的儿媳。从太祖皇后萧氏再到有名的萧燕燕,算来这萧氏可谓是“一门多后妃之贵”。
木塔全名叫佛宫寺释迦塔,顾名思义,这释迦塔是与佛祖释迦牟尼有关。是的,这寺里供奉着世界上罕见的释迦牟尼的两颗佛牙舍利,据说这天上地上一共也就七颗舍利,而被人发现的只有四颗。斯利兰卡有一颗,北京八大处有一颗,仅应县的木塔就占去了两颗。
我进去的时候,只能站在底层膜拜着高大的佛祖,看到它顶部精美华丽的藻井,还有内墙上画着的六幅如来佛像,门洞两侧壁上的金刚、天王、弟子等。我自然不太懂这些,好像进哪家佛寺都是如此雷同的雕刻,西侧墙的楼梯倒是分外吸引了我。楼梯也是全木结构,我凑近细看,果然在接口处是一木含一木,整齐而合理,全然没有钉子咬合的痕迹。我摸了摸,似乎有厚厚的尘埃,往上看,一条幽深的路打着弯通到楼上,光线黑暗,一种朴重、深沉的感觉扑面而来。
由于工作人员事先说明,虽然我想要拾级而上的欲望相当强烈,想踏着这厚重的历史尘埃走上去,走到更广阔的辽文化中去,但还是咬咬牙,遗憾地掉转了头。
底层有南北两门,从南门进来,从北门出去不远就到了后院的庙堂。我往下走了走,抬头再看木塔,塔顶是八角攒尖式,立着一个铁刹,每层塔的檐角下都挂着一个风铃,风一刮,叮叮当当,清脆悦耳,甚是好听。这样的建筑风格是继承了汉、唐以来的重楼建筑风格,共五层,各内层夹有暗层实为九层,塔顶是应县的最高处。
我无缘登上二层或是更高的地方,听人说上面光线充足,各留四门,均设木阁门扇,出门远望,苍茫辽远,美不胜收。,
有的时候,遗憾也是一种美,且让这美就永存心间吧。
仔细打量塔身,塔上挂了好多匾,其中“竣极神工”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四年率军北伐,驻军应州,登城玩赏时亲题。而“天下奇观”则是正德三年明武宗在今天山西阳高、应州一带击败入侵的鞑靼小王子,登木塔庆功时亲题。
这里,除了佛牙舍利、各朝牌匾、对联,还有很多珍贵的辽代文物、经卷、尤其是辽刻彩印填补了中国印刷史上的空白。
我是震撼的,为这一座宝塔而震撼,更为古代的能工巧匠而震撼,是什么样的智慧才能让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这宝贵的财富,才让这木塔屹立千年不倒?
木塔的周围日日有无数的麻燕环飞,谓为一观,据专家说,它们以蛀虫为食,正好保护了浑身是木的塔。而我更愿相信,木塔不倒是源于一种精神,一种塞外人民不屈不挠,在逆境中坚强挣扎、存活的精神。
梁思成先生也曾慕名而来,叹为观止!
不是没有经历过风雨,不是在安逸的岁月中走过。生于边塞,就注定了动荡,在金戈铁马中探取着一丝安乐。从来不曾停止的争斗,从辽走到金,再到大元,后来跌入日寇的魔掌,军阀混战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木塔以及它脚下的土地满目苍夷,苦不堪言。
岁月无声,苦难无言,他就那么站着,固执地站着。
曾有200余发子弹凶猛地射向它的身体,而它依然骄傲地立在那里,像冲天的巨人。枪林弹雨经过,狂风暴雨也经过,更少不了地震,还有雷电的猛击,只不过,它都一一接了过来。要有多大的坚强才能如此屹立不倒呢?或者说要有多深的隐忍才能承受得了那么重的苦难?看无数人在它的面前血染长袍,看王朝替代,争夺不休;看日本人在它的面前对中国实施奴化教育,看他们对无辜的民众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也看他们的叫嚣。当然,它也看到了自己的同胞在解放战争时期自相残杀,暗无天日。
木塔,只是冷冷地看着,却分明它的身体有万万股热血在翻滚,在汹涌。我想,它一定坚信,捱过了漫漫长夜,就会看到黎明那一缕曙光,继而阳光加身,无比愉悦。
历经了民族的融合与分离,再融合,这一路走的好漫长,好艰辛。辽不存在了,后晋也好,大宋也罢,都成为了一缕历史的尘烟。而今的应县是崭新。这一座塔啊,或许代表的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文明,而是多民族文化的糅合。雁门关前,边塞要地,这里生活过很多的少数民族,娄烦、鬼方、匈奴等等。应县,是一块多姿多彩的土地,浸润着五彩缤纷的文明。
这是一种融汇,更是一种提升。
木塔附近建起了许多仿辽建筑,在现代化的繁华之中,它们仿佛有点抢眼,但正是说明了辽文化在这座古老的小城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而且还会一直传承下去。
有着农耕民族的内敛与睿智,也有游牧民族的顽强与勇敢,这就是新时代的应县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建设着新家园,让自己的城变得美丽无比。他们也用自己的智慧经营着富饶的新生活。
应县人杰地灵,历代也出过不少的名人志士,战争年代更是英雄辈出。
应县其实很美,但它依然是平静的,它一直低调地存在着,缺少开发,缺少宣传,以至于这份美太过含蓄。它一直默默地存在,顽强地生存。
我特别想带父母再到木塔前拍一张全家照,我想现在定然不会再有惆怅的样子。父母满脸的幸福,必然像木塔檐下的风铃,叮叮当当,悦耳无比。与众多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一样,我们一直在用心地活着,在贫瘠的土地上攫取着卑微的快乐。我们也一样在岁岁年年的坚守中,顶礼膜拜着一种信仰,苦苦支撑着一个坚定的信念。
这也许就是应县的精神图腾,土地如是,木塔如是,它的子民亦如是。
大地,用最具体最生动的方式,记载着历史,大地也用最温暖的方式包容着残忍与苦痛,同时,大地又是以生生不息的形式传诵着美好,启迪着人们热情地去生活。
就这样,我们热泪涟涟地咀嚼着苦难,也不甘轻而易举地倒下。
木塔有点倾斜了,但毫不影响它的雄浑与豪迈,它一身都是故事,都是传奇,它见证着应县的历史,也孕育着应县的文明。我知道,以后,我也会像老辈人一样,把木塔的故事说给孩子们听,而孩子们,还会告诉他的子子孙孙。
我静静地望着这座塞外木塔,它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仿佛它又告诉了我许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