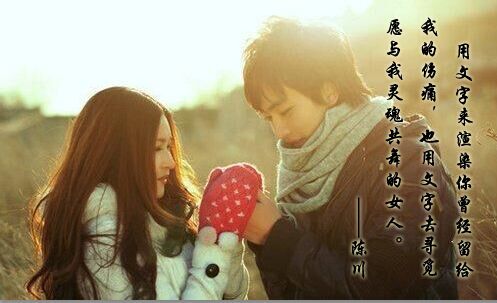【百味•夏之情】再见了,棚户区的老屋(散文)
【百味•夏之情】再见了,棚户区的老屋(散文)
“老李,钥匙拿到手啦?多少平方,几楼?”“八十平方,二楼!老张,你嘞?”“我?九十平方,六楼!”近段时间,鹤煤棚户区的拆迁户们,通过抓阄,全部拿到了新房钥匙,个个喜笑颜开,有的开始计划装修。
城市国企棚户区的拆迁,是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河南省鹤壁煤业集团所属22个单位的棚户区老屋,现已全部拆迁完毕。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新楼房,黄色的外观,宽敞的大玻璃窗,楼房还是集中供暖,又漂亮又气派。
座落在鹤壁市山城区汤河桥西鹤煤总机厂工人村的那片窑洞房,是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时期修建的,已有50多年的历史。如今,已不见了踪影,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十几栋带保温层的黄色六层新楼房。虽然水电还没有接通,但从拆迁户们的脸上,我看到的是掩饰不住的喜悦。大家隔三差五地就来新楼房外转转,盼望早些搬进来。
破旧的窑洞房,终于成了历史,定格在我的相机之中。看着窑洞房老屋的照片,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老屋虽然破旧,但我家和亲密无间的邻居们,足足住了五十多年,我儿时、少年时的美好记忆,都储存在这里。
我家是1959年住进这两间40平方米的老屋的,当时全家老少一共6口人,三代人在此居住。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我的孩提时代,可我这个女孩比男孩子还淘,能上树,能爬房,敢下河捉鱼摸虾。我家门口很宽敞,有棵大槐树,每到春季四月,上面开满了洁白的槐花,一嘟噜一串的,煞是喜人。香气扑鼻的槐花招惹了许多工人村的小孩,大家吵着要吃。于是,我就爬到树上,去摘那些开得最旺的槐花,然后一串一串地往下扔,让大家去抢,我则得意地在树上哈哈大笑。回头再看看我一身灰土不说,手上、胳膊上被槐树枝和槐刺挂得一条条血印。有时衣服也挂烂了,鞋也磨破了,少不了下来挨母亲一顿吵。但吵归吵,母亲一进屋,我又蹭蹭几下爬上了另一棵比槐树更高的大杨树上去看风景。
再一点就是不顾危险上房子玩,看谁的胆子大。我同几个男孩子爬上房顶或扑腾扑腾地来回疯跑,或不顾危险爬到房檐上去摘酸枣。大人们在屋里听见房上有人,就出门吆喝。这时,房檐上立刻露出一排小脑袋,冲着大人摇头晃脑地傻笑,根本不听吆喝。我当时伸伸脑袋往下看:呦,好高呀,房下的大人们那么矮小,直看得人眼晕。后来,有个厉害的邻居大叔掂着棍子上房来撵,我们这群淘气包才悻悻地下房。
那时的老屋在我眼里,是那样的宽敞、温馨、舒适。我们院一共两栋对脸窑洞房,10户人家,60多口人。虽偶有邻里摩擦,但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彼此以诚相待,无话不谈。端碗串门,互相交流生活经验。大人打孩子,邻居家是最好的庇护所;张家外出锁了门,就将钥匙放到李家;王家来了亲戚,刘家必得登门拜会;一家出了事,9户全来帮忙。老屋最快乐的时光是过年,那时没有电视,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将火墙烧得热热的,全院的小孩都挤在我家过除夕,吃花生、嗑瓜子,高兴极了。屋外北风呼啸,白雪飘飘,屋内暖暖和和,温馨无比。大家互相逗乐取笑吹牛,你挤我,我抗你。一会她给他起个外号,一会他给她出个洋相,来点文雅的,就是唱歌、讲故事、做游戏。那个开心劲,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每到夏季,我家门口的大槐树下,就聚满了前来乘凉的邻居。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大人孩子端着饭碗就来这里聚会聊天。这里,大家可以互尝饭菜,你碗里有饺子,就拨给他两个。他家烙了油饼,就撕下一块给我尝尝。谁家饭点来了亲戚,馍不够吃了,自然有邻居送上自己家蒸的菜馍馍。谁家的孩子馋嘴了,瞪着小眼睛看别人吃鸡蛋捞面条,这时候,孩子的母亲和邻居就来拉扯孩子,一个骂孩子“嘴咋恁馋嘞?”,使劲往家里拽孩子,另一个端着一小碗鸡蛋捞面条就撵着往孩子的手里塞,责怪母亲“见外,不心疼孩子!”我的隔壁邻居王叔家,7个孩子,但每每家里包了饺子,王婶、孩子们不吃,总要先给我家送上一碗。邻居杨奶奶,哪怕家里有半个西瓜,总要切两块送给我和妹妹吃。尤其是中午,树上的知了“知——、知——”地乱叫唤,大人们下了班,小孩子放了学,大家搬着小板凳就来到槐树下,一边吃饭,一边谈天说地,将各自看到的新鲜事、稀奇事来这里侃侃而谈。新闻谈资有工厂车间里的、有学校课堂上的、有工人村里的、有大街上的、还有广播里的、附近农村的、甚至老家里的,邻居们个个滔滔不绝,边吃边聊。那时候,邻居们的关系处得相当好,大家说啥都不见外,一碰面就挖苦:“5分钱的肉就够你吃了!”另一个立即回敬:“2分钱的肉就够你家过年了!”大家彼此信任,毫无隔阂,什么张家长李家短,自家的愉快与不愉快,从不忌讳,开心畅聊。这里没有矛盾,没有纠纷,心里有烦恼只管讲,人人开心舒畅。
每到夏夜,弯弯的月亮挂在空中,天上繁星点点,萤火虫点着灯笼到处嘤嘤,不远的汤河传来阵阵蛙声。我家门口的大槐树下,邻居的孩子们或抱来了凉席,或拖来了草苫,都来抢占地方睡觉。月色渐浓,小孩子躺了满满的一地,一边互相打闹,一边数天上的星星,看亮亮的银河,顽皮地吱哇乱叫唤。有时夜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机身上夜航的红灯和绿灯一闪一闪的,在黑色的夜空中显得格外漂亮。孩子们脸面朝天就大声喊叫,盯着飞机一直看,啥时候飞机看不见了,他们啥时候消停。凉席旁边坐着几个大人,手持一把芭蕉扇,一边乘凉,一边聊天,一边为孩子们赶蚊子。我躺在凉席上给大家讲故事,讲着讲着眼皮就开始打架,同小伙伴们一同进入了梦乡。半夜,家里的大人怕我们着凉,悄悄为我们盖上了带补丁的床单。然后,又摇着扇子为我们驱赶蚊虫。
时光如飞梭,转眼就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提起这些50年前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儿时的伙伴,如今都老了,各自奔东西。随着棚户区的改造,轰鸣的机器声,大家居住的老屋不见了,变成了一片瓦砾,后来,就变成了一幢幢的新楼房。
邻居、伙伴们虽然人人都盼望着尽早住上新楼房,但盼归盼,大家心头对棚户区老屋的那份感情,是永远也抹不掉的。现在,大家虽然都领到了新房钥匙,高兴地互相问候,但心里最想说的一句话便是:“再见了,棚户区的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