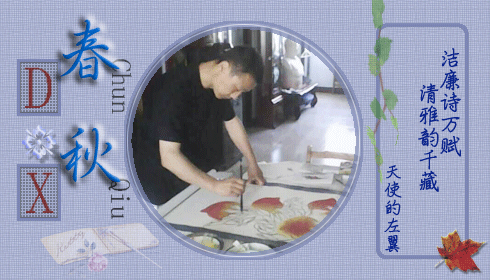【江山多娇】作业之殇(随笔)
【江山多娇】作业之殇(随笔)
![]() 唐代无名诗人留下两句脍炙人口的诗:“一种春声混难忘,最是长安课归时。”清代诗人高鼎的《村居》中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小时候放学时那种欢快、嬉闹得场景和感觉,让人终生难忘。孩子们如出笼之鸟,欢欣雀跃之情,溢于言表。放学之后,无拘无束,一群小狗似的玩疯了,一直玩到暮色渐浓,方才陆续回家。这是何等美妙的童年!多么美好的画面啊!天真的童心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释放,充满无穷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
唐代无名诗人留下两句脍炙人口的诗:“一种春声混难忘,最是长安课归时。”清代诗人高鼎的《村居》中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小时候放学时那种欢快、嬉闹得场景和感觉,让人终生难忘。孩子们如出笼之鸟,欢欣雀跃之情,溢于言表。放学之后,无拘无束,一群小狗似的玩疯了,一直玩到暮色渐浓,方才陆续回家。这是何等美妙的童年!多么美好的画面啊!天真的童心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释放,充满无穷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
从上面的诗句中不难读出,古代的孩子绝对没有那么多作业,不然,他们怎么可能玩得如此痛快?古代也绝对没有今天这么多考试,因为科举制度两三年才考一次。
提起作业,真的想说爱你不容易。网络上关于作业的各种调侃铺天盖地,都是经典的黑色幽默,有古诗词类:
风萧萧兮易水寒,写作业兮不复返。
黑云压城城欲摧,作业压人人悲摧。
醉卧作业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写作业。
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业。
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
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作业。
生当作人杰,死亦写作业。
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继续写作业。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写作业。
有歌曲类:
你问我的苦有多深,作业代表我的心。
起来,不愿写作业的人们!用我们的作业本筑起新的长城。
万家灯火数不清,灯下钢笔写不停;作业好似满天星,何时才能摘干净。
天上的星儿亮晶晶,那是仙女点亮的灯,为怕作业没完成,闪闪发光到天明。
四周老师有那么多,好像是浮云飘过。有个恶魔谁都斗不过,传说中的作业让你没处躲。
深夜的月光凝结成霜,迷茫的风和文字流淌。爸爸妈妈在幸福梦乡,独剩我桌前孤灯头晕脑涨,李白的床前满地白霜,清明的雨季路人匆忙。抄写和卷子比长城长,放假的日子还有那么漫长。
有名言名句类:
人之初,性本善,不做作业非好汉。
君子坦荡荡,小人写作业。
我对作业不仁不义,作业对我不离不弃。
老师带我们在题海中遨游,结果她上岸了,我们全都淹死了。
一大波作业正在逼近!
放假就是换个地方写作业。
作业与你同在。
笑一笑,十年少,少做作业多睡觉。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前不久刚发布的《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过去3年时间,我国中小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长虽然由3.03小时降低为2.82小时。但仍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比如,同为亚洲国家,我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是日本的3.7倍,韩国的4.8倍,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差距也比较明显。而且,91.2%的家长有过陪孩子写作业的经历,其中每天陪写的家长高达78%。
据有关数据统计,世界各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间如下:日本0.58小时,韩国0.76小时,法国1.02小时,英国0.6小时,美国1.22小时,德国0.94小时,加拿大1.1小时,意大利1.6小时,西班牙0.8小时,澳大利亚1.2小时。
按理说,学生做作业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每天花这么多时间用来做作业,那就不是作业,而是“作孽”!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还真有这个意思,作业,就是不想好好活了,作死。没想到如今竟然有点诡异地一语成谶。
今天的作业成了许多家庭悲剧的制造者:
2014年5月21日一位杭州父亲发现女儿抄袭同学作业气愤不过,于是把女儿拖到车棚里,先用一根草绳勒住她的脖子,再用另外一根绳子抽打,后发现女儿满脸发紫停止呼吸,即送浙医一院,女孩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7年11月22日夜晚,浙江义乌復元医院急诊室突然冲进来一名满脸泪水的中年女子,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我丈夫喝了一大口农药,现在在车上,赶紧帮帮我!救救他,救救他……”而问该男子(姓楼)为什么突然想不开要喝农药,知道真相的医生护士都懵了。
原来夫妻俩因为孩子做作业时字写得不好而发生争吵,吵着吵着,楼先生突然转身跑进杂物间,拿起墙角的草铵膦就开始往嘴里倒……
许多校园悲剧也跟作业有关:
不久前刚发生的湖南沅江三中学生罗宇杰弑师案,就是因为周末补课时,班主任鲍方布置大家观看一部励志电影,要求写完观后感再放假。罗宇杰说自己不想写,与班主任发生了争执,结果拿着弹簧刀捅了鲍方26刀。
有关部门整天喊着减负减负,然而中小学生的作业负担却越来越重。
正如一位网友所写:不久前国庆中秋假期,孩子带回家的作业,仅试卷就52份!以做完一份试卷2小时计,全部完成需要104个小时,而整个假期只有七天,还不包括来回路程的时间。这是何等可笑又病态的教育方式!
就拿某省新高考改革来说,本来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但是为了选课,绝大部分高中从高一开始就安排了10门课(其实是11门,因为技术包括通用和信息两门课)。这10门课不包括音体美和心理课。你想想,即使按照每天8门课计算,一门课如果留25分钟作业,也要200分钟才能完成。实际上,数学、物理等科目25分钟根本不可能完成。如果周日回家每门课安排40分钟作业,需要400分钟才能完成,将近六个半小时。
还有数不清的竞赛班、补差班、强化班,还有数不清的围棋、萨克斯管、跆拳道、英语口语、钢琴、书法之类的五花八门的兴趣班,简直就是把祖国的花朵变成了机器,孩子还不如一只小狗快乐。
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少做点作业,减轻点负担呢?
面对当今的教育生态,说实话,你还真的不能减。谁减谁吃亏已经被无数敢于吃螃蟹的学校证明。减到最后,你会发现,学生的考试成绩将一路滑坡,被人家远远甩在后面。有的学校想减轻一点学生负担,结果成绩下滑,结果领导不满意,家长不满意,成了人家的笑柄。所以,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做加法。看看现在的重点高中,一个月休息几天?我所知道的温州一所有名的重点中学,高三今年国庆只放了一天假。再说,如果公立学校减了,私立学校不减;学校减了,家长不减,最后还是一地鸡毛。
前不久,媒体人魏濂的一篇文章劲爆网络,他说中国的教育已经被剧场效应绑架,成了一个绕不开的死结:目的功利化、手段高压化。所谓剧场效应,就是如果剧院着火了,如果每个人都想着先跑出去,其结果必然是大家都拥堵在门口,谁都跑不出去,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他人利益的行为,导致了群体悲剧的上演。正如那篇文章里所说,开始大家都坐着看戏,后来有人站起来,于是后面的人、周围的人,都只好站起来;于是有人只好站到椅子上,最后所有人只好都站到椅子上。
现在的中国教育比的就是谁更不守规矩,谁更能压榨。你每天上八节课,我每天上十节;你每天上十节课,我每天上十二节。你每个月休息八天,我休息四天;你休息四天,我就休息两天,甚至一天。这个功利化的社会,只有分数才是硬道理。有位校长有句名言:抢时间,你不会抢啊?你抢不过别人你怪谁?呵呵,很有意思。
这个局究竟困在何处?
一是激烈的竞争环境,特别是就业竞争。职业待遇的巨大差距,就业环境的恶劣才是祸根:在中国一纸文凭是致命的,你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别人不会给你展示才华的舞台。几十年前我上学读书的时候,星期天节假日从来不做作业,当然也没少挨老师批评。记得中考之前,学校放了一个星期的家,我回家看了一个星期的《封神榜》。这些我从来不敢公开跟学生讲,讲了就是自讨苦吃。因为时代不同了,那时候也没想着一定要考上大学,反正考不上就回家当农民。我甚至打算,不上学就去赚点钱,买个手扶拖拉机开开就非常满足了。而如今,考不上好的大学,想找个好点工作,简直是天方夜谭。你看看那些好的企事业单位的招聘,动不动就是要求985、211,甚至还指名要那些名牌中的名牌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的找工作竞争跟古罗马的角斗场差不多。你只有在竞争中干掉别人,干掉成百上千的同龄人,方能脱颖而出。而要获得一切的顺利成功,你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由于教育资源分配极其不公,有的学校是中央军,有的学校是杂牌军;有的学校是嫡长子,有的学校是庶出的小儿子;有的是前娘生的,有的似乎是后娘生的。所以从幼儿园开始,就要上一流的,小学初中,直到高中大学都要上重点。
二是现代社会诱惑太多,领课余时间如果不用作业占,就要被手机和电脑游戏占领。如果没有很好的引导,你指望孩子周末回家能好好读点书,完全靠他自己的兴趣学点有用的知识技能,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不反对孩子玩游戏,但是凡事皆有度,如果你整天泡在游戏里不能自拔,那结果恐怕也是悲催的。因为人,很容易变成工具的奴隶。现代社会,大家都很忙,没有几个家长能有大把的时间陪着孩子。平时加班加点不说,就是周末也未必轻松。为了生存,许多人都累得像狗一样,哪还有精力花在孩子身上?怎么办?只能把孩子托付给老师,或者尽量用让作业来填补孩子的空余时间。在许多家长的心目中,还是“小人闲居为不善”,与其放任自流,还不如给他分派任务,让他不能闲着。造成的结果是学不进去,玩不痛快,睡不踏实。即使有空陪孩子学习,那又如何?孩子平时在学校有老师管着,回家还要被家长管着,真是不学习母贤子孝,一学习鸡飞狗跳!
三是评估体系的单一化、行政化、政绩化。现在评价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看什么?看高考;评价一所学校的办学成绩,看什么?还是看考试;评价一个教室的教学水平,看什么?还是看考试,看分数;高中大学的录取看什么,还不是看分数?只有分数才是硬道理,别的都是浮云。教育GDP是罪魁祸首。所有教育官员甚至政府主要官员都把升学率当成政绩,教育拨款特别是高考奖金基本上是与高考成绩成正比的。某个地区的高考只要升学率特别是一本率成了高考的命脉,考好了,可以一俊遮百丑,从上到下皆大欢喜;一旦出现滑坡,政府的板子就会打到教育主管部门身上,教育主管部门的板子就会打到校长身上,校长的板子就会打到教师身上,教师的板子就会打到学生身上。捶打凿子凿打木,层层传递,还要层层加码,于是乎不惜题海战术,甚至题洋战术,只要教不死,就往死里教;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不增加作业,能有何招?因为对付应试教育,最管用的还是刷题。
再说,如果中国的教育真的像美国那样招生,恐怕大学招生就会变成拼爹游戏了。
美籍华人沈宁先生在《培育自由》中写道,上小学时,他们班在老师的指导下,用了整整一个学期,制作了一条大木船。那么不上课吗?人家回答说:那不就是上课吗?制作木船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了绘图、读图、测量、计算,几何、三角、力学、化学、历史、地理、天文、气象、木工等知识,训练了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启动了思考力,扩张了创造性。
可是,我们的老师敢这样做吗?学校校长会允许你这么做吗?按照目前的考试形式,这么做你能保证你考出高分吗?我想起了多年前英年早逝的怪杰朱海军,此人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学教语文,非要搞什么英汉双语教学,还带领学生到什么墓地去感受体验写作文,结果被下放到小学教语文。从中学语文到了小学,喜欢胡说八道的习惯一点没改,结果连小学语文课也教不成了,竟然当上了小学劳动课老师。即使这样,他仍然不改本性,一年春天,正上着劳动课,窗外突然下起雪来,朱老师对孩子们说:还上什么课,春天下雪很难得的,都给我出去看雪去吧。最后他只好从课堂里滚蛋了。我们的社会没有容忍另类的土壤。
人,活一辈子,本该快乐,为何非要套上重重枷锁?如果以牺牲天性为代价,这种教育还是不要也罢,这种作业还是不做也罢。
随着科学的发展,机器化的刷题除了应付考试,将来能有什么用处?也许,不久之后,你攒了16年的一肚子墨水,或许还不如一串代码、一个程序。教育者再不转身,就不只是误人子弟那么简单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实行了将近一千四百年,出了无数状元,然而他们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绝大多数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已。
窃以为,教育改革的最大问题首先就是去行政化,让教育回归社会,回归教育本身。尤其是政府部门不要动辄用行政权力,对学校指手画脚。其次是使教师和学生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建立科学的评估制度,促进学生个性发展,跳出功利主义的泥坑,让学校真正成为所有孩子公平、快乐、成长的平台。文化永远比制度重要,也永远比知识重要。
特别是改革当前以分数为唯一的评价标准的单一模式。现在的招生模式,就像森林里召开动物运动会,本来动物各有特点,有的能跑,有的会跳,有的善飞,有的擅长潜水,然而,比赛就只比谁跑得快——一把尺子一个标准。这样看起来严格统一标准,一视同仁。但这样的公平显然是一种伪公平,它忽视了个性和差异,用表面的公平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公平。(《中国教育的出路》何良仆)
作业之殇,伤的是人的灵性。如果达尔文和爱迪生当年也要每天做这么多作业,我们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老师文章写意深刻,给人思考!敬茶明乔老师,期待更多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