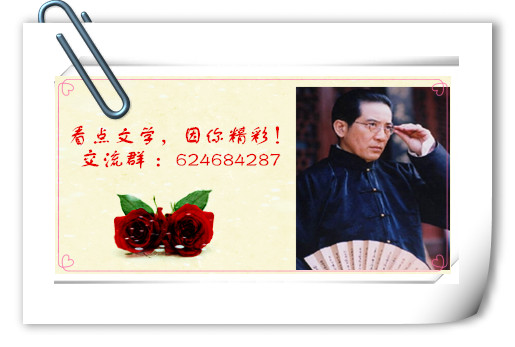【看点·春韵】爱他生计资民用(散文)
【看点·春韵】爱他生计资民用(散文)
![]() 在我的家乡,每到春天来临的时候,虽然也有“万紫千红”的小打小闹,但总归没有形成规模,唯独家乡的原野,一片连着一片,组成了集团军群似的“金黄”,铺张和集结着全世界的黄。城里的人,看惯了人为的纤“手”弄巧的盆栽和花圃,便去乡下感受着广袤无垠和铺天盖地的大自然的杰作。
在我的家乡,每到春天来临的时候,虽然也有“万紫千红”的小打小闹,但总归没有形成规模,唯独家乡的原野,一片连着一片,组成了集团军群似的“金黄”,铺张和集结着全世界的黄。城里的人,看惯了人为的纤“手”弄巧的盆栽和花圃,便去乡下感受着广袤无垠和铺天盖地的大自然的杰作。
与我同来的,不仅有前来郊游的红男绿女和老人孩子,还有成群结队的蝴蝶与蜜蜂。最善于捕捉大自然信息的昆虫们,自从第一朵油菜花从青翠的油菜茎上绽放,它们就到了。蜜蜂“嗡嗡”地飞着,发布着神秘诡异的信息,蝴蝶沉默不语,扇动着美丽的翅膀,在每一朵花儿上寻寻觅觅。
油菜花儿开了,开在融融的春风里和暖暖的阳光下。田野里,金灿灿的,这一片,那一片,最后连成广阔的一片。如同有人把黄色的染料泼在巨型的画布上。
油菜花很早就成为观赏花了,古人有很多写油菜花的诗作流传于世。但形成规模的还是当代,有些地方把油菜花作为旅游的景点,用它的天然本色来换取游人兜里的钞票。农作物几十种,能开金灿灿花朵的唯有油菜花。
作为农作物,它们的本质是给人类提供粮食和油料。油菜花,则是春天与众不同的给予。它在坚持“宗旨”的实用价值外,还给人类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不能不说它们是人类的“闺密”,是最善解人意的朋友。它们的一生,都在为人类服务。著名作家孙犁有一首诗概括得非常精确:
“凌寒冒雪几经霜,一沐春风万顷黄。映带斜阳金满眼,英残骨碎籽犹香。”
秋末,农人把它们撒播在泥土里。当冬天来临时,它们绿色宽阔的叶面,便抖擞在寒风中,帮助苦难年代的人们度过恐惧的“春荒”;而在温饱富庶的岁月里,它们则努力不被人们遗忘。人们用它们作为火锅的食材,攫取它们的叶绿素和维他命,改善心脑血管疾病和肠胃病。可以说,你贫穷,它们是你库存的“隔夜粮”;你富裕,它们是你血管和肠道的“清道夫”。正因为如此,农人们才把油菜撒播得相当稠密,为的是,可以不断地“间苗”。小时候,主粮不宽裕,晚上的一顿饭,就吃油菜。把油菜用锅煮熟,和上高粱面,这顿晚餐就对付过去了。现在富裕了,我们家在冬季还有吃油菜的习惯。不过,不是对付一顿饭,而是用油菜“涮火锅”了。
油菜作为农作物,与水稻小麦不同,它们不需要大量施肥,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它们也不“择良木而栖”,不在乎高低不平的土地。播撒到哪里,就能在哪里生长、开花、结子。给人们带来可观的收益。更让人赞叹的是,它们对季节的“敏感度”低。早种、晚种都有收获。不像那些主粮,种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1968年,我的家乡曾遭受特大洪灾。洪水消退后,只能种晚秋作物。晚秋作物收了,立即种上油菜。在严冬里它们也同样隆重地生长着,一任霜打雪压,供灾后的人们随取随吃。此时,几十种农作物,只有它们还在严寒中努力壮大自己。
油菜开花是很早的。“清明节”还未到,它们便成为“战地黄花”了。油菜花是油菜的“颜值”,也是它们的少女时代。不仅“招蜂引蝶”,还“勾引”着“高级动物”。正因为如此,某些地方才动用行政手段,号召农民大量种植油菜,用博大恢宏的气势来掏“游客”的腰包。
朴实而娇柔的油菜花有一种集体的力量。在油菜花盛开的乡村原野,太阳照在油菜花地里又蒸起若有若无的金黄色的水汽,连蓝色的天空也被油菜花熏染得金灿灿的。只有油菜花才能最大面积地尽情地表达着春天,展现着春天的胸怀。不思归窠的成群结队的蜜蜂贪婪地地飞翔在油菜花的花蕊上,它们要把这无与伦比的博大储存在甜蜜里。如果,孤零零的一茎油菜花,生长在路边,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倘若长得不是地方,农人还要毫不客气地将它像野草一样拔掉。而连成海洋似的无边无垠的油菜花,就极具观赏价值了。也就是说,油菜花天生就不是孤芳自赏的“公主”,而是依靠群体的同气连枝来赏心悦目,在花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么壮观的宽广面前,无论多么孤独寂寞的心情都会变得舒畅而充满热情。融入社会、参与集体将成为迫切愿望。
油菜的花期相当长,人们可以从容地赏玩。花期一过,就等着收获了。这也不同于别的高贵的花儿,姹紫嫣红了一阵子,陷入沉寂。花儿谢了,或枯萎在枝头,或“零落成尘”,便无人问津了。而油菜的花期一过,便更具价值。油菜籽的含油量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五十。油菜籽油,是人们喜爱的油料。乡下做“卤锅”的,必用菜籽油,这样卤出来的肉食,才能色香味俱全,成为人们舌尖上的宠物。炒菜、油炸食品,风味、品相很有特色。尤其是在食用油市场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农民更热衷于种油菜了。把油菜籽往油坊里一送,清亮的油就出来了,吃了放心。现在,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多数都是去乡下直接购买油菜籽,再拿到“油坊”里榨出货真价实的油品。为的是吃个健康和省心。现在,农民们已经没有储备粮食的习惯了,收割完毕,就把粮食拉到粮管所卖掉,但储备油菜籽的人家却有增无减。
说油菜一生的各个阶段都在为人们奉献,是毫不夸张的。正因为如此,乾隆皇帝才有了一首倾情讴歌油菜花的诗作《菜花》:“黄萼裳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新油。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