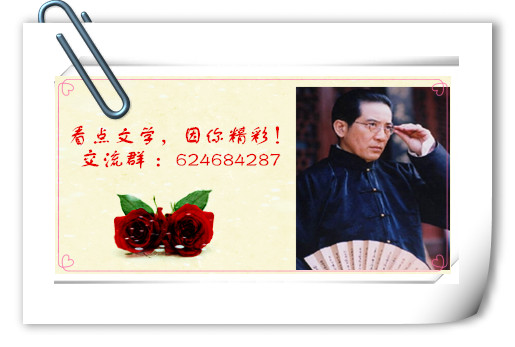【看点·春韵】我的山东哥们(散文)
【看点·春韵】我的山东哥们(散文)
一
我有许多山东哥们!女的倒没几个,因这,感觉有点对不起自己的尊容,更有点没有炫耀的资本了。
年轻时,媒人介绍了个山东姑娘,当时只怪自己眼拙,拒绝了人家。试想,事成了,那该是怎样的人生呢?人嘛,总是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这就不奇怪了。
我这辈子结识的山东哥们贯穿南北各地,横行东西乡里!同学,同村,同乡,以至邻居也曾是的!
打小学三年级吃了同学拿的山东煎饼,感到这食物咋就这么好吃!然后又吃了他们的小虾米,那个香啊,终生都很难忘!特别是用链条做的枪,见了真是爱不释手,两眼盯的放光,见我这可怜样,顺手给了一把,那可是我最得意的玩具。我那小木猴,折四角,铁桶圈都回赠了他们!看他们拿来的小说,真是过足了瘾……我和这些山东哥们的结识,是最快乐的日子,最难忘的时候。以至高中到这些同学家,见了同学妈妈也亲,见了同学哥哥也亲!同学妈妈做的绿豆馍也香,大碗菜也香……
“山东帮,帮山东,顿顿吃饭摊煎饼!”同学们很是调皮,见了山东同学就是爱喊。这些同学听了不吭声也不在乎,甚至毫不在意笑笑,我听得刺耳,挽起袖子有干架的样子,被班长拉开了。他们来自北岭和东荒的小村子,个个衣服跟身材很不搭配,长的长,短的短。也许是哥哥穿了弟弟穿,姐姐穿了妹妹穿!破破烂烂,油油腻腻,这是他们帮家里做活闹脏的。他们一块说山东话,呱啦呱啦快的一点也听不懂,转身说当地话也挺顺溜的。
二
也许是山东煎饼那种甜甜的,有点酸奶味道的诱惑,总爱和山东同学黏在一起。
星期日,有个叫王强和孙哲的同学跑了几里地扛着捆绑了沙布的网杆,屁股后边跟了一群小伙伴喊着叫着,前呼后拥,约我一起下河,说是捉螃蟹,摸鱼,捞虾米。
一伙儿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向清浴河走去。山路弯弯,碎石坎坎。山坡上吃草的羊群似云团片片,河岸的草坪上牛儿在啃草 ,有的撒着欢 儿,又是甩尾,又是喷着响鼻,好像在欢迎着我们。河水清清,潭水中的鱼群,散开一片,又聚在一堆,倏然逝去,河面上留下细细的波纹……水草丛也有小小的虫儿钻出来在水面上来回飞跑。一堆一片的被网了上来,虫子!虫子!谁在叫喊,不是!不是!这就是虾米!这就是虾米,会飞跑的虫子!
星期一,王强拿来了小虾米,那儿敢吃,试着吃了,真香!自行车链条做的手枪,用皮筋做的拉簧,再有一根火柴就能打响,谁的发明?摸鱼捉蟹,捞虾米,做手抢,心里很佩服,他们真了不起……
这些哥们拿来《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红日》《播火记》和一些有前言,没后尾的小说,使我废寝忘食,许多认不得的字,只认半边偏旁,以至现在认字也只认偏旁提手,闹出了很多笑话。数学更是马马虎虎,荒废了学业,失去了上大学当官的机会,就是想当个文字自由职业者也难以胜任。倒是这些哥们小时的淘气,好玩,爽快影响了我,再到大了结识更多的山东哥们,那豪爽,真诚,实在,顽强,好学,向上的品格影响了我。假如交住的是河南籍的哥们,我一定是个狡黠聪明,满脸狐疑又十分灵动多虑的人!
三
一日,父亲让我到北岭村打点醋去,常听人说他们都是山东人,做豆腐和醋都是用涝池水做的。想到我同学,有的穿的被鼻涕沫得发亮的衣服,有点犹豫,想想能和王强和孙哲玩,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天还没有黑下来,就对父亲说,我在同学家呆一晚,明个回来!
到了北岭村,很快找到了李强孙哲。
这北岭村不大,北高南低,台阶形分布,一个台价就是个高坎儿,人们依这土坎挖深,又开掘窑洞,窑洞面南,十分向阳,东西一字排开,散落着五六户人家,一个坎儿一个姓,也就是张,王,孙三个大姓氏族。他们都是二十年代左右先后逃荒来到这儿的。也许这个坡地原是个荒草坡,贫瘠的无人问津,这些山东汉子从此在这地方落了脚,刨出了地窑窝窝,驻扎了下来,开荒种地 ,散播种子,艰难的生存了下来……
王强就在村南坎的中间一个半明半暗的院落。几孔窑洞,中间一个有门,两边都是没门敞开口的门洞,挂着麻袋片儿遮挡着,西边一孔窑洞是醋房和豆腐房,用泥土坯垒了半截,常年烧柴草的缘故,被燻得黑漆漆的,场畔上堆满了柴火。
进了作坊,我好奇的看着:一个大锅靠窗,后边是个小石磨子,另一边是大小几个瓷瓦缸,其中一个小缸用木架子撑着,缸底一个小眼儿流着醋,窑里散发着一股特殊的味道,我提这问那,王强一边告诉,一边拉着我做示范……
这一切都好奇好玩,整个下午都是在快乐高兴中度过的!
晚上,和王强睡在炕上,没有褥子,苇席光溜溜的发着油光,煤油灯照着屋子,虽暗而亮,火苗儿冒着黑烟。忽然,我被炕角的一堆书籍吸引,什么书都有,物理化学,数学语文,俄语,历史地理,还有许多写过去的作业本,我齐齐翻了过,发现本子的字十分漂亮,对两本地理历史书有了兴趣,放在一旁,想借下明天再看。小强说:“这是大哥的,他书念的可好啦,本应能上大学,他报考了师范,为的是减轻父亲负担,好让我和二哥继续上学!”我问:“那你二哥呢?”王强自豪的说“他上高中!他学的可好了,是学校的尖子!”
不知和王强说了多久,我不知不觉睡着了,好像在做梦,周围全是书,我不知看那一本才好!突然被一阵响声惊醒,好像是铁桶倒水的声音,屋子黑乌乌的什么也看不清,窗外有一丝亮光,好像是月光,一阵脚步声,好像俩人的,咣噔,咣噔的走远了……有点害怕,伸手去摸王强,没了人影,他那去了?胡思乱想的又睡着了……
一个鸡叫,一群鸡叫,一村鸡都叫起明来,我知道天明了,睁开了眼睛,天己亮了,还没见王强回来,穿好衣服走出屋子,发现王强和父亲挑着水从西边回来了,王强挑了两个半桶,额上满是汗水,头上冒着是热气,他俩把水倒进缸里,清亮亮的。
“起来啦!”王强用手抹着汗,不好意思的打了招呼。
“这么早,那儿去担水?”我问。
“斜坡河!”
“就是清峪河!”我太吃惊了,要走二里平路,再下坡,来回十里路里。看样子父子俩挑两回了!
“没有水窖吗!这太累了!”我对王强父亲笑了笑说道。
“不累!不累!”王强父亲说着,放好了扁担,解下了粗布腰带,又重新紧了紧。他是个红脸大汉,身板十分硬朗,声音很是响亮。用山东音调说着当地话也十分好听:“他大哥师范就毕业了,二强和王强再考上,我下点苦都值得!娃些念书才有出息!”王强见父亲又想说自已要好好念书的话,赶快说:“院里这口窖根本不够,不知啥时才能放水,河边的泉水做豆腐做醋最好啦!豆腐白漱,醋味馨香!”
王强母亲不知啥时早已做好了饭,招呼着,看来又要吃上煎饼了……
那时候看电影《南征北战》见到山东大妈给子弟兵做煎饼;好像是王强的妈妈在做煎饼!看《红日》小说,山东父老乡亲为解放事业所做的牺牲!什么“闯关东”呀等等,有关山东大汉,好像就是王强父亲的样子!我又找了许多描写山东人和事的故事来看,这些故事深深感动着我!心想,我是个山东人多好啊!
四
上了高中,才知道世界之大,全校四邻八乡的学生都有,班上原籍是山东同学也不少。不几日便又结识了于杨和孙林等同学,才知道是移村和坳底村的。这两村和北岭,东荒村基本在一条等腰线上。
王强也上得高中,拿的是二哥的铺盖卷,虽己很旧,但还凑合,只是背的干粮全是高粱面做的窝窝头。孙哲是独生子,铺盖和衣服都是新的,背的蒸馍是麦面和玉米面二合一。只是新结识于杨更差些,铺盖卷又小又薄,罩面己洗的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一不小心光脚就会蹬破,想必已用的很久了,他的馍更奇特,是青绿色的,不是菜馍的那种。我十分好奇,要来吃,感觉挺好吃的,说起来才知道是绿豆面做的!
于杨瘦瘦,高高的个儿,脸颊也瘦瘦的,留着平头。从脸到头咋看都像“鲁迅”样,我们都叫他“于鲁迅”!
名也付实,他分析解剖数理化之透彻外,政论性文章更是深刻,有据有理,入木三分;讲起话来,伶牙俐齿,引经据典,辨证而富有哲理,佩服之处,心存敬意,成为知己。
星期天回家,于扬顺道领我去了他家。
一条东西胡同,南边是一个好大的地坑院子,住了好几户人家,院中心是个雨水池,旁边有一小丛竹林,有粗粗的葡萄藤蔓被木椽撑着,窑洞开挖的很随意,大的大,小的小,是每户人的需要吧!
于杨的母亲见了很是热情,用手撩了撩白发,仔细打量着我,我见到她很眼熟,在那儿见过?哦!这不是电影上的山东大娘吗,瘦高个,灰白的头发,兰色的补丁衣服,明亮有神的眼晴……大娘热了绿豆馍,滩了煎饼,炒了几大碗菜,盛情的招待于杨这个同学,我们明白,这是大娘把家里尽有的好吃食全端了上来……
于杨兄妹八九个,是个大家庭了。大哥,二哥,三哥见于杨引了同学回来,都凑一块聊天,弟弟妹妹们也涌到一个屋子,你一言我一语什么都谝,国内国外,谈古论今,我挺佩服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
恋恋不舍告别于杨和他们可爱的一家人。上了场畔,我眼前是一排排参天大树,我惊呆了,这全是杨树,粗壮而有立,直直的向上耸立,不知是于杨的父亲栽的,还是爷爷栽的,它牢牢的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