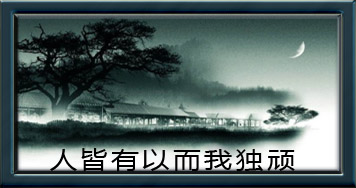【流年】苞米皮(散文)
【流年】苞米皮(散文)
![]() 县城,大概是中国最低级别的城市,身份有点尴尬。乡下人称县城为城里,而大城市的人却把县城也称为乡下。都不无道理。县城就是在乡村田野之中,硬撑出来的巴掌大的一小块地方。出门走不上几步就进了农田,就听见了乡村的鸡鸣狗吠。小县城——摆脱不了一个“小”字。盖上几栋楼,学学大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这虽然与乡下有了区别,但与大城市还是有着几杆子的距离。居住在县城里的人,不管如何努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却总也挣不断扯不开与乡下丝丝缕缕的关系。
县城,大概是中国最低级别的城市,身份有点尴尬。乡下人称县城为城里,而大城市的人却把县城也称为乡下。都不无道理。县城就是在乡村田野之中,硬撑出来的巴掌大的一小块地方。出门走不上几步就进了农田,就听见了乡村的鸡鸣狗吠。小县城——摆脱不了一个“小”字。盖上几栋楼,学学大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这虽然与乡下有了区别,但与大城市还是有着几杆子的距离。居住在县城里的人,不管如何努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却总也挣不断扯不开与乡下丝丝缕缕的关系。
比如一个很小的细节——县城里的人较少到外面买饭吃,多数是自己做。北方人喜欢吃的主食:馒头、包子、发糕等等,更是要自己在家里蒸。而蒸饭食时,不是像大城市里的人一样用蒸布,是和乡下人一样,用苞米皮。
从“苞米皮”这称呼上,也证明县城里的人的一条腿还没有彻底地从泥地里拔出来。大城市的人文明,说普通话,称呼苞米的正式学名——玉米。
苞米皮就是苞米生长过程中,从抽穗开始就一直紧裹在苞米棒子上的皮,有好几层,呵护着苞米棒子的整个成长过程。到苞米棒子长大成熟、籽粒饱满后,就失去了作用,成了农人收获苞米时的麻烦、废物。
说是废物,倒也不是一点用处没有,最起码可以用来做烧柴,取暖、做饭。在乡下,是不存在真正的废物的,万物自有有用之处。在物质贫乏的时代,作为下脚料的苞米皮曾经为生活窘迫的乡下人带来过极大的益处——内层的白白的,可以编草辫,做蒲团、提篮之类的日用品,或者做成花鸟鱼虫之类的工艺品,都是可以换钱的。往往日常的油盐酱醋,孩子上学的铅笔、写字本,甚或过年的新衣裳,都会从苞米皮上得;片张较大、完整的,用来蒸馒头、蒸窝头、蒸包子用,有时候也可以当做包装纸用,是居家过日子不可或缺的东西。
现如今,编草辫的早已经销声匿迹,乡下人也用上煤气灶、电磁炉、暖气之类的城里人用的东西,苞米皮连烧火的作用也失去了,真正成为丰收之后的多余了。但是,替代蒸布的作用却没有消失,甚至随着人们对返璞归真的追求,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趋势。
用苞米皮蒸饭,有许多好处——其一,易得,不花钱,本身就是废物再利用。其二,方便,这也是第一条衍生出来的,用完了随手一扔,不心疼,不必像蒸布一样还得洗干净重复使用。尤其在乡下,比如在山上吃饭,没有水洗手,可以把揭下来的苞米皮像纸一样包着馒头或者包子吃,这时候,苞米皮就充当了包装纸的角色;还有,从热气腾腾的锅里往外拿蒸好的饭食会烫手,你就可以捏着苞米皮往外拿……其三,味道好,味蕾发达的人会品出饭食里的田野的芬芳。其四……
我住在县城里,一只脚结结实实地踏在农村。当然也用苞米皮。母亲给的。
母亲已八十挂零,独自生活在乡下的老房子里。不是我不孝顺,不接了母亲来享受城里人的生活,是母亲喜欢住乡下。母亲说,住在城里的楼房里,出门不认得路,也没个认识的人;我们得上班,剩下她自己一个人呆在屋里,和蹲监狱差不多,不如在老家热闹乐呵,只要自己还能做饭吃,就绝不拖累我们。仔细想想,也是。母亲除了年轻时出了过头力,落下腰腿不好的病根外,身体没有大毛病,拄着拐棍,是可以出门晒太阳、和街坊邻居聊天拉家常的,甚至还能给我做点咸菜什么的。当然也包括给我弄苞米皮。
我知道,人老了,就怕拖累儿女,怕在儿女眼里成了没有用的累赘。往大了说,这似乎还包含着个人尊严的问题。所以我也就坦然地接受母亲的劳动成果,做出欣喜的样子。其实,我根本吃不了那么多咸菜,用不了那么多苞米皮,多数是带回来分给了同事、朋友。他们都很羡慕。
母亲似乎对弄苞米皮更上心。如今的乡下,大多种果树,我的家乡就是以“果都”而扬名,种苞米的很少了。母亲从春天就开始,和老太太们聊天时,关注村里人对田地的播种安排。谁家种苞米了,老早就和人家打招呼——秋天收了苞米时,她去剥苞米皮。种苞米的人家也很认真地承诺,而且,果真都会特意登门告知母亲。母亲就乐颠颠地拄着拐棍约上几个有相同期望的老太太,到收苞米的人家去。主人常常备了茶水、水果招待她们。因为这省去了主人的许多劳动,是两厢欢喜的事情。秋日灿灿的阳光底下,几个老太太围坐在苞米堆旁,不紧不慢地剥着苞米皮,边嘻嘻哈哈地开着她们自己以为好笑的玩笑,聊着家长里短,场面很是温馨。
国庆节放假回老家。母亲包了我爱吃的荠菜包子。我习惯地要拿碗,母亲说,吃包子用啥碗,于是,我就像小时候一样,用苞米皮包着吃。香。
母亲笑着看我吃。在聊了几句前后不搭的话后,讪讪地问我:
“卫啊,妈问你个事呗?”
“嗯。”
“要是有一天,我走了,这老房子,你是继续留着呢?还是卖了?”
我咽下一口包子,说:“妈,您说什么呐!吃饭呢!”
母亲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怕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今年八十出头了。咱们老蔡家,还有你姥姥家,从老辈子就没有一个人活到八十岁的,你妈我也算是老寿星了,知足了。不是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吗?早晚的事,也不用避讳。前些天,老李家的儿子,就是比你大两岁的、在烟台上班的那个大林子,回来把老房子卖了。我问问你,等我走了以后,咱这老房子,你是留着?还是和大林子一样,卖了?”
我不假思索,说:“不卖。”
母亲如释重负一样,笑了,紧着说:“对呢!对呢!咱不卖!老房子怎么能卖了呢?老房子卖了,就是把村卖了!把根卖了!”又说,“咱家这老房子结实着呢!再过个几十年也不会坏。当初和你爹盖这房子时,那木料、砖瓦,都是用的最好的,木匠请的是王家庄的王木匠,瓦匠请的是上口村的疤脸刘,都是咱这十里八村里最好的手艺人,可是费了不少的劲呢……”
母亲似乎受了鼓舞,待我吃饱后,拄了拐棍带我往西边两间空屋去,说:“卫啊,你来,妈给你看样东西。”
老房子共五间,母亲住东面三间,西面两间用来盛放杂物。在靠西墙处,并排着四口硕大的泥缸。有两口缸的缸口被绑上塑料纸封住了。我知道,其中的一口大缸,盛放的是我从上小学开始,直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课本,参考书,笔记本,甚至作业本、练习簿等等带有我写的字的东西。我曾经要把这些劳什子废纸卖给收破烂的,因为我虽然读了大学,也没能免得了下岗再就业的命运,看见这些让我寒窗十年的玩意就郁闷。母亲却死活不让卖。这是母亲的骄傲。因为我是我们家族第一个“读书人”,念过“大书”的人。母亲带着点天真的神秘,指着另一口封着的大缸让我打开看看——解去绑塑料纸的绳子,里面是草木灰,灰下面是牛皮纸,纸下面,竟然是满满一缸苞米皮!
“这大缸真好呀!一口缸就能盛二百斤粮食,上面盖上牛皮纸,再盖上灰,封起来,多少年都不会坏,也不生虫子。还记得吧?这几口缸是你八岁那年冬天,你爹去黄县的窑厂买的。你爹推着小推车,带着干粮,早上起五更就走,半夜才回来,道太远呀!小推车一边绑一口,四口缸,你爹连着去推了两趟,可是吃了大苦呢……”
我说:“您弄这么多苞米皮干什么?”
“留着给你们用啊!”
“哪用得了这么多?”
“怎么用不了?日子长着呢。眼看着成成(我儿子)也快成家了,不也得用?……今年春上,你五奶奶老(死)了,给闺女攒了两缸苞米皮呢!我寻思着,趁我还能动弹,给你们把这三口缸都攒满了。唉!现在种苞米的越来越少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攒出来……”
我张嘴刚想说“成成他们年轻人还不知道用不用呢”,忽然就觉得心头一热,就把话又咽回了肚子。
午时的阳光透明热烈,从老旧的窗户、敞开着的门照进来。老屋子亮亮堂堂。
对儿女有用,让母亲活得很有尊严。
祝福母亲健康快乐,福寿绵延,让我们好好享受做母亲儿女的幸福吧。
文章的布局谋篇颇为讲究,情节、思想环环相扣,最后落脚在三大缸苞米皮上,不仅作者感动,作为读者,我也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