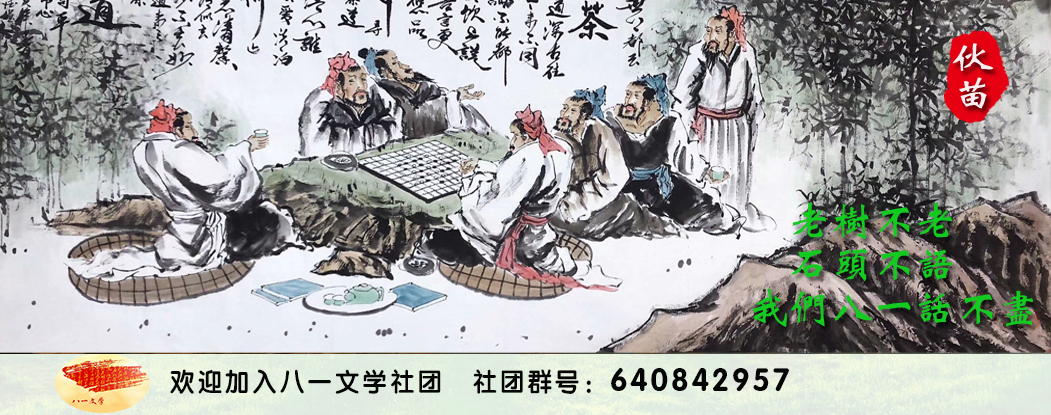【八一】那贫穷年月里的亲情(散文·家园)
【八一】那贫穷年月里的亲情(散文·家园)
![]() 一
一
一天中午,我和二哥出村外的莜麦地里捉叫蚂蚱,在街上碰见四老爹正要回家,问我们大热天的去干啥?他听说我们出野外贪玩儿便说道:“晌午村外没有人,注意庄稼地里有狼。走吧,回四老爹家歇歇凉。”
在我们家乡,晚辈对父亲的兄、嫂称呼为“老爹”“老妈”。按排行,最大的叫“大老爹”“大老妈”,为二的叫“二老爹”“二老妈”。隔了三代以上的父辈的兄长、嫂嫂分别称之为“大爷”“大娘”,没有叫“大伯”“大妈”的。
四老爹把我们引进家。他们住着五间土窑洞,堂屋两边排放着几个泥瓮,中央摆着一张供桌,上面放了一个木制的神龛。从颜色看已经多年,里面供奉着一尊神像,头戴古代官帽,大红脸,又黑又长的胡须,身穿盔甲,手拿一把长柄大片刀,前面摆着蜡座和香炉。村里人们叫财神爷龛儿。这是他们家的一件珍品,供奉财神祈望发财,就是四老爹唯一的儿子——我的堂兄叫的名字也有个“财”字,可以看出他们家也是穷怕的,求财神保佑,盼日后发财。
四老妈在食堂帮锅还没有回来。四老爹把我们引到堂屋进了家,从桌子上端过一个碗,里面有一块儿用黑豆、玉米面混合做成的饼子,饼子下面有几个像核桃一样大的山药蛋和一些山药蛋皮。他拿起豆饼一分两半送在我们弟兄俩手中,说:“晌午肯定你们没吃饱,把这点饼子和山药蛋吃了吧。”
我手拿豆饼,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顾不上品滋味便吃进了肚,接着和二哥抢着把碗里的山药蛋和山药蛋皮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四老爹看着我们饥不择食,吃得是那么香甜,脸上挂着一丝丝微笑,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表情,像是可怜又像是心疼我们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熬到啥时才能填饱肚子?”
吃完四老爹家里的半块豆饼,好长时间回忆起来还那么润,那么香,那么甜。直到后来家里吃上白面、大米,在饭店里吃着地上走的、天上飞的和水里游的,都品尝不到像那半块豆饼的可口味道。我曾经在家里也试着蒸过豆饼,怎么吃也不合口、不入味,这就奇了怪啦。难怪人们说,饥饭甜如蜜,饭饱蜜不甜。
十几年后,四老爹身患重病,我曾多次前去看望。去世那天,我瞻仰了老人的遗容。出殡那天,我手拄着柳棍缠着白麻纸的丧棒,穿着全身白布做成的孝衣,和其他兄弟侄辈排成一行拉灵时,想起他老人家给吃半块豆饼时的情景,眼里不禁流出热泪,并痛声大哭:“四老爹,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
日后每到清明节给父母及祖辈们扫墓的时候,我给父母坟前摆上的供品最多,烧得纸钱最多。再接着就是在四老爹坟前要多上点香,烧点纸,摆点供。四老爹生前爱抽烟,我每次点燃一支香烟放在他的坟前,以表达对老人家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有时家里吃饭看到孩子们挑三拣四,我总要和他们讲起半块豆饼的事儿。以此教育和告诫下一代,在生活富裕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曾经的贫穷和饥饿!
二
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吃完饭到秀英姐家叫上外甥搬喜子一起去学校。有一天中午经不住硬劝吃了秀英姐家的五个油糕,惹得母亲训斥了一番。
秀英姐是四老妈的闺女。四老妈前夫因病去世后,带着孩子改嫁到四老爹家里。秀英姐没改姓,一直姓张。不到二十岁嫁给本村郝家为媳。
在村里,我们姓温的是小户人家,虽然秀英姐和我们不同姓,但在家族堂弟兄姊妹中,因她年龄最大,是我们同辈共同称谓和尊重的“秀英姐”。
她的长子搬喜子和我同龄,从小学到初中是一个班的同学,我们又住得不远,去学校时总是形影不离,不是早晨他起得早去叫我,就是我吃饭快去叫他。
秀英姐家里虽然不是多富裕,但不缺吃少穿,早晨山药蛋小米粥、中午玉米面馍饼、晚上玉米面糊糊,一日三餐还是有的。比起每天饥一顿饱一顿、晚上连口玉米面糊糊也喝不上的我家,还算是富裕户。每到秀英姐家叫搬喜子一起上学时,看到他们有吃有喝十分羡慕。
她知道我们家的贫困,在她家里也经常让我吃饭。我想人穷不能志短,每次以“我刚放下饭碗,一点儿不想吃”的谎话婉言谢绝,其实嘴里早就渗出口水,想吃而又不好意思吃,心想啥时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由于秀英姐劝吃的缘故,我一般不进秀英姐的家,尤其吃饭时更不进去。用母亲的话说,人家在炕上吃,你在锅边站,那叫“巡门子”。我从小懂的“巡门子”是嘴馋。因此,我叫搬喜子上学时总是站在秀英姐邻街的院墙外喊一声,院子里也是很少进的。
一天中午,我吃完饭又到秀英姐邻街的院墙外叫搬喜子上学,秀英姐让我进去。我说:“叫喜子快吃吧,我不进去了。”
秀英姐说:“你进来,姐问你几句话。”
我信以为真,进了秀英姐家。
她们一家人正在吃饭,秀英姐在地里忙着端上端下,搬喜子不上炕站在地上端着个碗吃饭。炕当中放着半盆油炸糕,大人、小孩坐在炕上围了一圈,都在忙着吃饭。
只见秀英姐夹了满满一碗油糕端着捧在我的面前。
“你快吃吧,刚炸出,热乎着呢。”
“秀英姐,你吃吧,我在家吃过了,不想吃。”
“不要说了,赶快吃,五婶家孩子多吃不饱,更吃不上油糕,你快吃吧!”
“我吃饱了,不想吃。”
“甭哄姐了,吃完这几个姐再不给你夹了。”
“我真不想吃。”
她把一碗油糕放在我的胸前硬是让我接住。一看秀英姐硬劝的样子,我只好接住碗吃了起来。
我先夹了一个菜馅油糕,一口几乎咬掉半个。嘴里不停地吃着,眼睛还盯着另半个。不知不觉地吃了五个油糕。秀英姐还要给我碗里夹,我硬是不好意思地推脱了。这时喜子也吃完饭,我们一起出来去了学校。
走在路上,我边走还边想着秀英姐的油糕,要是在自己家里,再吃几个也不成问题。不知为什么越是贫穷越能吃饭,更不知自己到底有多大胃口。
傍晚放学回到家里,我如实地将中午在秀英姐家吃油糕的事向母亲作了汇报,挨批受训这是预料到的事。母亲说:“以前咋和你们说的?说破嘴也不听,我最怕人家正吃饭,你扒在锅边等人让着吃。”
“我在街上等着喜子,是秀英姐硬叫进去的,我也不知道进去有啥事。”我分辩道。
“晌午正是吃饭时候,叫你进去能有啥事。”母亲说。
“她让我进去说要问几句话。”我想把当时的情景解释清楚。
“进去叫你吃你就吃?好像死了爹妈的没有教养。”母亲不容我解释。
“进去就进去,吃就吃,一个姐姐家过分讲究有啥意思?说一说让他知道就行,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父亲听的已经很不耐烦,插话道。
“看你这个人,小孩子就惯他天天巡门子,你不说还嫌别人说。”母亲埋怨父亲一句才算停止训斥。
以后,为了不惹母亲生气,也为自己少惹麻烦,我再没因为吃完饭叫搬喜子一块儿上学进过秀英姐的家门,再没因为所谓饥饿“巡门子”端过秀英姐的饭碗,但没因为自己参加工作离开家乡忘记过秀英姐的恩情。
三
二哥结婚不久,批了宅基地碹了三间土窑洞,开始和我们分开生活。按照父亲的安排,我们要分家。吃过早饭,家里邀请的宾客陆续到齐。
二舅来了,他顾不上出去放羊,提着水烟袋和羊腿骨做成的水烟锅来得最旱。他是母亲的堂弟,兄弟中年龄最大,辈分最高,是娘舅中的代表;表兄来了,他是母亲的亲侄,代表着母亲娘家里的至亲;姐夫郝满仓、妹夫郝所先、奶哥郝希顺来了,他们是按各自的身份而被邀请的。
炕上坐的、地上站的、堂屋蹲的,把整个家变成了十分拥挤的会议室;抽水烟的、吸旱烟的、叨卷烟的,把整个家笼罩在一片烟雾中;大嫂抱着孩子,二嫂倚着柜子,在堂屋里等待和静观着会议的开始……
父亲坐在炕上主持会议。
“今儿个把大家叫在一起,商量一下分家,这是迟早的事儿。继恒(长兄)结婚多年已经另过;二旦(二哥)也成了家碹了窑洞搬出居住;三子年龄也不小了,要不是家穷也到了找对象的时候。”父亲吸了一口旱烟接着说,“咱家穷,就有五间土窑和三间不值钱的西下房。依我看,西边两间窑归继恒,东边两间窑归三子,三间西下房和一间堂屋归二旦。继恒和三子每人出五十元给二旦,堂屋就归你们弟兄俩。”
父亲讲完分别瞅了瞅我们弟兄三个,下意识地在征求我们的意见。
既然早已安排,我们兄弟仨也认为公道,大家也没有异议,分房的事顺利通过。
父亲接着说:“家里也没有啥值钱的。以我看,继恒家里摆的归继恒,二旦结婚做起的柜子归二旦,没分的坛坛罐罐二旦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归三子。”
不知道父亲已经讲完,还是人们听的有点不对劲,妹夫耐不住性子先开口说:“他大舅、他二舅成家时都把院子里成材的榆树做了家具,他三舅结婚时啥也没有了。院里还有不成材的榆树,都应该给了他三舅才谁也不吃亏。”
大家都觉得郝所先说得在理,父亲没有表态,长兄和二哥没有意见,我也没有吱声,分家的又一议程顺利通过。
父亲又接着说:“继恒结了婚没带外债,二旦结婚欠下九百五十元,我已上了年纪没有偿还的能力,二旦碹了窑花钱多就负担四百五十元,三子暂时还没结婚就负担五百元。等到三子结婚时,所花费用你们弟兄三人平摊。大家看合适不合适?”
听到让我负担二哥结婚时所欠一半还多的外债,我犯了愁。民办教师年挣三百多个工分,每个工分值最多只有四角钱,每月国补民办教师工资仅有十一元,这五百元债啥时能还清?我没敢当场反对,也没有表示同意。
听到父亲提出的有些不公,在场的人纷纷提出质问:
“三子没结婚就担了五百元的外债,如果有人提亲从哪里凑钱?”
“三子年龄也不小了,不是不到结婚年龄,而是因为没钱难成家,分担上债务还找不找对象?”
“三子结婚让两个哥哥各负担三分之一,万一谁也拿不出该怎么办?”
……
大家一连串的质问,我的沉默,使分家议程受阻。人们提出让长兄、二哥发表意见。
长兄说:“只要都同意,我也没意见。就看二旦和三子吧。”我一听就明白,长兄结婚没负担分文债务,将来能不能分担一部分谁又能说得清?现在是表态又不是拿现款,因此说“咋分都行”。
二哥心理不平衡。长兄结婚父亲还债大伙跟着受穷,轮到自己结婚没人负担债务觉得吃亏,要让他发表意见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只能表态“我同意爹的说法”。
聘了姐姐给长兄娶了个媳妇,聘了妹妹给二哥娶了个媳妇,并且又都欠下债不愿自己负担。我还没有找对象,均分出聘姐妹的彩礼没有道理,但不能因为我没有结婚就让我负担兄长的债务吧?
邀请参加分家的人们为我鸣不平。明知道这样分家不公平,我又不好意思拒绝父亲。但父亲真正这么决定,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讨论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债务分割无法进行。父亲一言不发,坐在炕头直抽闷烟。大家都带着一种憋气,整个家充满了火药味儿。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时近中午一直僵持不下,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无法拿出更好的办法调停,在大庭广众面前很失面子。便心灰意冷地说道:“当家人说话不算数,我还给谁称老子,活着还有啥意思?我死了一个一个地看你们的本事。”
父亲分家分不下去以死相威胁,在场的人们都觉得自讨没趣,全家死一般的沉默。
父亲讲出这样的话,是给长兄听吗?长兄从小娇生惯养,什么事都依着他。况且今天的分家长兄已经明确表态,咋分也没有意见。
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是给二哥听吗?说不定分家前已经征求过二哥的意见。况且二哥再有看法,表面也同意爹的意见。这种表态对谁也能交待下去。
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是分明在逼我。要我负担五百元的天文数字,但不能因为没钱或负债成不了家当面伤父亲的心。况且父亲不乐意母亲能高兴吗?我只好当场满口答应,一式三份立下契约。并当下从手腕摘下刚买几天的“红旗”手表作价一百元给了长兄顶债。债务分割就这样不平等地通过。
分家结束,不少亲戚提醒父亲,这是个错误决定,都说这样只能为难我,但父亲不吭声,低着头直抽烟。也有人说我太傻,但我不能再说什么。我心里清楚,该分的分不到,不该分的推不掉,分与不分已经无所谓。自己以后找不找对象听天由命,现在是火烧眉毛——只能顾眼下,按父亲的意见办。
当时,我是为平衡父子关系和弟兄关系、为减少家庭矛盾换得父母开心,才勉强同意承担债务的,而内心里很不情愿,受着很大委屈。我总觉得父亲太偏心。后来才明白父亲这样做,一来长兄孩子多生活困难,二哥刚结婚经济负担重,把债务分担开谁都能够承受;二来父母年迈,到自己成家时没钱担心我独自担当不起,让弟兄互相帮一把。毕竟亲弟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那真是不堪回首的年代,难以诉说的亲情!
那时候物质太贫乏。半块豆饼和五个油糕,才显得弥足珍贵,亲情温暖。而分理处所表现父亲的无奈和拉扯兄弟之情。让人唏嘘。
祝您生活愉快!佳作不断!^_^

那时候物质太贫乏。半块豆饼和五个油糕,才显得弥足珍贵,亲情温暖。而分家所表现父亲的无奈、无力和有心拉扯兄弟之情。让人唏嘘。
祝您生活愉快!佳作不断!o(* ̄︶ ̄*)o
把上面我的那条评论删除吧,手机匆忙发表,评论。请温老师海涵!o(* ̄︶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