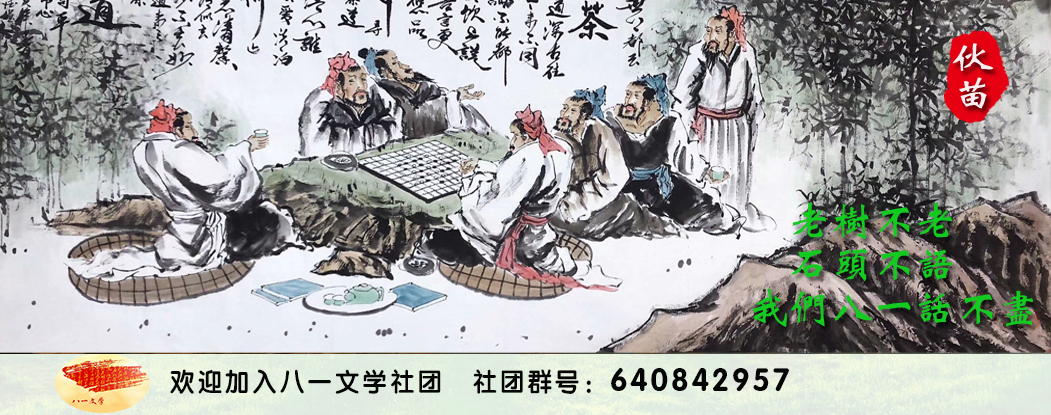【八一】刻在心底的童年时光(散文·家园)
【八一】刻在心底的童年时光(散文·家园)
![]()
我经常回忆起我的童年,童年时的生活在我心里就是天堂般美好。那时,我们居住的地方,三面环山,前面是一座水库。山清水秀,花果飘香。很小时候随全家搬过去时,那里还都是荒地,父母和他们的同辈们破草开荒,养猪种地。听母亲说,那里的土质好,是“夜潮地”,开出来以后,种出来的瓜果蔬菜长得水灵灵的。
那时候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排长长的平房,一间靠着一间,房与房是用木板隔着的。坐北朝南,住着十几户人家。房屋两旁树木环绕,一年四季茂盛葱茏。平房后面紧靠的是一座杉树山。听大人们说,那是请了安徽民工把后面山上修整后载种下了杉树。我们搬进去时,这些杉树,有的已经长得很高,主干笔直地指向天空。
春天,杉树的绿来得晚些,其他植物早已绿得恣意,叶片在春风的浅唱低吟中轻轻摇摆,一副沉醉的模样。而杉树们还是憨睡未醒的,沉浸在自己的梦境里,光秃秃的枝丫看不出一丝绿意,一点儿也不着急。春去春回,杉树已越来越高大粗壮。
出门是一道山湾,上面有一座木制桥,过了桥,便是一段小路。约莫大半里的路程,前面就是一座水库。水库不涨水的季节,旁边还有些田地,那是水库坝脚下一个村庄的,他们种些萝卜菜,荞麦一类的作物。除了那些田地外,还可看到很多青色的砖,瓦堆在那里,看上去已有些年头,听一些老人说,那里原来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后来迁移到水库坝脚下去了。这些破碎的砖石瓦片风吹雨淋布满了历史印记。
春天到来,风和日丽,每每走在路上,和煦的春风吹拂面颊,带着大山的气味,清新舒爽。即使在春雨连绵之日,大大小小的雨点淅淅沥沥,也觉得是一种有趣的音乐,无数个夜晚,就是听着这种滴答起伏的音乐安然入眠的。
春天是花的海洋,空气中、晨雾中、雨水中,满是花朵的气息。我最喜欢兰花的香。兰花,幽香,朴素,美丽,优雅。兰花盛开的季节,走过那条山道,循着淡淡香气就能找到隐在山涧里兀自盛开的飘飘幽兰。我把它们摘下来插在扎起的小辫子上。还要摘一大把拿回家插在玻璃瓶里养着,于是,满屋都是兰花扑鼻的馨香。除了兰花,还有梅花,杏花,海棠花,野桃花,含冬花(即深山含笑),杜鹃花……春天里竞相开放,一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
清明过后,有竹子的地方都有很多笋子。我小时候喜欢提着个竹篮去抽笋,不多时,就是满满一篮笋。到了芦珠(一种小型的,长圆型,吃起来带酸甜味的小果子)成熟时,我还会摘下很多芦珠带回家。笋子抽回家后,我就把那些笋子倒在地里,一会儿,其他的小孩子也会过来几个,一起剥。剥的时候,把笋子壳折起来,折成“笋壳伞”,还一个一个地穿在各个手指上,边剥边笑边玩,自得其乐。一会儿一篮笋子也不知不觉剥完了。母亲把剥好的笋子煮一下,再切碎,和在饭里面,放点盐,那时候也感到挺好吃的。我们住的平房前面是一片桃林。
初夏,那里的桃子因为自然环境的得天独厚,桃子的味道特别鲜美。家前面是个水库,水库旁九曲十八弯的小路。每到梅雨季节,水库涨水淹没山路,要坐船出行。坐在船上,能看到两边山上杨梅树上挂满的果实。这些杨梅只能在船上看到却不能摘到。待杨梅成熟后,我们就去旁边或更远的山上摘下满桶的红红的,白白的杨梅。那种白色长不红的,妈说是糯米杨梅。后来长大成家来县城多年后,我几次曾有过去那里摘杨梅的念头,但听人说那里早已荒芜,路都没有了,全被柴乱长实了。所以心里感到不能再去体验儿时的那一种生活也是一种遗憾,非常无奈。青青的山上长的那种原生态的,酸甜鲜美的杨梅只留在一生的记忆和回味里。
夏天最热的时候,也是父母最辛苦的时候。大人们都到杉树山上去搞抚育。帽子,锄头,水壶,柴刀是必带的。记得伴着蝉声一声接一声的鸣叫,我喜欢去湾里捉满身白色或青色透明的小虾和压在石底下的小螃蟹。去陇田里(外村人的)捡螺丝,在河沟的泥巴里面翻泥鳅。那时候的泥鳅真多呀。父亲经常带着铁钯,桶子,水勺等工具,去捉鱼类和黄鳝。捉泥鳅时,父亲把沟的一处作个坝堵住,再用勺子把水浇干,翻开泥巴,就看到大大小小的鱼鳅翻滚着,我用手有时在泥巴里可以捧起很多泥鳅。还有一种扁身子的叫沙鳅,也可吃。记得小时候去外婆家,我还看到过有人把鱼鳅一条条地挂在斗笠上把玩。现在花几十元买一斤的鱼鳅是饲料养的,没原来的鱼鳅美味,更比不上那种营养了。
我喜欢去流水潺潺的湾里,可以看到水中自由游弋的鲹鱼,那种鲹鱼身上有几种花的颜色,不知为什么长得那么好看?离开了那个地方以后,一直没有再见到过那种“美鲹”。父亲把它们叫做“花鲹”。记得我提着衣服去湾里洗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看着它们游来游去,看得入迷。而后还下水去想捉住它们。可是那些鱼儿非常机警敏锐,只打发了我的时间,我根本就抓不到它们。经常玩得投入,听到母亲的叫唤我才提着洗了的衣服回家去。
夏天的夜晚,父亲还经常拿着袋子和电筒去湾里照“山鸡”。有一次,我们都不知父亲什么时候出的门,回来已是快凌晨时分,照了满满一袋“山鸡”回家,大的有一斤多一个,满身油亮的黑皮。那天中午,母亲把“山鸡”用家里的辣椒和大蒜烹饪好大一碗,一家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我还端着饭碗去同伴家去吃,记得那次那个人的家里正好来了一位家住县城的亲戚,闻着我饭碗里喷香的“山鸡”味,又听我说我父亲照了一些“山鸡”,就去我家出了高价想买,无论那人怎么说,父亲一个都不肯卖。全部留给我们吃。那种鲜美的味道至今让我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听说现在这种正宗的“山鸡”要卖几百元一斤,还不一定是真正的野生的“山鸡”。
乡村生活既平实又丰富,有时去亲戚家看见有人在水塘里摘菱角藤上的叶子,把那些叶子晒干。在那个饥荒的年代,这些晒干的菱叶与粮食和着吃,可以节省些粮食。我最喜欢用长秆钩去钩塘中长了刺的鸡菱秆,上面的叶子有刺,可以剁碎煮熟当成猪食。秆上有刺,是长在皮上,剥掉皮是一种很好的菜。鸡菱球剥开里面那种圆粒的籽籽,咬开是白色而甜甜的浆汁,和现在的石榴里面的籽一样,淡淡的甜。
到了晚上,我们三五成群结伴捉萤火虫,捉后放在罐子里。那时候的萤火虫真多呀,飞得到处一片光。我们边捉边跑,口里还唱着:“萤火虫得光光,你快飞过来……”有时候四个女孩子还结伴出去照过青蛙。这种青蛙大人们都叫“花鸡蛤蟆”,满身是绿色的花花。两人一伙,一人拿手电筒照着。那时候的生态多好,田边草地的青蛙也多。没多时,一碗青蛙就照了回来。长大后,其中一个女孩后来逃婚和一个安徽的男子去了安徽。人生几十年,一直没有再见到过她。白天,表弟也去像钓鱼一样,在水塘边钓过这种青蛙。现在想想,那是一种多么有趣的童年生活啊!
到了秋天,不上课的时候,去山上砍柴。说的是砍柴,其实是想去山上玩。小时候就喜欢山和水,秋天的山上,各色的叶子,点缀着满山满岭。果子有熟的,未熟的,有半熟半未熟的。有野生的柿子,毛栗,猴枣,蓝莓子,弥猴桃等。除了自己摘,父亲和母亲也去摘给我们吃。我在家里算是最野的那个。最喜欢去山上,经常看到黄鼠狼,野鸡和小兔子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因为山靠着家很近,所以也不害怕。现在的山上别说是摘这些野果子,看这些小动物,连走的路都没有了。市场上卖的都是种植和饲养的,野生的十分稀少。
冬天,爬树,唱歌,跳房子,跳绳,打拐脚,踢毽子……是常有。到了大雪纷飞,手冻得通红,嘴里呵着气,还要跑去外面堆雪人,摔雪球,用棍棒敲打着屋子上冰冻吊着的“令珠子”。最喜欢的是围坐在父亲烧的火堆旁,映着我们红红的脸蛋儿。弟弟们小时候就是“书迷”,记得小弟看了故事后,又讲给我们听。他记性特别好,能把一个故事完整讲完。最不安分的就是我,用火钳这里拨拨,那里拨拨,把烧下来的“火钟得”又夹在“熏桶”里。大雪的天,记得有好冷,在那个山涧里,家里经常吃两餐。母亲煮的杂饭,里面放了菜,特别好吃,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的生活都是原生态的。洗碗根本不用洗洁精。每次洗碗的时候,去家的旁边南瓜墩上摘一、二片南瓜叶子,把碗洗得逞亮逞亮的。那些未放洗洁精的潲水舀在“旯边锅”里煮猪食最好了。那时候没有被浪费的东西。因为每家每户都养猪,养鸡或者鸭。家里的东西不够,甚至还要去外面打些猪草和野树,野藤叶子来喂猪。
人生啊,一转眼就是几十年。岁月面前没有人是壮士,你想让往事珍重,偏偏没有这个机会。父亲已故五年,我做过关于许多童年与他生活的梦。就连父亲带我去砍柴,用挽在颈上的毛巾时不时地擦汗的情景,还有经常在那个烂柴堆摘一种叫“八担柴”的白色的野菇,也会在梦中再现。那种野菇炒熟后味道特别鲜美。离开了那里以后,一直没再见到过那种叫“八担柴”的野菇。
许许多多童年时候记忆,虽烟尘般朦胧,却又总挥之不去,转化为甜蜜而又辛酸的回忆,常常萦绕在梦里。很多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原生态已消失殆尽。再也难以见到益虫吃害虫的那种良好的生态循环。也让现在孩子们的童年少了许多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快乐机会,就连乡下出生的孩子一到上幼儿园年龄,就由父母或老人家带着租住到县城来。除了上课时间,更多的是与手机和补课为伴,这样的童年是不是让他们的人生多了一份缺憾?
初夏时节,一场小雨过后,我漫步于山中小道,漫山遍野的野花,满目青翠欲滴的绿叶。旁边有小桥流水,淡淡的花香沁入肺腑。沉浸其中让我流连忘返。绿水青山,岁月静好。童年那些天真烂漫的往事多么值得留恋和回味。想起我曾走过的乡村,就仿佛回到了那些山水的怀抱里,心灵就拥有了一片深情和宁静。
那个山清水秀童年时的家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桃花源。
——原稿于2019年5月16日晚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