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风】有个地方叫西园(散文)
【西风】有个地方叫西园(散文)
![]() 老家的旧房子位于村子西头,出门一条僻静小路,西行约百米,有一个三分大小的园,我们管它叫西园。这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从一个苏姓人家手里买来的。栽菜,种粮,植树,在贫困的岁月里,这小园不仅滋养过我们的生命,也给我们“酿造”了许多的快乐。从春天开在篱边的小花,到冬天翘在树上的蝉蜕,从北面池塘的青蛙到南边墙根的蟋蟀,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这故事丰盈了我的童年,并刻在脑际,成为美好回忆的源泉.
老家的旧房子位于村子西头,出门一条僻静小路,西行约百米,有一个三分大小的园,我们管它叫西园。这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从一个苏姓人家手里买来的。栽菜,种粮,植树,在贫困的岁月里,这小园不仅滋养过我们的生命,也给我们“酿造”了许多的快乐。从春天开在篱边的小花,到冬天翘在树上的蝉蜕,从北面池塘的青蛙到南边墙根的蟋蟀,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这故事丰盈了我的童年,并刻在脑际,成为美好回忆的源泉.
一.西园有树
西园为东西狭长的长方形,北临一个池塘,临塘斜坡是一排高大的柳树,东南两面插着稀疏的竹篱,西边一溜茂盛的蓖麻,这些简单的屏障,与其说是为防护,不如说为美观,因为爷爷父亲都是热爱生活,懂诗书的农民呢。
走进西园,最抢眼最霸道的当然是植物。我记事时,北面斜坡上的柳树,就已高大挺拔,夏日里,树冠遮出浓荫,风过时,柳枝不时从池面掠起水滴,并四处扬撒,所以,即使是炎炎夏日,西园也足够清凉,柳树大约是喜欢安静的,可总有蝉儿栖在上面放歌,小时一直纳罕,蝉儿为啥喜欢栖在柳树上?
若说树,枣树才该是西园的主角。东西向两行共八棵枣树,树干粗大,树冠丰满,每天粗壮的汉子般站在我的面前。中秋前后,枣子熟了,圆滚滚、红彤彤、亮晶晶地挂满枝头,大眼瞪小眼地互望,任性地把甜香撒满空气,毫无忌惮地充斥着你的鼻息。这个时候,枣树是需要人看管的。奶奶便每天颠着小脚,带着同样需要看管的我,把“根据地”从家里到挪到西园。在园中间空地上,铺一领小席,摆几样吃喝,奶奶盘坐席上编着她的草帽,我则由着性子玩耍:摘野花,捉蚂蚁,捏泥人……若有人自园外小路经过,奶奶停下活计招呼人家过来吃枣,人若不肯,便打发我提着小篮子追过去送上一些。成天在枣树下转悠,难免会被青刺蛾蛰伤,奶奶便忙前忙后,用碱水为我冲洗,这办法如何管用的,已没了印象,但提到“青刺蛾”,我会立马想到小时西园的岁月,小时也一直纳罕,那些烦人的蛾虫,为何总喜欢粘在枣树上?
西园的西北角边,有几株野葡萄秧,因贪恋野葡萄的美味,对那秧每每也是眼巴巴地望着,从小苗新出,到枝叶丰满,再到秋天果实饱满紫莹,揪一颗放在嘴里,啧啧,那酸酸甜甜的滋味真是无与伦比呀。精于营务田园的父亲常给西园除草,但那几株野葡萄秧,父亲却从不触碰,留下来任其茂盛生长,我知道,那是父亲留给我的童年。一年如此,年年如此,所以野葡萄生长的日子,和我在西园的岁月一样蓬勃,一样悠长。
二.西园有屋
红绿掩映着的西园东北一角,坐北朝南有一黄泥小屋,方方正正十来平米的样子,四壁浑然一体,东西墙各开一方窗,正南面开得大些的,只能叫门了,只是半米高的门槛,我需费力才能爬上。这小屋平时放些锄镰扫把板凳的同时,也供看园人遮风避雨之用。夏日里,偶有风雨突临,我和奶奶便匆匆钻(爬)进小屋,坐在高高的土坯“门槛”上,倚着厚实的土墙,不顾奶奶的呵斥,把手臂伸进风雨里舞抓唱歌,雨腥裹着泥土的香裹着枣子的甜,充斥鼻息,润满心肺,叫人经年不忘。
冬天,万物失去生机的时候,我们也少来西园,堆放了柴草麦秸的小屋显得温暖而僻静,因此引来流浪狗猫儿休憩。颇为离奇的是,除了狗儿猫儿,小屋居然也接纳过流浪的孩子。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刚刚起床的我睡意未消,便见父亲一身寒气一脸惊喜地外面归来,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父亲说,这孩子家在四十里外的邻乡,日子贫苦,和奶奶一起出来讨饭的,昨天却不小心和奶奶走散,傍晚时,男孩凄凄惶惶地躲进我西园的小屋。今晨父亲去小屋收麦秸,发现了蜷曲着睡在麦秸里的男孩,于是领回家来。母亲端出热腾腾的饭菜,打发男孩吃饱,又找一件哥哥穿过的厚实点的棉衣给男孩套上,男孩讷讷地道了谢。后来父亲怎么送走的男孩,送到了哪里,我都不记得了,但男孩怯怯的眼神,吃饭时狼吞虎咽的样子,却深深印在我心里。同时年少的我也多了一桩心事,总惦着西园的小屋,想着什么时候会住着流浪的孩子,因此,许多个早晨,我悄悄跑到西园瞧看。
三.西园有故事
西园的中央则是一片相对开阔的空地,这片大人们用来晒枣晒草晒粮空场却做过我们的“避难所”。那年的唐山地震,毫不客气地波及而来,沧州也震感强烈,且余震连连,不少老屋歪歪塌塌,胆小的人不敢睡在家里,纷纷跑外面空地上搭起窝棚来。
父母是不怕的,他们依旧睡在屋里,但在西园空地上给孩子们搭起了窝棚,几根木头架成立体A字,四周用苇席、苫布、塑料遮严。一个简易结实严密安静的窝棚成了几个女孩的快乐之所,我和姐姐,还有另外三个堂姐,五个女孩数我最小,夹在中间,四个大点的分列两侧,每天抵头足而卧,数天上明亮的星子,听树上不寐的老蝉,叽叽呱呱地笑闹,讲着属于我们的故事,与对面不远处哥哥们的窝棚大声对话,任月光从绣花小布帘的缝隙挤进来,洒在我们明媚的脸上,那一年那个夏秋,外面地震的传闻纷杂惊悚,五个半小不大的丫头,在西园窝棚里,度过了一段惬意时光。
后来警报解除,住窝棚上瘾的我们,依旧不愿回屋,害得哥哥们也一直住对面窝棚里守护,直至天气微凉,才在父母的“逼迫”下,依依不舍“撤离”西园。如今,当年的小女孩都已年近(过)半百,每每相聚,总会忆起西园窝棚里新奇快乐的时光。
四.西园有宝
除了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更有一种神秘东西引领着我对西园那片土的眷恋。我成年,父亲已经故去,一天,母亲和我拉家常,突然想起似地提起一件事情,母亲说家里原来一祖传的绿瓷香炉,极细腻极圆润极莹亮的,据说是很有些年头了,那阵子“破四旧”闹的厉害,父亲担心这香炉被毁,便悄悄拿到西园,在小屋后的漫坡上挖坑将香炉埋藏起来,自那以后,就再没动过。这件事情母亲说得虽不甚经意,我却是用心了,不是指望它多么值钱,而是出于一种新奇怀恋和温暖:祖传的香炉?父亲亲手埋藏?西园的屋后?我便叫上哥哥不只一次去西园挖掘寻找,想找出父亲当年埋下的那个物件,但是寻挖了好多次,终也没有找到,按母亲的说法,地方应该不会错的,当年父亲怕后来找不到,还特意在埋香炉的地方种了一棵小树,如今小树出奇地茁壮茂盛,而那个小香炉却不知所踪。我想,万物皆有灵性,那个漂亮的小香炉精灵般地下游走了?找不到也罢,找不到便总有一种神秘,一种希望,找不到便是另一种美好,另一种念想。
五.心中西园
后来村里统一规划,我家西园被零落瓜分,大半已成了他人的宅基,西园不见了。也曾无数次走进坐落在西园的这家院落,仔细打量眼前的红墙绿瓦,眼前的景也是这般明亮这般突出,但无论如何和它亲近,也代替不了我心中的那个西园:碧绿的柳,通红的枣,黄泥的小屋,棕红的窝棚,吱吱的蝉,呱呱的蛙儿,还有游走着的调皮的香炉,那个地方曾经在我生命里,如今已驻进了我心里。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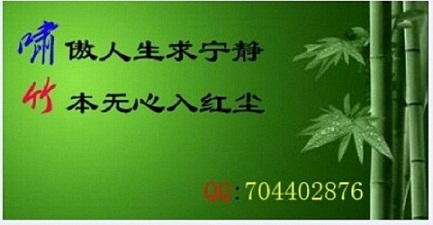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