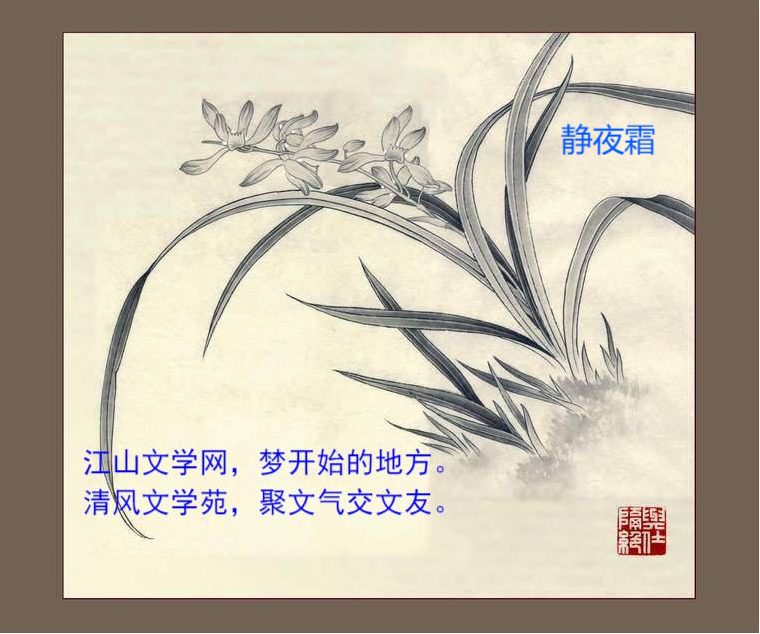【八一】深圳往事(散文)
【八一】深圳往事(散文)
![]() 我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去过深圳了!
我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去过深圳了!
对于深圳最初的印象,源于初中的政治课堂上,“说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啊,同学们将来有机会你们到深圳看一看就知道了,一个小渔村不到二十年时间就变成了一座驰名中外的大城市,这在人类史上绝对是个大奇迹呢……”政治老师站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说着,却没人知道他是否去过深圳,但他的一番描述,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深圳这座城市。当时年少无知,心里觉得——自己有生之年能到深圳看一看,也可死而无憾了。
几年后,到金城江上大学。正是QQ网聊流行的时候。见一些陌生人资料上的地址是深圳的,我总是习惯性地问一句:“你是深圳的吗?”听到对方说不是,不禁有点失望。
每次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可以借两本,我都会借一本《深圳青年》杂志。只是我一点都想不到,还没做好准备,自己就去深圳了——2005年7月,学校组织学生到深圳一家电子厂勤工俭学,我和班里的几个男生都报名参加了。
去深圳前,班里的阿伙冒着被全校通报批评的危险,偷偷摘了校园林荫大道上一些芒果树上的芒果,装进一个纸箱,密封起来。后来带上班车,半夜里我们爬起来吃,又苦又酸,几个人居然吃得津津有味。那天我们下午1点多钟上车,第二天上午11多点钟,才到达目的地。二十多个小时的路程,平生第一次如此长时间坐班车,用同学的话讲,蛋都疼死了。整个人昏昏沉沉,浑身酸痛。
班车进入市区,早晨七点多钟,有淡淡的雾,朝霞天边若隐若现,高楼耸立,道路纵横交错,公交车上赶着上班的白领丽人有的打盹、有的对着镜子化妆、有的毫不顾忌形象地将小笼包往嘴里塞,很多地方都看见有邓小平的巨幅画像,我心里想,深圳人民确实应该感谢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这就是深圳啊?”我喃喃自语了一句,眼前忽然浮现初中政治老师那张脸,心情并没一丝激动,倒是显得有点复杂。太阳升高时,我们终于到达水围新村现代电子厂了——巨大的厂门,在阳光的照射下,隐隐弥漫着一股陈年的气息。
站在车边,抽完一根烟,我心神仍恍恍惚惚。带队老师吩咐各自找地方吃完午饭,就在一栋宿舍楼前的空地上集合,由厂里人事部的办事员统一帮我们办理入厂手续,然后安排我们住宿。
我和班里永国同住一个宿舍。五楼,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宿舍住了十个人,虽是校友,却不大熟悉,肮脏的墙壁、破烂不堪的卫生间,让我和永国不由地怀念学校那明亮而宽敞的宿舍。第二天,我们就正式上班了。7:30-11:30属于早班,11:30-13:00属于午饭和午休时间,13:00-17:00属于下午班,17:00-18:30属于晚饭时间,18:30后属于加班时间,每小时3元,早班和下午班每小时2.4元。
固定模式的流水线工种,哪怕你在学校当过班长或成绩异常优秀,都不顶事,上班时候照样汗流浃背,灰头土脸。下了班,回到宿舍,个个叫苦不迭。整个宿舍就一个卫生间,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像筷子一样大,十个人轮流洗澡、洗衣服,轮到最后一个人洗澡、洗衣服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当时夜里十分闷热,第二天早上醒来,不仅头发湿了,就连内裤也湿了,那天花板中央的吊扇不起一点作用。
每隔两天,拉长发一次饭票。还在学校(院)时,领导们说厂里包吃、包住。上了几天班后,我们才知道厂里并不包吃,只是先发饭票,过后再从我们工资里面扣钱。
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确实很辛苦,有些人受不了,打电话叫家里寄了路费,就直接回家,没办什么辞职手续,一分工资都拿不到。大约是半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发生了一件让我郁闷不已的事——临睡前我把裤子放在枕头边靠墙的角落,裤兜里装着全部身家一百一十块钱,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裤子却在脚边,裤兜里面的钱不翼而飞了。
“可能是半夜时,有什么人撬门进来偷的!”几个校友纷纷说道,我并不认同他们的话,心里怀疑钱是被某个校友偷的,因为我睡的床在宿舍最里面的角落,距离宿舍的门很远,况且宿舍的门平时轻轻打开也会发出很大的响声,倘若真是有人撬门进来,何以单单偷了我裤兜里的钱,其他人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失?我估计啊,肯定是我洗衣服、裤子时把钱装进第二天要穿的裤子的裤兜里时,被某个心存歹意的校友看见了,于是他趁大家沉沉酣睡的时候摸到我床边把钱偷了,让我吃了一个大闷亏……发生了这样的事后,除了永国,宿舍里的其他人我都不再信任,也很少和他们说话。
我打电话叫哥哥寄两百块钱给我时,为了避免哥哥担心,只好撒谎说,我需要拿些钱去买饭票。哥哥信以为真。
尽管上班很累,下班后我们仍喜欢往一些网吧里跑。工厂周围当时有很多小网吧,虽然没有任何营业执照,却收费很贵,有的每小时3元,有的每小时4元,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特殊爱好者)来上网,这些网吧直接在电脑屏幕上建立“情色电影”文档。我到网吧上网,除了听听歌,主要是把自己写得很没章法的小说《或许此生都不懂》发到一个叫“深圳青年”的论坛上。
有一次,在一个网吧看见电脑屏幕上有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时,我激动不已,心里居然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以前电视剧热播时没能看过第一集。所以,在网吧里反复看了几遍第一集,我仍不觉得过瘾。每当我们回到宿舍时,通常已是凌晨一、两点钟。
由于手头紧,不敢多花钱,加上饭量很大,我经常被饥饿折磨。早上食堂提供稀饭、炒粉、油条、包子、馒头、豆浆,我很喜欢吃炒粉,可是一份2元,常常让我望而止步,只敢花1元买一根油条和一碗稀饭。早班一到十点多钟,我就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以我那时的饭量,早上至少要吃一根油条、一份炒粉、一碗稀饭,才算饱——这事只能想想罢了,毕竟我不能像其他同学任性,没钱了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家里人要,他们父母也不曾指望过他们勤工俭学时能够挣得多少钱,这与我家里人很不同,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没到深圳勤工俭学前父亲和哥哥都希望我自己能够解决大二的一部分学费。
为了不辜负父亲、哥哥二人的期望,我一直对自己说,哪怕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在深圳勤工俭学两个月,不可半途而废。
就这样,日子在我不断地给自己打气中渐渐远去。上班唯一的乐趣,也许就是干活时车间一直播放《丁香花》《突然的自我》《披着羊皮的狼》三首流行歌,将机器发出的嘈杂声掩盖起来。记得是,很寻常的一个下午,不知什么人趁我们上班,撬开宿舍的门,将永国密码箱里两百块钱和几张饭票都偷了,气得永国暴跳如雷。
恍恍惚惚,八月到了。有一天,我们不用上班,永国的父亲、哥哥、姐姐来了水围新村一趟,他们准备去一个小饭馆吃饭时永国把我叫上,我得以大快朵颐了一顿,这也是我在深圳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我后来还多次笑着跟永国说,吃别人的啊汗流,吃自己的啊泪流。也多次让永国笑得前俯后仰。
换到另一条生产线干活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个已在厂里上班两年多了的老员工,一个叫陈锦燕的女孩,年纪二十多岁,浓眉大眼,身材略微肥胖,是个很好说话的人,有时见我忙不过来,她都会主动帮我。下班后同学们都喜欢笑着打趣我,说我走“桃花运”了。有一次上班时候,陈锦燕忽然对我说:“很羡慕你们这些大学生,读得书,又能吃苦,不像我啊高中都考不上……”我怔了怔,就笑着对她说道:“你才厉害呢,年纪轻轻时就已经能挣钱养活自己了,不像我们二十多岁了还是寄生虫!”
“厂里老师傅们经常讲你们这些大学生很会说话,果然一点都不假!”陈锦燕咯咯地笑了起来,我问她QQ号码是多少时,有些出乎意料,她居然不会上网。于是约定好以后回了学校我就给她写信。
大约“朝夕相处”了一个星期,陈锦燕一共给了我两次饭票,让我加菜,我起初都很犹豫,直到听见她说她要与宿舍其他同事去外面吃晚饭后,我才坦然接受她的馈赠。
没多久,我们这些大学生暑假工又被从三楼调到二楼的其他生产线上了。当真苦不堪言。原来在三楼虽然也很累,但至少干活时可以坐着,到了三楼却是站着干活,而且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以致放假休息时除了睡觉,哪里都不愿去,为此同学们还多次笑着说,哪怕有艳遇,屁股也无法从床板上挪出一丝缝隙。
在我沉甸甸的回忆里,宿舍楼下夜宵摊的蛋炒饭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最好的蛋炒饭。永国当时说,其实不是蛋炒饭好吃,而是我们饿晕了,把普通的蛋炒饭当作山珍海味。
千盼,万盼,日思,夜想,两个月的暑假工生涯终于结束了。班里号称喝水都会发胖的小胖同学,也明显地瘦了一圈。
休息两天,我们就到办公大楼的财务室领工资。厂里发现金。扣完伙食费(两个月的饭票)和水电费,每个人还得一千三百块钱,揣回宿舍,一个校友将这些钱亲了又亲,接着,扔到地上,用脚踩了踩,最后眉开眼笑地捡起来,大声嚷他要去网吧通宵打怪兽,誓死保卫钓鱼岛。
我和永国、大念两位同班同学逛夜市时,与陈锦燕不期而遇。她也正和宿舍两位同事逛夜市。我们匆匆交谈几句,就散开了。但由于一时粗心,我并没有想到要送她什么礼物,感谢她之前的照顾。
转头,看见永国和大念毫不犹豫地掏出几百块钱买衣服、跑鞋,我的心情颇为复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我花40块钱,买了一个耳机和一本《安妮宝贝》精品集。耳机我打算送给父亲,书是留自己看。
第二天我们钻上回校的班车,夕阳西下的时候,天边晚霞如火。我恍恍惚惚地想起初到深圳的那个早晨,那片淡淡的雾,那些朦胧的街景。
也是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班车,我们才回到学校。
开学不久,我按之前的约定,给陈锦燕写了一封信,在信里除了给她寄去一张我的生活照,还告诉她隔壁1003宿舍的座机号码。
待陈锦燕打电话到我们隔壁1003宿舍找我时,是一个星期后的事了。我当时正和高中同学“洋妞”在南桥市场的一个小炒店里喝酒。陈锦燕找不到我,于是叫接电话的小李把她手机号码记下来,转交给我。我带着几分醉意回到学校,夕阳正缓缓下山。路过蓝球场,我看见外教露西(丝)伫立篮球场外的一片草坪上,一头金发在晚风中轻轻飘动,她身后火红了一片,那是晚霞倒映在光滑的地面上,有一种别样的美。
我一进宿舍,隔壁1003宿舍的小李就走进来跟我说,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找不到我,他就把她的手机号码记在他草稿本上。“我去你们宿舍看看!”我说了一句,就跟着小李走去他们宿舍,照他记在草稿本的号码拨打过去,电话很快就通了,陈锦燕的声音显得有点沙哑,可能是座机听筒不大好的缘故。陈锦燕在电话里说,手机是那晚逛夜市时买的,写给她的信是下午收到的……我们淡淡地交谈了几句,感觉身上汗渍斑斑,很不舒服,我就对陈锦燕说,需要洗个澡,改天再聊吧。“好的,你先忙,我们改天再联系!”陈锦燕点头应道,把电话挂断那一瞬间,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第一次通电话也是最后一次。
急着回宿舍洗澡,我忘记将小李草稿本上写有陈锦燕手机号码的那页纸张撕下来。过了两天想起时,小李已把草稿本丢进垃圾桶了,他们宿舍的座机也像我们宿舍的座机坏掉了,没一个人拿去修。我第二次写信给陈锦燕时,已是十月下旬,不知她是否收到——因为,八月在现代电子厂勤工俭学时她跟我说过国庆节前她可能会辞职,重新找一份工作。
两年后,我带了几本书,独自到广东的阳江市打工。后来辗转珠海、佛山,始终都没有想过要去深圳寻找出路的念头。那些在深圳现代电子厂勤工俭学的日子,仿佛被尘封了起来,往往都是在填写求职简历时,我才突然想起自己有过勤工俭学这样一段经历。那个叫陈锦燕的女孩,每次似乎都是顺带着想起来的。与爱情无关。
一别,十五年。
将这些关于深圳的往事写出来时,我心里想,那个叫陈锦燕的女孩也许正在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
没在流水线干过,看了书生的文章后,知道因为文凭学历的限制,体力劳动者难以向脑力劳动者转变的艰难。好文章,支持啊。特别是吃半生不熟芒果和钱被偷那些事,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