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风】回不去的故乡(散文)
【西风】回不去的故乡(散文)
每当我走近故乡,我的心情就苦涩难当。当我走在朝思暮想的故乡村巷里,我却被陌生和失落所代替。席慕蓉说,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在有月亮的夜晚响起。可是我觉得故乡是一首心扉涌动的诗,回忆时欣喜而甜蜜,走进时悲凉而苦涩。
其实,我现在生活的城市离故乡也不过百里,但是因口音的不同,还是被当地人贴上了“外地人”的标签。朋友曾调侃我,别人普通话说着说着就方言参半,而你正好相反。朋友无心之说,却是我心底隐忍的痛:原来我已不能用家乡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的悲伤与快乐。
想起十六岁那年初次出门,因不会说普通话而常常遭到工友们的奚落,甚至阴阳怪气地模仿我说话:阿木了?阿木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觉得家乡话好难听,也暗自发誓要学会说普通话。
光阴如梭,多年的漂泊与历练早已让我脱掉了乡音,虽然不太标准,但是交流起来已能轻松应对各地来客。每当抓起电话,脱口而出的问话不再是“阿木了”而是“怎么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虽在,却早已生涩冷硬,那柔软的乡音在舌尖打转,却早已发不出儿时的韵味。而那些我曾经刻意纠正的乡音,现在听起来是那么的婉转亲切。每一次回家,心头便多了一种说不清的情愫,且这种情愫越聚越多,如潮汐漫过堤岸,浸湿心扉。
去年夏天回家,到离家不远的小镇闲逛,顺便去店里看看姐姐。路旁,卖水果的小贩热情地招手打招呼。看着小贩真诚的笑脸,再看看红嫩欲滴的大樱桃,发亮的紫葡萄,毫不犹豫地买了两大袋。到店里,外甥告诉我:大樱桃五块钱一斤,葡萄和香蕉十块钱五斤……原来,我整整被多卖了两倍的价格还不止。中午去饭店帮姐姐买面,一份面又多收了两块钱,而且肉放的比以往少,面的量也小。一股涩冷在我心底蔓延,正逐步浇灭我内心对故乡淳朴乡情的赞美。“人生无根蒂,漂如陌上尘。”恍惚间,觉得自己像一支无根的浮萍,飘飘悠悠,没着没落。
其实,多年漂泊丢掉的何止是乡音,流失的又何止是青春岁月。在岁月的长河里,我们如岸边的鹅卵石,在风雕浪琢下逐渐磨去了棱角,变得圆润光滑,最终失去了最初的模样。
在无数个梦里,我回到了儿时的村庄,常常奔跑在村子周围的阡陌小巷。田野里油菜花正旺,蜂儿蝶儿正忙;沟渠边柳树正绿,艾草正散发着柔柔的清香。
走出属于我的故乡后,除了熟悉的方向和旧时的鸟雀,我已无所适从。陌生的巷道,新修的水泥路,陌生的房子,新砌的院墙,路边的新车,和一溜陌生的坐车人。村人一大半已不认识,即使认识也是一脸的疏离与冷漠。转过身,背后是探照灯一样的目光和不曾掩饰的低语声。
电话里曾不止一次地听母亲轻描淡写的说起收玉米,事实上我也以为收玉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国庆回家,去地里帮父母收玉米,不到半个小时,我的脸开始火辣辣的疼,右脸颊又红又肿,手虎口处也被磨出一个紫色的大血泡。我汗流浃背,拿着铁锹狼狈地围着一棵玉米树打转,玉米根却牢牢地抓着地皮不肯松手。
远远地,我看见佝偻着腰的母亲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的将军,铁锹过处,玉米树便整齐地匍匐在她的脚下,顺带着杂草也分了家。跟在母亲身后的父亲,瘦胳膊一扬一抡,锄头在空中优美地划出一道弧线,玉米树根便乖巧地搬了家。我悲哀地发现,故乡是父母的故乡,是我童年的故乡。故乡的人,故乡的事,还有那泛着青草香味的土地,都已离我远去。现在的我,对于故乡来说,已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局外人。
远去了。曾经赖以支撑我信念的故乡已经远去了。它已经随着沾满露水和草香之间的泥泞小道隐藏在了繁华背后,它已经随着散发着青荇味的沟渠的变化而改头换面了。那里曾是小伙伴们的乐园,那些年曾有过的泥巴混着唾液的泥玩具,那些年曾有过的扮家家、背新娘的欣喜;那些年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上的碰撞声和启蒙入学的郎朗读书声,亦随季节的风成了我甜蜜的怀念。
远了,近了。近了,远了。朦胧中我想努力抓住些什么,睁开眼,只有一缕风从手边吹过。
东面的大庙山青了又黄,西面的大夏河涨了又落,北面的黄河水依旧哗啦啦地向西而流,而我再也找不到回去的小路。那些盘亘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渐渐地化成了笔端的一首乡愁诗。也许,在另一个陌生的城市,我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家,自己的记忆。也许它会成为我的另一个故乡。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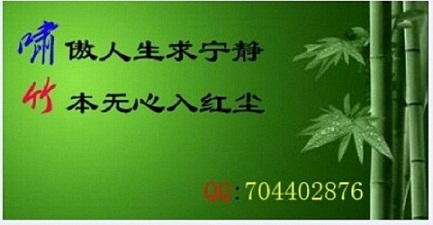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