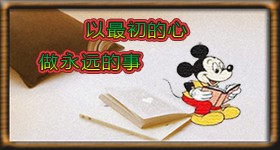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匣中玉(小说)
【流年】匣中玉(小说)
![]() 1
1
她看到他的时候,仿佛看到的是一个影子。
他瘦多了,走路像阵风,可并不快。她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们怕有五年没见面。是的,正好五年。但她还是一眼能认出他,哪怕瘦得像个影子。他从公交车上下来,四处张望了一阵,才看到她。
“绿珠!”他快步跑过来,亲热而又羞怯地喊了一声。
“你认不出我了吧。”她笑着说,并没有问他的意思。
“不是,刚刚没看到呢。”他更加羞怯,相对便减少了亲热。
“石崇,你太瘦啦,再这样下去可以糊到墙上当纸菩萨。去检查了没有,是不是身体有病……”
讲完这句,她突然发现他心事重重,赶紧收住口。昨天,收到他发来的短信,一个压根儿没有想到的短信,她惊讶自己不仅恨意全无,心里甚至还泛起了那么一点点惊喜,好像这五年来她一直在等这个短信似的。而其实,从听到他结婚那天起,她就发过誓,再也不会理他了!
他们在同一个村子里出生、长大,同时发蒙读书,读完初中同时戛然而止,回家务农。他们的家境也差不多,整个村子各家各户都差不多,就像荒地里长出来的野草,有长有短,但都是野草,没有长成一棵树的,也没有短成一片叶的。仔细比较,他家稍好,因为只有石崇和他姐姐两个小的,她则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年纪尚小的弟弟,负担自然重些。但这种差别,肉眼几乎看不出来,同样的五六间瓦房,同样的家具电器,同样的青布衣裤,每张餐桌上摆着同样的饭菜——他们就是这样,长在了同一根藤上。他们是同一根藤上靠得最近、大小最为接近的两只瓜,不生出些事来,好像对不住造物主的安排。
务农第二年的秋收完毕,她没事来他家玩。他们关系很好,你来我往的,几乎没有性别意识。她大大咧咧,他略显文静,看上去更像兄弟或者姐妹俩。没能进入高中深造的本村同学大多南下打工去了。他因为姐姐去了佛山,家里只剩下一个儿子,而她哥哥去了深圳,家里希望女儿能做个帮手,都被留了下来。他们自己也不约而同地没有南下打工的意愿,而是更希望待在老家,待在这个偏僻的村庄里,过那种野草和南瓜藤一般的生活。
那天晚上,他父母碰巧有事出门了,他们聊会天,忽地静默下来,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做什么好。他就带着她在自家屋里乱翻,不期然在父母卧室五斗柜最底层的抽屉里翻出一张碟。贴在碟上写着片名、印着剧照的彩纸被撕得稀烂,看得出是故意撕成那个样子的,仿佛要掩藏一个秘密。没事,我们看碟吧。他说。好哇!她随口附和着。他把碟片塞进电视机下面的VCD内,找到遥控器摁下去。
像是打开了一个魔幻而奇妙的匣子,从里面飞出令人晕眩的光芒像一群嗡嗡直叫的飞虫,钻入这两具尚显稚嫩的身体,胡乱按遍了体内每一个青春的按钮。那些他们心里明白却从没想过要做的事,受到启示般引诱着他们,有如一艘沉没海底的巨轮被强劲地拉出水面。
碟片磨损严重,在电视里卡得厉害,画面时常模糊不清。这反而造成一种强烈的效果,牢牢铆住了喷得出火的四束目光……时空被割裂开来,村庄、田野、季节、晨昏、农事、亲友,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记忆,统统退出了他们的脑海。他们依葫芦画瓢,在电视机前完成了第一次游戏。由于毫无经验,他很快完毕,草草收场。欲望之火渐渐熄灭之后,从没有过的羞怯让他们抬不起头来。她没说一句话,撇开他,匆匆没入夜色,撂下他一个人坐在屋里发呆。
不久,父母回了。他躲进自己房里,坐在床上继续发呆。直到第二天下午,父母去田里干活了,他才恍然想起,碟片还在VCD里面。他慌忙打开VCD,里面却没有那张碟了!父母卧室的五斗柜最底层那个抽屉里也没有,五斗柜的所有抽屉里都没有,他能找到的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
吃了晚饭,他出门去绿珠家。在山坳上碰到绿珠。他忐忑地问,你去哪里。她近乎粗鲁地回道,不去哪里。硬硬地像扔过来一粒石子,砸得他愣在那里。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但他知道现在得听她摆布。她会如何摆布他呢?他就那样傻愣愣地站在那里。一阵风吹过来,贴在他耳朵边说了一句悄悄话,他似乎是重复了风说的那句话:你去哪里。她依然粗鲁地回道,你管啦,一整天都没见人!她暗示他错在哪里了。他走过去,委屈地说,今天被我爸捆在菜园里,这不去找你嘛!她一副没有解气的样子,扭身往坳上的一片枞树林里走。他快步跟了上去。她越走越快,他也越走越快,夜晚也越走越快。走着走着,她突然停住,他也突然停住。夜晚没停得住,一个趔趄绊着了他们,将他们重重推倒在厚厚的枞毛须上……
从此,这片枞毛须几乎每天都会录制VCD里面那样的节目。直到有一天,女主角没有主动配合猴急猴急的男主角,而是眼光迷离地问他,石崇,你喜欢我吗?男主角停下手上的动作,说,喜欢啊!她攥紧他的手臂:不,你看着我。他看着她:你今天怎么啦?她说,没什么,我发现我爱上你啦。他说,绿珠,我也爱你。她开心地笑了,笑得眼角湿湿的。她松开他,捏着他灼热的掌心说,我们不能老是玩这种偷偷摸摸的游戏,下一次,我想要名正言顺地放到我们的新房里!他向她保证,没问题,我回去就跟我爸妈说,等我的好消息吧。绿珠把他的手臂攥得更紧,生怕他跑掉似的:说话算数哦,我天天这个时候在这里等你,没有好消息不要来见我!
“绿珠模样儿不赖,脾气却倔得像根檀木扁担,在家里总跟她妈扛起吵。你又是个糯米砣,我们都会跟着受罪。”他妈妈一听他的话就打破,“我晓得你们有名堂,昨天还跟你爸商量,让你去广东打工算了。你姐还有点钱寄回来,你呢,闲在屋里,不造些事出来不得舒服!”
石崇嘟着嘴说:“你和爸老是吵架,一样日子过得好好的。绿珠脾气大,我让着她就是,肯定会比你们和气。”
“你让着他,娘心里不添堵啊!你越让,她越嘚瑟,你落个清静,到时候还不是婆媳间麻纱不断。你要和她结婚就出去搞,再不要进这个家门;要不就好好待在家里,从现在起,莫跟她鬼混啦。否则,我就操起条子去她家里,老子要抽脱她的腿!”
接下来三个晚上,绿珠都没在那片枞树林里等到石崇。第四天一早,她整了个简单的行李包,跟她爸说,她去深圳打工了。
她从村里走到乡上,在乡镇的车站坐中巴到县城,她哥带她来县城玩过两次。她从县城坐大巴到南山市,发现南山市只不过比县城大点而已。她从南山市坐客车到省会潭洲市,发现潭洲只不过比南山大点而已。她想,深圳或许也只比潭洲大点吧。她哥从深圳寄钱回来,汇款单上写着“深圳宝安区龙华镇振亚制鞋厂”。她坐火车去了深圳,再从深圳火车站坐中巴去龙华镇,没费多少周折就在振亚制鞋厂找到了哥哥。哥哥问她,你怎么来了?她没好气地说,来了就来了呗。她蒙头睡了两天,第三天哥哥介绍她到鞋厂的包装车间上班。这个镇比他们县城漂亮多了,但制鞋厂里面,硫、苯、碳、氮沆瀣一气,橡胶、棉布、涤纶、锦纶耀武扬威。最初几天,她唇干嘴燥,双眼流泪,鼻子出血,呕到胃里出酸水……一周后,她就适应了,并一跃成为包装车间最能干的工人。
2
春节,绿珠和哥哥一起返乡。她在家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石崇和邻村一个姑娘结婚了!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到坳上那片枞树林里,趴在厚厚的枞毛须上,完全敞开自己,痛哭了一场。山上的枞毛须被她的哭声震得飞到半空,像利剑一般四处砍伐,将夜晚的外衣砍成了碎片。她发誓再不理他,否则自己遭万剑劈杀。回到家,妈妈骂她,死到哪里去了?她避而不答,心里却难得地认同一次妈妈说的,真是“死”过一回了。妈妈追着她唠叨,今晚猫头鹰叫得厉害,三十多年没听过猫头鹰叫了,不吉利啊!你乱跑,小心撞见鬼!她就把自己关进房里,没有乱跑过一步。
大年初四,她初中时的好朋友孙秀过来看她。孙秀说,东莞打工的环境和条件比深圳好多了,跟我一起去东莞吧。绿珠受够了振亚制鞋厂的味道,问孙秀,东莞也是制鞋厂?孙秀笑着说,你眼里就只有制鞋厂吗?天下大着呢。去制鞋厂那是慢性自杀,我保证你在东莞绿色、环保,更重要的是,还赚钱。她就跟着孙秀去了东莞。
到东莞才明白,“绿色、环保,还赚钱”是做那事。她怪孙秀骗她。孙秀说,不做这事也行,那就和在深圳一样,去工厂车间吸毒气吧。她从孙秀所在的发廊里出来,连续跑了虎门、樟木、长安、厚街等几个经济发达的镇,不是制鞋就是制衣,不是家具厂就是电器厂,仿佛一个个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巨大魔兽在追逐她,恨不得将她生吞活剥。逃无可逃,她回市区找到孙秀,才吁出一口气。她在孙秀那里蒙头睡了两天。第二天晚上,她梦见了那片枞树林,梦见了那个可恨的人,半夜醒来,她把剩下的泪水流干了。清早,她对尚处于迷糊状态的孙秀说,我愿意。
孙秀不愧是好姐妹,毫无保留地向她传授经验。客人如果是看着还顺眼的,就想象他是你生活中想念和喜欢的男人,这样也给自己一点福利。大部分是看着不顺眼的,那就把自己当成一根骨头,把他们当成一只啃骨头的狗。狗性难改,它啃几下就完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有时也会碰上恶狗,甚至疯狗,就要想办法保护好自己,千万别和他们硬掰,那横竖是你自己吃亏,受伤害。恶狗、疯狗更要哄,一哄它们就会乖巧许多。孙秀的经验很管用。第一个看上她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他趴在她身上真像一只啃骨头的狗,不过没啃几下,自己就蔫了。他对着她抱歉地笑笑,希望她陪他再躺会儿,直到这个钟点结束。她同意了,因为他递过来不菲的小费。这个老头以后再没来过。是嫌她没服务好,还是被老婆发现了,还是……她竟然时常想起他,或许第一次总是令人难忘吧。偶尔也有让她比较投入的,像孙秀说的那样,可以想象“他是你生活中想念和喜欢的男人”。那个时候,她脑海里无不浮现出那片枞树林。她有时会用家乡话喊出“石崇”的名字,客人听不懂,他们似乎颇喜欢她这样喊,做起来更加带劲。
不觉在东莞做了三年。这是一个见不得人的行业,就像生活在卑湿之地和阴暗角落的蚯蚓、潮虫、蚂蚁、土狗子,它们和她们,都是这个世界公开的秘密。人们不了解蚯蚓在地下如何生活,不代表蚯蚓就没有它们的生活。严格地说,很多客人都不了解她们,大部分客人和社会上的人没有两样,认为她们脏。其实,她们比客人干净得多,更多时候,是她们嫌客人脏。他们中有的人身子像从没洗过似的,比如打工仔、建筑工人或者不爱干净的知识分子,和他们办事真像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还有的比牛粪更臭,简直是狗屎。他们衣着光鲜,道貌岸然,因为自己贱,所以把别人看得更贱,各种奇葩服务令人难以招架。有次,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欲强行将脚趾塞进绿珠口里,绿珠坚决不从。那厮扇了绿珠两记耳光,打得她鼻血直流,还砸坏了店里的饮水机。
沦陷于屈辱之中的绿珠多么想抽身而出,回老家去,特别是当她哥哥告诉她,他听妈妈说,石崇在她一气之下跑去深圳后,几次到她家里向她妈妈打听绿珠的下落。妈妈对他当然不会有好脸色。不久,妈妈经常发现崇伢子站在绿珠家的后山上,像个傻子样地盯着绿珠的卧房。有回妈妈对着他破口大骂,说他是猪鼻子插根葱装蒜,绿珠死也不会嫁给他这个脓包!
妈妈为什么不告诉我?绿珠蹙着眉头问。哥哥说,妈妈怕你知道了就要回来,她恼火石家对你的态度,也不想你嫁到石家去。妈妈还提到一件事,石崇小时候有个老头给他算命,说他八字带劫,会有血光之灾。绿珠嗤笑道,迷信得没救。此刻,她无比后悔自己当初出走的冲动,对石崇的恨意随之大为减少。但她越想回去,越清楚自己回去不了了,因为她越爱石崇,就越不想见到那个已为人夫的石崇。哪怕是过年回家三五天,她也是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走亲戚,不串邻舍,让自己与世隔绝,或者说,与石崇隔绝。
东莞的问题是已经成为全国的眼中盯,三天两头扫黄打非。她们发廊虽然妈咪在公安局有熟人,每次都躲过去了,但日子过得就像大雪天过独木桥,心惊胆跳。圈内朋友建议她们回潭洲。潭洲娱乐业越来越发达,流动人口增多,做这行还比较隐蔽,好赚钱。经常来她们发廊的一名王姓商人,她们叫王总的,引荐她和孙秀去潭洲市的金谷宾馆。孙秀不想回本省,被人撺掇去了四川。绿珠琢磨了一个晚上,如果东莞待不住,她还是更想回潭洲,离家不近也不远,心里踏实。
她很快喜欢上了潭洲这个城市,街上讲南山话的不少,显得亲切。但她必须用普通话将自己遮蔽起来,特别是当客人中有讲南山话的,她就不能露出半点南山口音。这是她们俗成的行规,对客人好,也对自己好。有好事者问她哪里人,她会说,湖北人或者江西人。
前天上午,她意外地接到石崇发来的短信,说他到了潭洲,有急事,想见见她。这个短信让她百感交集,她看着看着视线就模糊了。擦了把眼睛再看,看着看着视线又模糊了。那半天,她就在不停地调出那个短信看,让自己的这个世界变得时而模糊,时而清晰。但她一直没有回复,连回复键都没有按过。晚上,她接了两个客人,发现自己比平时更有活力,身体感觉也不一样,把客人高兴得屁颠屁颠的。直到昨天吃晚饭的时候,她才决定以前的誓言作废,一来她早已不记恨他了,二来“有急事”也让她担心和好奇,万一是她家里有什么事委托他来的呢?她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匆忙回复,约他“明天上午十一点,人民公园门口见”。
灵魂对晤、以心悟心,逝水的时光变得更丰盈和饱满。
善待别人的文字,用心品读,认真品评,是品格和品位的彰显!
我们用真诚和温暖编织起快乐舒心、优雅美丽的流年!
恭喜,您的美文由逝水流年文学社团精华典藏!
感谢赐稿流年,期待再次来稿,顺祝创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