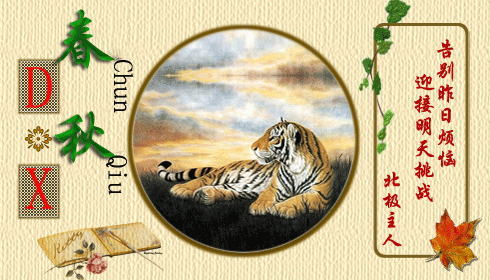【春秋】最初的记忆(散文)
【春秋】最初的记忆(散文)
![]() 有人说,小孩子两三岁前是没有记忆的。问了下度娘:“正常人开始记忆时间是3-6岁,不会过早过晚……”
有人说,小孩子两三岁前是没有记忆的。问了下度娘:“正常人开始记忆时间是3-6岁,不会过早过晚……”
也有人说过,一个人经常回忆往事,特别是小时候的事,就说明她已经老了。
真的是这样吗?
很小的时候,就对一句话耿耿于怀:人过三十天过午。那时专注地听站在黑板前的老师在讲: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点的太阳……还有无限向往《中国少年报》眉头醒目位置上的那行充满魔力的字:奔向2000年……用当下的说法就是:太辣眼了——无限美好的2000年怎么就成了“午后”人生了?
真的到了跨世纪的那一刻,一直萦绕大脑海中不忍离去的“魔力”消失得了无生趣。
还好最初的记忆还在,从来都没有变过。
那应该是我三周岁生日刚过的早春,抑或是四周岁前的隆冬,是早上五六点钟,抑或是傍晚四五点钟,我穿着厚厚的老棉花絮的棉袄棉裤,两只小手对抄在袖口里取暖,依着比我高出很多的酸菜缸。
妈妈,妈妈,我几岁了?(现在还能想起那童稚的声音清脆中透着娇骄二气。)
你四岁了呢!
妈妈蹲在冒着热气的灶台前,一边往灶坑里填着柴火一边耐心地回应着,不记得问了多少遍又回应了多少次,可以确定的是不止一次。
记忆的碎片里还有这样一幕:那是一个中午,向来乖巧的我大声的哭闹着,着急去上班的妈妈在地上团团转,奶奶在一旁说:悄悄去上班吧,你走了就好了!妈妈向门口走了两步,不放心地回头又看看我,急着一大步窜回,顺手抓起一旁的抹布塞到我乱蹬乱踢的两腿之间,一面忧虑而又无奈地转身走了。奶奶踮着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过来,一边哄着我别哭,一边把我抱离“尿窝”,拿起那块抹布拧干,再来擦着炕上湿的地方,反复几次后,又来抱起我,帮我换了条干的开裆裤……
而这张几经辗转的老照片,算是我的童年唯一的影像留痕了吧。记忆的碎片中,还依稀可见:
那天是妈妈的同事,一位下乡青年为单位劳模拍照,我和妹妹正好在那玩,不记得妹妹是什么原因很是不开心,一直在哭,就有人提议:别哭了,给你们也照一张。我顿时高兴得不得了,妹妹也止住了哭。有人从屋里搬出长条凳,我跑着爬坐上去,有人把妹妹抱起放在我旁边,说:搂着点,别掉下去。
于是就有了这张无比珍贵的照片。
说它珍贵,于我是最美好的童年时光的唯一,于流逝的光阴,它又承载着许多时代的元素和印迹。那个时代,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
那扇敞开的木门,那墙上的大字块,两姐妹身上穿的毛衣——用拆下来的缝面袋口的线织成的……
时隔半个世纪,我庆幸,那扬在脸上的笑容一直在——无论多苦多难,笑对人生,心有阳光,做一支不屈的向阳花,哪怕扭曲了躯体,也要向着那束光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