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年】挖掉的绝不仅仅是墙脚(小说)
【流年】挖掉的绝不仅仅是墙脚(小说)
这年的公历六月份,绵绵不绝的细雨,蚀软了高岭村东北边的那座学校的地基,学校就垮了,连累着屋后山坡的根基,泥土夹裹着树木细草碎石滑了下来,冲垮了校舍前边的围墙,又把坎下根根家志明家的老房子,都砸烂了一角。
噩耗来时,根根刚好走出陈英牙科医院,除掉了他人生中的第三颗牙齿。这时的根根,正处于人生的最低潮。他打工的那家小型家纺厂,老板娘突然被检察院的人带走。起先工人也没觉得什么,就像平常老板娘出去进材料,隔个三、五天也就回来了。没想到一等就是一个多月,甚至连老板都没出现过。大家就耐不住了,四处打听,才知道老板跟老板娘早在两年前就离婚了,一直瞒着大家。像一场阴谋。看来老板娘归来是遥遥无期,不可预测,大家就作鸟兽散。根根失业,成了无源之水,时间一久,又浑又臭,和媳妇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最后闹离婚,因着孩子的归属问题,又闹到法院。想到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争取不到,他气得在法庭上脏话乱喷,骂了N次草泥马。最后被罚两千拘留十五日。
交了罚款,拘留所待了十五天。
他已穷途末路,穷困潦倒。他翻遍住处,也没找着有任何值点钱的东西。他满大街游走,孤魂野鬼,就为了能遇见熟人,讨也好,借也罢,只要能拿到几个钱到手心里,那都是救命的稻草。熟人是见过几个,包括报不上名字只能喊“嗨”的。人家拿眼睖他,人家黑眼翻成白眼鄙视他,连打发叫花子的怜悯心都一丁点儿不给。想着马上要忍饥挨饿,想着房东老头儿将要把他扫地出门……急火攻心,牙疼,疼到满地打滚。不敢去大医院,大街小巷乱窜,终于在一个无名弄堂口遇见“陈英牙科医院”,便钻进去,见人就龇牙咧嘴喊道“拔牙拔牙拔牙”。牙科医生并不善解人意,劝他保留那颗被虫蛀成空心壳的牙齿,说修修补补兴许还能用个几年。
我饭都吃不起了,留它何用?
牙科医生算是听明白了,下手毫不客气。
金属和碳酸钙碰撞,一秒铿锵响,那颗制造痛苦的罪恶,便离开了他,划道弧线,在屋角的垃圾桶找到了它的归宿。
虽然除掉了痛苦的罪魁祸首,可余孽未尽,仍在噬咬他的肉体。但他毫不在乎,他知道,剩下的那点疼痛,垂死挣扎不了多久了。他走出医院大门,立定于弄堂口,眯着眼,嗅一嗅新鲜空气。
走在大街上,正在思考人生该何去何从的时候,突然就听见有人大喊:根根,根根。
他顺着呼啸而过的喊声,追逐到一辆黑色小车。它突然减速,紧接着猛然停顿,发出一声刺耳的聒噪。从车里面钻出一个胖子向他招手,一头柔软稀少的长发,在街风轻拂中飘逸。原来是他的邻居志明。也就是这个时候,志明告诉他,他家房屋倒了一角。
我家的墙也倒掉了。志明撇了一支华子给根根,自己先点上了,猛吸一口,眯着眼在迷雾中沉思。
看他肥头大耳的模样,油水充足,奥迪A6,肯定混得不错。传说不是空穴来风。说他结识了一个温州大老板,多女无子,看上他了,把小女儿嫁给了他,经营多年的五金厂当作嫁妆,也给了他,自己四处云游逍遥快活去了,有钱无事一身轻。此刻的根根想想自己看看志明,百感交集。
志明把叙旧地点选在一家小酒店,场面虽然不大,却小而精致。根根一次又一次被感动得稀里哗啦,话题就如潮水,把这些年的酸甜苦辣一倒而尽。根根和志明,就像一根藤上的两颗瓜,小时候的命运要多相似就有多相似。两家的房子肩膀挨着肩膀,一边的泥墙靠着泥墙,连一只鸟儿都难以飞进缝隙。老鼠钻来钻去、钻来钻去,风吹吹雨淋淋日晒晒,空洞越来越多,蜂窝也越来越多,鸟窝就越来越多,生儿育女,成就了一片热闹的鸟村,繁衍生息。根根和志明同年同月生,同样有一个大三岁的姐姐,两家大人都死得早。志明八岁时,冬天,父亲上山砍柴,跌落悬崖,离去。冬去春暖,来了个瘟疫,根根的父亲没熬几天,便执意追随而去。志明十四岁,母亲积劳成疾,丢下两个半大不大的孩子,归西。眼见邻居孩子都还小,根根的母亲将抚育的担子挑了过来,为几个孩子刨食,终年辛苦劳作,日积月累,终于耗尽能量,在一个暴雨天里,呜呼哀哉。
别怕,有我。见根根喝一口酒唉声叹气一来回,志明就说,过去的事情就让随它过去吧,重要的是以后,你讲,以后你想做什么,告诉我,只要我帮得上,都帮,没有问题。志明的话犹如春风袪寒,让人振奋。根根决定了,先去一趟高岭,看看老房子,看看能不能修修,修不了再说。然后回城再找工作。根根不是个偷懒的人,他干过工地,搬砖,挑泥。他干过船工,行船不分昼夜,跑遍运河钱塘江富春江兰江新安江。他不怕苦不怕累,只求个安安稳稳过日子。这不,收入一不稳妥,婚姻就摇摇欲坠。妻子带着孩子避瘟神似的逃离他,过去的情情爱爱,仿佛就是一坨屎。根根在心里把前妻咒骂了一番,又连带着思念了一回孩子,最后徒然在酒桌上饮泣自怜。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崩溃的感觉在全身蔓延。毛病到底出在哪儿,根根自个儿无法剖析,他天生不善于下定义,无论是对别人,还是他自己。
有了志明的话,根根陡增信心,有了面对现实的勇气。志明对老屋,无所谓的态度。他十六岁时,他姐跟了邻村的一个鳏夫。那男人大姐十几岁,家徒四壁。志明不明白姐图那人什么,无财无貌亦无才,难道就因为是个男人?志明无解。高岭不再有他留恋的,便毅然离开,远走他乡。只是年龄渐长,便又有点思乡的味道了,后来,偶尔和姐有联系,仅此而已。老屋倒塌,是姐电话告知的。如今,偶遇发小,便滋生出一种近似母爱的情愫。他业务忙,出差到老家所在地的县城,见到了这个正失魂落魄的发小,根根。没想到根根不老的年纪看去是如此的苍老,发茬稀拉,一簇白一簇灰一簇浅黑,色泽斑斓,整个头比以前缩小了不止一围,满脸皱皱巴巴,似只干枯的核桃,背也驼了,瘦小如猴,要不是左脸手指印那么大的黑胎印顽强地效忠,他无论如何是认不出的。
去吧、去吧,也顺带帮我去瞅瞅我家那老屋。酒是好东西,有了它男人更豪气,更大方爽快。志明加根根微信。就当这些日子你放假,工资照发。志明手机屏幕上手指扒拉扒拉,“叮咚”一响,对着根根晃一晃手机,说,钱转给你了,收去。去高岭上看看,你有想法告诉我,我来办。久旱遇甘露,根根省略号似的点头,好好好!
这时根根才意识到好几年没有回过村了。三年,还是四年?他真搞不清楚了,大概三年多吧。
第二天他开着他的唯一家产电动车去高岭。高岭不远,路也好走。公路是好路,根根初懂人世时就存在,卡车能开。以前石子土路,现在水泥铺垫。路就那么存在着,走得人少,跑的车少,就像那种不愿意老去的女人,以那种不易察觉的细小缓慢的步调衰落。高岭的路风韵犹存。只是村子落在山巅,像只百年果树树梢头的熟果,难以到达,盘山公路,海拔陡升。村子就是那么个村子,二十几户人家,几十年过去了,村子还是那么个村子,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早来鸡犬喧,夜暮炊烟起。还是以前那个味道,还是以前那个气息,带着土腥味草腥味潮湿味。
那天还是下雨,不大,淅淅沥沥,尿不尽的样子。村子里不见有人走动,家家大门都开着,人都在着呢,门边小凳子上坐着,呆望着门外迷雾一般的小雨,灵魂出窍。下雨的日子村里人实在无事可做。实在无事可做,那就守着屋内屋外的唯一通道,门。这里可以透过弄堂看得见一溜儿雨中的山,歪歪脖子能看见对屋屋檐滴水珠子,忽然就见有人经过,眼睛都亮了,精神气都来了。那不是根根吗!啊哟喂,根根啊,这么难得哎多年没有看见你过了哎。
难得、难得,家里坐家里坐,吃杯茶。这是眼神儿还好年纪不太老的老人招呼。
你哪个?哪里来的?啊,啊哟哎,你,你,不就是那个根根啊,多年了啊,到哪里去了啊,来家里坐下、坐下。这是真正老了的老人招呼。
根根受宠若惊。禁不住人家的热情,走了几家,才转到老屋。地势稍高的学校完全垮了,似一堆绞烂的动物内脏,屋后的山扒了皮,裸露出鲜黄肉身。木门苍老沟壑纵横交错,已辨不清原来模样。银灰色大挂锁脸上长满烂疤,钥匙与锁已不相认,怎么也对不上暗号。他只好拿石头砸开,推门而入,大门发出扎心的嘎嘎嘎声响,同时侵犯到上门框的九脚蜂窝,几十只九脚蜂奋起进攻。他觉得头皮一阵一阵麻,抱头鼠窜,遇着一胖子,连忙呼着去他家。胖子用苞谷烧给他洗脸洗头,皮肤又瘙又痒,受酒精味刺激他咳嗽喷嚏不断。忍不住脸上挠,抓痕条条。
我会不会被叮死?他觉得呼吸困难。
胖子大笑,说,这九脚蜂毒,是会死人的。你看看,他指着地上的一只死蜂,到我家它还死叮在你眼皮上呢。胖子踏上一脚,把力道运到脚尖,又扭又按,把那只蜂变成一点肉酱。
到这时根根对胖子还是疑惑重重,一脸问号,谁都看出来他不认识眼前的胖子。胖子有点不高兴,啥人哇,自个村里人都不知道自个村里人。我祖山,祖山,晓得不,想起来了没?
噢噢噢,根根仰头狠想一通的样子,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祖山、祖山。名字是熟,但和这个人对不上号啊,他想。胖胖想是见多了这种情况。是啊是啊,我以前瘦这会儿胖,身体不好咧吃药吃胖的。
胖子唠叨自己的病。上不了班,只好归家来养病,困不着觉啊,日日困不着觉啊。突然转话题,说根根啊,你还好不在家,屋是夜里倒掉的,轰隆隆,轰隆隆危险地响啊,我没困着觉啊就听见了,刚开始还以为山洪暴发了呢,你要是歇在屋里头啊那笃定完了。听到这,根根出了一身冷汗。
老屋其实老得很,要不是大姣把学校围墙底大石头砌的坎掏空,再大雨,学堂也倒不掉,那你家和志明家的屋也不会倒。
原来如此!
大姣家就在学校旁十几米处。学校地址原来是个斜坡,先造教室后围墙,地基打得深,填大块大块青石,基垒得高。大姣家龟缩在一旁,像大汉和小猴试比高。学校学生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没人了,围墙大栅铁门一把锁。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好像有几年了吧。老头归天,儿子去县城打工。生活费吧儿子会给,不用愁生活。这日子,要多少无聊就有多无聊。得,那就种点菜吧。可孙子到了读书年纪了,一切就变了。为了小孩读书方便,大姣儿子咬咬牙,在学校附近买了套房,二室一厅,一大半的钱都是问亲戚朋友借的。时间不久就经常有亲戚来家里串门,打听她儿子的情况。她明白那意思,人家怕他儿子一时还不上呢。她就急,那就养鸡吧,那,索性再养几头猪吧。正好村里有人做民宿,那便是要吃的喝的,城里人要吃土鸡土猪,她这里正好供应,能换些钱凑些帮儿子还债。
猪有猪舍,鸡就算了吧,屋旁用大网网出一大圈子。
根根能想到大姣是怎么想的。刮风下雨下雪,鸡们也要有个藏身之地啊。学校地基底下有些石块松了,小鸡经常进出。干脆,把大青石撬掉几块,不够大,再撬几块,腾出大块地盘来,嗨,像个天然溶洞,鸡们终于幸福了。
出了祖山家,根根又转回老屋。他脸肿胀发红发亮,眼睛成一细丝状,很妨碍他的视力。
他家的东角和志明家的西角,塌方的基石烂污泥一下子撞进了屋,似喷出的呕吐物,直喷射到大门。丧气的感觉全身蔓延,他不由得垂头丧气。他犹豫半天,还是打了伞,蹑手蹑脚,像个小偷在屋里转悠。都说人倒霉起来连喝水都会噎死,何况在缺胳膊少腿的屋里。老鼠听见动静了,一只二只四五只,探头探脑。或许只当他是个偶然客,那些老鼠围着他走来走去。看来是一个大家族携老携幼参观“大象”来了,老屋怎么成动物园了吗。
呼啦啦啦,屋梁出几只黑色鸟,也不知道是个什么鸟,朝倒塌的缺口冲出去。响声吸引到几只鸡,还以为有什么美味,便飞奔而来。果然有散落的虫、蜂、雏蝶。鸡子快乐啄食。见着鸡根根就来气,抄起地上的笤帚就打,鸡们咯咯咯叫着扑腾,拼命朝缺口外逃。根根提杆后仰,使劲一投,笤帚如长箭,气势如虹,勇追穷寇。就在他气撒尽舒坦一口长气时,一串尖厉刺耳的骂声劈头盖脸砸来。
啊哟喂——哪个见阎王的哎,怎么赶死都要拉只鸡垫垫背个,真个没有出息的东西啊,几只鸡吃它的草困它的觉,哪里就犯着你吃饭上茅坑了啊!追着话瘦干干的大姣就到了根根面前。哟,哟哟哟,我说呢好端端的扁毛畜牲叫厉厉老鹰来啄似的,是你啊,你还活着啊,听别人讲还以为你瘟病瘟掉了呢!
你才瘟掉呢。根根口拙,吭哧吭哧半天,才吐了这么几个没有创新的词。
嘎嘎嘎!大姣笑起来了像鸭子叫,说,是不是发洋财吧归家来做新屋?
这不是打脸吗,根根面孔涨得绯红。我,我赚不来钞票的,就是归家来看看。大姣一贯来说话怼人,根根怕听,想躲开点。眼睛避开大姣,哪晓得大姣又讲了句不当的话,说,赚不来钞票还来看倒屋,倒霉哦,你准备困天公塌下?这种破屋当鸡宅我都不放心。
根根胆小怕事,能躲能避为上策,但当他连鸡都不如,太侮辱。要不是把学校屋基掏空,学校怎么会倒?学校不倒他家房子怎么会倒?他气得脸若关公,攥着拳,身子抖,脑子里翻江倒海,电闪雷鸣,可一出口,像是装了消音器。他说:都是你害的。声响似只苍蝇一飞而过。却似捅了马蜂窝。大姣两手叉腰,拉开起跑架势,居高临下,呱吱呱吱,一张嘴几张口的效果。我养鸡管你个屁事,你个外姓人高岭收你太给你家大面子,早就好滚出去了,学校早就关门没有人,倒和不倒都一样,那都是我自个村里的事,用不着你个外姓人操心……滚滚滚!滚,滚!她骂到激情处,伸手弹指直指根根眉心。在这个时候,根根的反应愈发迟钝,仿佛就是个天生哑巴,呀呀呀老半天憋不出一个字。那快戳到眉心的指尖,让他心痒痒难受。随手一拂削到大姣的手臂。大姣过于专注手臂的指向,外力介入,失衡,往前一扑,倒了,牙齿扣到石块,崩飞了一个。这还得了,便打几个滚,披头散发,一脸血糊泥女鬼状,尖叫:打人啦杀人啦!

妖不写大开大合,而是以一个较小的切口进入,缓缓展开,用大量的场景细节烘托人物:根根。一个普通得丢入人群里再也找不到的人物,人穷,貌不出众,说不来话,娶个媳妇有难时也是个白眼狼,处于人生低谷时离他而去。其实,根根是善良的,客观现实的残酷,击碎了他的打工发财梦,老家村子的现状让他新的想法,他决定走自己的路,适合自己生存的道路,在老家打理田间地头、果林园地,以及留守老人、儿童和身患疾病的人,也许养老院呀,夕阳食堂啊……根根的眼前,仿佛如黑夜里走路远方出现的那一抹亮光。
妖妖注重小说的细节,场景的描绘,铺场蓄势,水到渠成时,让人顿悟。
小说人物和刻画很成功,笔墨围绕有效人物上下飞舞,就连转场也是那么自然,就如风过无痕,整篇文读下来没有一丝刻意、突兀。语言简洁,无任何拖拉。
妖的小说我欣赏。

读完这篇小说,我突然有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困难莫大于心衰。小说主人公根根因为经历了失业离婚的打击,进而表现出精神颓废、萎靡不振。即使当他后来遇到热情帮助他的发下志明,即使他遇到热情欢迎他归乡的胖子祖山,他依然表现出了一副衰败颓废的状态,直到最后他无意间打开了寄放在老屋的箱子,看到了箱子里的小人书,他才重新真正找回了昔日那个有理想有抱负有志向的热血少年,发展果园、勾画“老人福利院”……当然,这篇小说的闪光点不仅于此。这篇小说,语言细腻幽默,刻画人物鲜活生动,字里行间充斥着真实的乡村烟火气息,欣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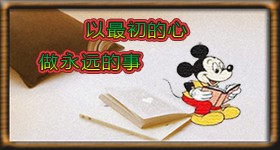
妖怪的小说写得太精彩,包袱留到了最后。语言干净有力简洁,非常有辨识度。小说紧扣当下乡村振兴大主题,妙。佩服,学习!

灵魂对晤、以心悟心,逝水的时光变得更丰盈和饱满。
善待别人的文字,用心品读,认真品评,是品格和品位的彰显!
我们用真诚和温暖编织起快乐舒心、优雅美丽的流年!
恭喜,您的美文由逝水流年文学社团精华典藏!
感谢赐稿流年,期待再次来稿,顺祝创作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