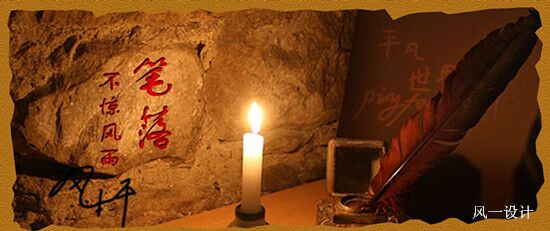【江山·根与魂】【东篱】天后慈航的信仰(散文)
【江山·根与魂】【东篱】天后慈航的信仰(散文)
一
在中国的沿海市镇,差不多都有一座天后宫,宫内供奉着“天后”,又叫“天妃”,用胶东半岛的话称“海神娘娘”。
天帝有天宫,皇帝有皇宫,佛有佛宫,道有“三清宫”,甚至太阳有“日宫”,月亮有“月宫”,自然,海也有宫,曰“天后宫”,天后宫里的海神娘娘叫“林默”,据说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女,从身份上说,为之建宫称后,这规格,高得不得了。这“海神”的身份,不像西方文学里的那些神人,出身高贵,不食人间烟火,就像雅典娜,那是天神的女儿,谁也未睹其面,不知所宗。
天后是中国渔民的神,出身卑微,不慕显贵,人们虔敬其功。这是中国人信仰中最现实主义的色彩,渔人膜拜天后,就像农人尊崇神农氏。这与西方诸神皆神秘有着巨大的区别。
在有着“小香港”之称的胶东半岛石岛,中心区就保留着一座“天后宫”,四围建筑耸天入云,而不侵宫庙,可见人们对其的护敬态度。岂止是留住了一处遗迹,还留下了不灭的信仰。神即人。我这样认知,还有着与天后宫相距十里的“李龙爷庙”可佐证,这个李龙爷就来自邻县文登的南昌山(今天称“回龙山”)。而且,在天后宫之北十里处的赤山,也有“赤山明神”,他的出身,一说是《封神榜》中的王武吉,本就是一樵夫。这和中国文化一直把关公敬为“武财神”是同出一辙。从信仰的来源说,先祖能人的行为,通过传奇而使人建立信仰,从而崇拜之。我特别欣赏作家梁衡在山东长岛看海得出的观感——“神人不分”。(《长岛读海》)如此说来,天后这样的海神,是不孤单的,不必期待奇人唤风唤雨,天后,在石岛,是和李龙爷、赤山明神一起构成了神的体系,这个体系,用今天的话说,是具有草根性的。
将这些材料收集起来思考,我发现,中国民间的神,几乎都是“选举”出来,就像擢拔官吏的“举孝廉”一样,有着广泛的民生民意基础,如此来说,在华夏土地上自古就有着浓厚的民主性。
二
惊春三月,半岛的大天鹅正练飞准备北归,春风从黄海深处袭来,惊动了海澜,一扫冬季的凛冽,渔汛被唤醒,仿佛听见了天后启唇呢喃声,与之互动的是,临宫的海,一箭之遥,波光潋滟,浪随春兴,百鱼近岸,渔港千帆正待祭拜天后之后,鸣笛海捕。我再次走进了天后宫。
三进庙堂式结构,南北进深35米,东西阔29米,全系砖石木结构,布局严谨别致,造型古朴壮观。红木镂空窗户,木质迎面壁,古风浓郁,满院中国风。黛瓦青砖,肃穆雅静;红石铺院,巷陌幽深。青苔些微,自石缝萌出,一睹复苏的宫阙,沧桑历新,就像打开一页历史,历史写在哪?一院皆是,我不能按照从扉页至尾章去读,每一处都抢眼。和今天复建的那些庙宇宫殿相比,这个天后宫是袖珍型,给我的感觉是刺绣在一面绸缎上,据说去年已整修维护,深红上漆,漆光如镜,焕然全新。金字耀光,彩绘栩栩。自改革开放以来,石岛渔协每年都要粉饰一新,为春季渔汛前的第一盛事。斑驳,是历史的样子,而焕新则是今人的态度。
主体建筑“天后宫”,两米出檐,雕拱画栋,彩绘相叠,四柱立面,红漆披光,黑木镶楹联,金字镌其上,难得一见的是有“中联”和“边联”。
中联是——
覃恩浩荡常流海
厚德巍峨独配天
怀念其恩,盛赞其德,瀚海涌流,云天旷渺,受恩天日,行海鱼获,一代代渔人,以恩德表达着自己的信仰,真的是天地可鉴,大海为证。
边联是——
玉炉烧炼延年药
正道修行益寿丹
天后宫,在乾隆年间,山西洪洞县商人王一德为报海神娘娘在海上的救命保货之恩而建,从楹联看见其道家心念,于此说来,这种道家的观念,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信仰,这样的生活意识,一直延续至今,显示出对生命探索的极深程度。道家之道,在于切近真正的民生,不必参透程序,不必咬文嚼字,一顶玉炉,一粒仙丹,都是生命的承载,烧炼的岂止是一丸药,苦求的岂止是一粒丹,敬重庚年,修行正道,这便是人间丹药。
大地有尽头,出海无界,何以为生?心中有一尊海上女神,劈波斩浪,生老病死,用信念来解释,一切都是那么合理,这就是渔人的生活。
“万里波平殿”,视海为池,看波似涟漪。“循池步涟漪,澹然波不扬”,海不扬波,托起生活的希望。
“行宫”,这是以皇帝的配置给天后的寝息之所。“仙姑殿”,云霄、琼霄、碧霄“三霄娘娘”三结义,人间有“桃园三结义”,天上也如是,和谐的信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启迪人们抱团相助。
“观音菩萨殿”,慈悲为怀。“王母殿”,一干女神,护佑生息。“财神殿”,“龙王殿”,“君王殿”,各司其职,佑生殿后。
民间对神主的安排,特别有意思。民间信仰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杂糅性,渔民将佛道神话民间传奇人物里的神,全部搬来,并被俗化,给我们留下了多元的文化,我觉得,西方把一切归于上帝的神念,是一种禁锢,也没有丰富的情趣。活跃的中国民俗文化,一直是推动进步的力量,而不是对归属的简单理解。“人民有信仰”,就是看重信奉、敬畏、膜拜的精神力量,在最开明的政治背景之下,信仰才被尊崇为生活的灵魂。想起泰戈尔的诗句——“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海上渔耕,需要光明的照射,鱼获的丰盈满足,于是,这些被视为神灵的人物,就成为渔人一起讴歌的合唱者,这是渔人的宗教,就像藏人一步一叩首,朝觐布达拉宫;就像穆斯林齐聚麦加,不惧朝觐之旅的遥远与艰辛。石岛的渔人选择了民俗的方式,一点也不乏虔诚的心意。他们为此而郑重,因此而反复,感觉到了生活信仰的无比价值。
在文明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价值趋向,正如余秋雨在《伏羲睡了》一文说的那样,“兴盛的是术,寂寞的是道”。普通的渔人,并不在乎“道”,但在石岛,我听说,过去出海驾船,必须先拜天后,天后属道非术,这种程序的先后说明了什么?这里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道之人方可学道术,有术无道止于术。天后的形象,那就不只是一个平波抚浪的信符了,而是一种慈悲的心怀和修行。
三
在石岛天后宫近300年的历史中,这种渔文化的传承,也像其他文明一样,有着曲折委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一个非渔的人,曾经有幸走进了天后宫。
1975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石岛供销社做售货员。供销社和石岛商店的饭堂就共处天后宫。记得那时就是在正宫打饭,我们端着饭盒,或坐于各宫台阶,或在宫檐下,或边走边吃,巡视各殿,那些海神旧影成了我们吃饭的陪伴。不过,大部分宫内物件,包括神像都置于最后的“万里波平殿”,那时没有这个名字,我曾戏言,比打入冷宫好。
那时,渔业还是以扁舟舢板的方式,捞捕近海的鱼鲜,规模微小,但面对大海,渔民还是坚守祭奠天后娘娘的习俗。我认识当地一个渔人,而且非常要好,曾带我出海,走之前,他悄然进入天后宫,我在宫外候着。他母亲说,拜拜娘娘。
这让我想起父亲的所为,每年的春天,父亲总搬一块石头放在自留地头,他和石头一起对着土地坐一会。走时,把石头留在地头,父亲说,我们就是一块石头,看着土地醒来,不然,土地睡不醒。
出海拜天后,置石于地头,应该都属于一种礼仪,表达的是对大海和土地的虔诚与敬畏,我曾将此归于无聊,其实,错了。人们从未真正解读清楚大海和土地,只能以一种热爱的方式,与之絮语对话,哪怕一句话也没有,心灵在此时,与之交汇,愿望可以借此传递。这是渔人农人最简单的宗教,不是蒙昧,而是粗糙的近似于原始的文明。就像击石取火,那一闪即逝的光,也可以在夜空划出一道口子,留取的是光明的信念。文明不会被隔断,而是延宕起伏的。
也曾引起我的疑问。在十年浩劫中,为何天后宫没有被“破四旧”?一位老职工半开玩笑地说,因为太旧,不值得去“破”,自己就碎了。其实,有的东西是永远也碎不了的。残破的是物象,人们内心的虔敬,只是暂时搁置起来。美好感情的表达,一度被冷落而落寞,但好在时光没有把她给废除,算是在她的历史中暂栖吧。美好的东西,不会沉寂,待她苏醒的时候,又是焕然一新。老职工还有一句话——这不是迷信。开始只是以为天后真有其人,且来自民间。其实这是一个命题,也是我这些年还是关注这座神宫的理由。
荣成首届国际渔民节(1991年)就在是天后宫响起了锣鼓的,这不仅仅是一种民俗文化,而且是将古老的渔家文化进一步广大。天后宫显得局促了,但她留下的渔家对大海的不变信仰,当初,渔民节10万之众,挤爆了石岛沿岸街道,百鱼上岸,万民沸腾。为“天后文化”注入了澎湃的力量,光大了渔耕文化。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册封以建立地位,树立信仰了,更注重的是内涵,信仰变成了梦想,不会等着硕果仅存,而是要创造崭新的成果。
面对渔民节的宏大场面,我并未被场面震慑,我在想,真正的海神,就是这些对大海十分虔敬的渔人,这是一种境界。由一个孱弱的天后,到每一个渔人,都是打捞幸福生活的神。就像作家梁衡所说的,是神,也是人,有信仰的人,就是自己的神。
镆铘岛,大鱼岛,桃园,赤山,三车,牧云庵,朱口,院夼,介口,靖海卫……千里海岸线,穿起了一串渔耕文化的明珠。如果问,渔耕的根在那?天后宫只是一个愿望,真正的根扎在海岸线上。渔民在浩瀚的海洋里,撒渔网,耕海田,他们有一个魂,就是被那个美好愿望牵动着的丰富多彩的海上生活,不必天后举灯了,在多么远的大海上,依然可以找到安全和方向。
2017年,我为荣成二中创作一篇赋文,再次走进天后宫。从私塾教育,到正规的小学教育,这是教育的第一次现代化,民国期间,石岛有了“明德小学”,就是借用了天后宫作为教室。祈祷之声息,而朗朗书声响,天后宫承载的,更加负重,她也是包容的。在“天后娘娘”的情怀里,本就有护佑生存的基因,她听到了孩子们的欢乐,应该就像听到了大海扬声,一定也在助力每个人的成长。“夜浪动禅床”,(贾岛)正作“沧浪吟”。我想,这段天后宫转折的历史,不会被认为不伦不类,反而更有了历史深度和温暖。所谓中国文化的“博大”,不仅是她的宽度,更有一种温度。
其实,石岛天后,就是福建一带所称的“妈祖”的化身。她善航海,乐善施,死后被奉为海神。海上救难,功德胜过法术,宋太祖敕封为“顺济夫人”,元季封为天妃,清时封为天后,她的神位就被三个朝代一步步造就了。一个普通女子,能够走上神坛,创造了一个真正的神话。一个千年的形象,如今还是鲜活的,不能不说是奇迹。因为她宣誓的是人生平安的大主题。据说,凡在沿海,特别是东南亚,皆有妈祖庙,只要有华人在,妈祖就是他们的神。更有甚者,沿海从事渔工的,要成立一个“妈祖党”,果真的话,无需一句纲领,妈祖就是,是永不退位的党首。
落座黄海之滨的村落,有的人家便在后院设“天后祭坛”,甚至塑天后雕塑,渔汛来了,烧香放鞭,以求平安。改革开放,以个人能力购置两对大马力渔船的家庭很多,天后纤指单臂,已经无力保佑,而时代可以为他们的渔船护航慈航。
我还发现,在石岛沿海一线,有着很多奇石奇观,石岛湾的“姑嫂石”,深情地瞭望着海面;石岛西岚山的“儿女石”,可以近望天后宫,远眺大海;大鱼岛山的“望夫石”,临海而不去,出海归来石欲语……这些,我看作是对天后宫文化的补充,慈航之慈,来自女性,传温于石头,辅助地表现天后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派生。我想就是毕加索、米开朗琪罗等大画家在世,也未必可以创造出这样的杰作,因为他们没有站在这个文化的土壤上。
天后宫,让我想到了荷马史诗《奥德赛》里记载的一个传说,那个叫“希萨斯”的要去大海斩妖除怪,和父亲约定以黑帆为沉海,白帆为荣归,归来时,可希萨斯忘记了把黑帆换成白帆,父亲一见,纵身投海,父亲叫“爱琴”,那片海就叫作了“爱琴海”。这是一个“殉海”的故事,换来是只是一个富于诗意的名字;而天后,她所表达的境界,更为深广,襟怀里装着的是众生,交给人们的是一种信仰。
文明在自然面前,往往是不堪一击的,但人类的存在,一直是文明的余绪和光芒在护佑。真正的慈航时代也出自明朝,天后的背景是不可忽视的。
我不能不思考一个现象,自中世纪开始,在欧洲大陆上不断有教堂崛起,成为这个世纪最壮观的风景,但从没有一种力量阻止过炮火的袭击。而此时,中华的沿海,妈祖诞生,开始的是征服大海。人们试图在生命与大海之间找到一种力量,于是才有了“击水三千里”的抱负和真实,其背后的东西就是妈祖信仰。
四
天后宫,就是在过去,也不单单的一种祭祀求佑的所在,其艺术价值也不可忽视。2016年,在专家团队的帮助下,发现了很多未曾示人的秘密,在行宫和斗门处,发现了七组水墨壁画和三组木雕,据考证,属晚清作品。壁画的内容有“温酒斩华雄”“曹公赠赤兔”“千里走单骑”等,这些壁画,应该说是独立于“渔祭”文化之外的,怎样解读呢?民俗,还够不上文物的层次,但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石岛人的人文风情,天后宫容纳了优秀的文化,这种文化,依赖于文学的普及,也表达了渔家对文化的选择性。三国故事,是最接近真实的传奇,传奇里充满了智慧,故事里包含着勇敢,出海的担忧和骨子里的勇敢,是矛盾的,他们要找到榜样的力量,这些壁画,应该可以理解为对渔人远航的智慧补充和行为激励。
璀璨的浪花,漂浮的云朵,在渔人心中,都是诗,在沿海,谁都不会说一句诅咒大海的话,哪怕大海发了脾气,来一场惊涛骇浪,也默默地注视着;哪怕天云密布,要掀起暴风雨,也在默默地祈祷。在渔人的心中,浪花和云朵就是他们的性格,就是灵魂——流浪的灵魂。
在中国,渔耕皆有神佑,龙王是为了布雨抗旱而存在,天后是为水安海晏而站起的,她来自真实,来自另一个神系。
我无法描述天后雕塑的相貌,只记得,看到一眼便是云鬓霞帔。够了,她的美丽,在于一颗祈海佑渔的心。
石岛天后宫,早已成为山东省重点文保单位,妈祖信仰,也已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天后文化说到底还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放在宫阙庙宇里待人观瞻,而是不断进取求索的信仰力量,至少是生活的信符。如今的边陲小镇,它依然怀抱着这处天后宫,小镇的居民,心中怀揣着一个希冀国泰民安的灵魂。
大海无垠无根,一座天后宫,寄存着渔人的信仰,那就是他们在海上讨生活的根。
天后,不是站在江南采莲扁舟上的采莲女,而是踏着巨浪,挥袖抚波,打开一片风平波静的海线航途,身后就站着一位慈航者。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惊波慈航,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壮阔镜头。
2024年3月18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