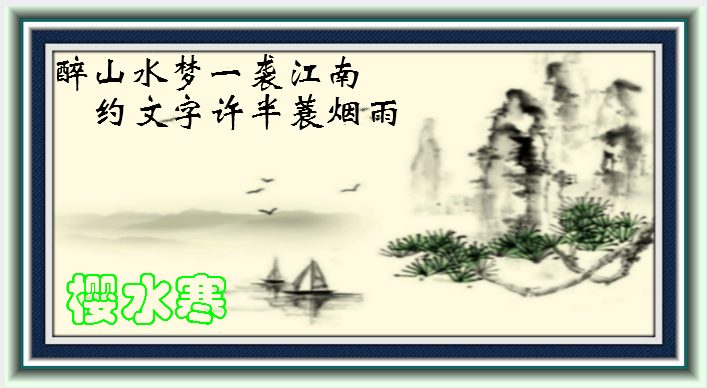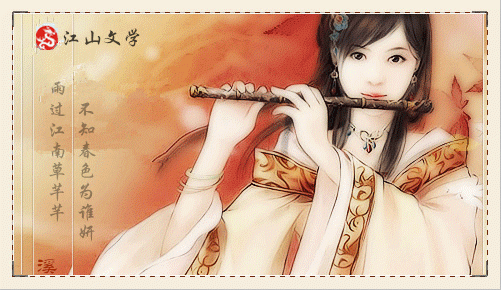【江南】行走在消逝中(散文)
【江南】行走在消逝中(散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光的流失就像奔腾不息滚滚东去的江水,奔流到海不复回。人行走于世间,就好比海滩上留下的一串串叠加的脚印屡屡湮没,如烟的往事正如天边的云朵一样随着岁月的风渐行渐远。行走在消逝中,感情的酝酿和积淀越来越深厚醇正;在消逝中行走,汲取的养分与能量始终在供人们继续前行。忘不了往昔岁月里的那树、那物,还有那人,生命的年轮里铭刻着的是时代的记忆和历史的荣光。
(一)那棵苦楝
记忆中,老家的那棵苦楝,就长在厨房后茅房前的夹角里。
当时,既没有谁种它栽它,也更没有谁护它养它,是它默默无闻地自生自长的。记得那里原是一堆砌院墙无法使用的烂砖头和碎瓦片,像是无法补天的顽石遗留于无人关注的角落。苦楝刚出生的时候,绿莹莹、乱蓬蓬的一丛,好似一个怪物冷不丁地站立起来。它不去讨好谁,也不想得到别人的赞美,只是一味地翠绿葱茏着。
想来,它应是顶着压力来到这个世界的。好则鸡不叨,羊不啃的,没有太多的打扰。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名望和付出是成一定比例的。苦楝在生长中,不知不觉地,树干在自然竞争的环境里脱颖而出。任何事都是如此,一旦有了领头的,便有了主心骨。苦楝集中了力量,蓄足了劲头,不多久,就“噌噌噌”地窜出老高,很快超出了茅房,接着也超出了厨房。眼看着那棵苦楝,就出落成了一个大小伙,身段挺拔,头顶像把打开的绿伞。
每到春天,那棵苦楝也和其他树木一样,沐着温暖的阳光,浴着温润的春雨,享着轻爽的风,发芽长枝生叶。细细的楝枝呈轮生状,皮灰褐色,先有稀疏的短柔毛,后渐渐光滑起来。小小的楝叶对生,呈卵形,叶脉突起明显,具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说来也怪,苦楝好像有自知之明似的,它不与果树争春。待到四五月的时候,它才在碧叶间开出一束束的小花,花瓣白中透紫,花蕊像一条条紫色棒,蕊心好似小喇叭,不见蜜蜂的到来,却也惹人喜爱。
苦楝,花期很长。有的年份能持续开放一个多月,但它并不故作姿态,招人耳目。令人称奇的是它一边开花,还一边结实。楝实又称楝枣,青青的,圆圆的,一嘟噜一嘟噜,隐藏在楝叶的后面。微风一吹,像一串串摇动的樱桃,一个个探出娇小玲珑的脑袋,一副活泼可爱的样子,好看极了。
直到秋末,树叶落尽,圆圆的淡黄的楝枣还结结实实的挂在枝头。有时,蓝灰的喜鹊落在上面,啄几口或抖动翅膀瞪几下,散掉几个枣子来,滚落在青灰色的瓦垄里,呼琅琅的声音清脆悦耳。楝枣结实光滑圆润,黄黄的,亮亮的,非常好看。记得小时候,伙伴们常玩一种游戏,游戏的名称好像叫作“遴窑”,就经常常用到它。
现在,我们那里有时说平均分开,还通常叫“遴窑”。它似乎是一种极为公平的分配方式。其实,所谓的公平,就是大家统一使用一个规则罢了。如果规则就不公平,那也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言了。有时候想想,玩中创造的规则倒是很有意思的,生活的语言也是多么的形象而又富有生命力呀!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棵苦楝树皮纵裂,呈暗褐色,虽然年龄不大,但给人以沧桑之感。它似乎看透了人间冷暖,对地对人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也不太依赖水分和营养,它的抗旱能力可以说是极强的。苦楝的木质纯实,可制家具用作硬料。只是当时的农村,好像有种说法,楝树不能做床。据说,因为“楝”与“殓”谐音,人死了装入棺材叫“成殓”。因此,做床不能用楝木,这是一种民间的忌讳。但苦楝的树枝在那时的农村,也和其他树木一样只能做烧柴。不过,据说苦楝的根叶实和汁液都能入药。我真的很难看出人们要轻视它的理由,常常为苦楝而鸣不平。
至于苦楝苦不苦,我想很少有人去尝它。即便是苦,能治病又有什么不好呢?记得有一次我问父亲,人们为何给苦楝起这样一个名字。父亲笑笑说:“苦也就是一个称呼吧,瓜还有苦的呢?苦大概就是他的特质。” 只有有特质有个性才有它独特的作用,世间才有它立足的一席之地。当时我好像没有弄明白,只是点点了头,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现在想一想,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苦不苦自己知道,不靠天不靠地,不仰他人鼻息,活个自在。保持住自己的本性,说不定对自己对他人乃至对这个世界都还有用,那有什么不好呢?“苦楝”这一名字,似乎在告诉我们,人生在世,不就是需要“苦练”自己吗?
今生在世,我永远不会忘记老家的那棵苦楝!
(二)桑木扁担
在我幼年的印象里,老家堂屋的门后,一直放着根长长的扁担。 那根扁担,我非常地熟悉。它中间宽而鼓,两头扁而尖,五尺多长,桑木做的,浑身上下都像是汗水浸渍过的,斑驳的纹路清晰可见,细密的年轮尽显沧桑,不知里面到底蕴藏了多少故事,凝聚了多少情感。它像岁月长河里的一只木船,漂泊淡定,直直弯弯。
扁担长长呦,岁月悠悠。小时候,篱笆墙边的柴扉前,我总是见父亲早早地扛着扁担走出了家门,很晚很晚才从窄窄的小巷尽头,一步一挪地挑着柴草走回来。那忽悠忽悠的扁担,那由远而近熟悉的身影,常常让我望眼欲穿,常常成为我们姊妹几个心头的期盼。
“ 回来了!回来了!”随着这一声声的呼唤,我们姊妹几个像小燕子似的飞出家门,不等父亲把挑子放稳,就急忙跑上前去寻找好吃的。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笑着说:“娃儿们,都有的。慢些!慢些!”说着便把扁担放在了一边。我们哪里肯听劝阻,各自都如饿虎扑食般地分头找各自的。 父亲的话一点也不假,每次回来,我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或玩的东西。
那个时候,物质匮乏,谁的奢望也都不高,只要满足口欲和手欲就行了。翻来翻去,我们得到的常常是三两节秫杆、一大团毛根、几个枯皮的秋茄子或一捧干瘪的花生。当然,有时也会有细长的烤红薯、蛙皮甜瓜、线穗靑梨、红嘴桃子等。待我们都吃够玩够闹够了,父亲才一边收拾,长的喂羊,短的剁剁喂猪;一边安排我不要忘记把他的扁担放在堂屋的门后。
记得有一次,我问父亲:“这扁担是啥时候的古董呀?”父亲微微地一笑,慢悠悠地说:“你猜猜?”我说:“您小时候的吧。”父亲说:“比我年龄还大,那是你爷爷留下的!当年小日本侵略中国,蒋介石扒开黄河口,滔滔的黄河水淹没了我们的家乡,你爷爷就是用它挑着全部家当去南乡逃荒的。后来,你爷爷又是用它一担一担地挑着建起了我们现在这个家。”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看到那根桑木扁担就成了父亲随身不离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白天下地,父亲总是用它翻红薯秧,担粪肥,挑粮种,抬土筑坝。累了,把它往地上一扎,靠着小憩;闲时,把它往树边一放,做个枕头。傍晚回来,用它挑水,背柴禾或担起劳动分得的些许收获。夜里,看场护院,父亲也是常常带着它。甚至有时种菜画沟、打枣敲梨、晾晒衣物等也能用到它。它简直就像一根金箍棒,可以变作花样用。从那时候起,我对扁担就怀有一种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感情。
要说得具体些,它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的农村,家家户户没有烧的,都需要天天拾柴禾。因此,扫树叶、捡柴草或剜麦茬、搂豆叶,就成了孩子们常干的活儿。我们姊妹几个都深知父母的劳累,这些小活就经常争着干。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姊妹几个,每次拾的柴禾总是堆得高高的。由于当时家里没有架子车,通常只好等父亲收工回来,无论早晚,都要一大捆一大捆地用那根桑木扁担挑回家。
记得有一次,我跟在父亲的身后,看着他一走一颤、步履艰难的样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勤快究竟是对还是错,心里有一种极为矛盾的感觉。不拾吧,家里要烧火;拾得多了吧,说实话真的不想在劳累父亲了。我就不由自主地说了声:“看把您累的,下次我们都少拾点。”父亲初听有些疑惑不解,回头问:“为什么?”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没想到父亲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后说:“傻孩子,难得你一片苦心,再累我也很高兴!”
后来上了学,课本上有篇课文叫《刮扁担》,我至今还能熟练地背出来。“刮扁担,刮扁担。灯花闪,刨花卷,激起我心中浪花翻。当年烽火革命路,有多少扁担压上肩。担粮担菜担子弹,担风担雨担艰险。担来老茧摞新茧,担来新山新水艳阳天。如今虽说两鬓白,钢肩铁臂胜当年。老师长,新学员,月夜房后砍桑木,嚓啦嚓啦刮扁担。”那是一首现代诗歌,节奏鲜明,读来朗朗上口。由此,我对扁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扁担不仅是一个家庭父子亲情相传的维系,也是一个国家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不朽的精神支柱。
渐渐地,我长大了,父亲却老了。记得有一次田间浇水,看着父亲踩着田埂挑着水桶颤悠悠的样子,我不由得接过扁担。父亲说:“一根扁担,就是一副担子。既要挑得起,又要挺得住;还要向前看,甩开膀子,迈好步子;昂起头,不停歇,目标专注,勇往直前。”我大声地说:“记住了!您放心吧!”
时间过得飞快,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他从爷爷那里接过的那根桑木扁担到我这里也算打住了。不知为何,生活中,每当我遇到困难挫折心灰意冷的时侯,父亲教诲的话语总是萦绕耳畔。我想扁担作为古朴而简单的劳动工具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但扁担中所蕴含的那种担当坚挺执著奋勇的精神,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哪个人,又能少得了呢?
扁担长长,我怀念那段过去的时光;岁月悠悠,我更向往美丽如花的未来。
(三)蒜薹·黑穗·韭花
记得小时候,有几种东西,好像不是正货,只是意外所得,但吃起来又方便又有味,觉得很是高兴。这其中,最有代表性、记忆最深刻的当数蒜薹、黑穗和韭花了。
每到农历三四月间,青青的蒜苗渐渐地长高了,忽然有一天,嫩绿的叶片中露出个小尾巴,不几天连泡带秆都挺了出来,这就是蒜薹。蒜薹是蒜的花茎,又称蒜毫。小时候放学,下地割草,捎上块剩馍,没有菜,这刚出的蒜薹正是现成的就馍菜。夕阳西下,晒了一天的大蒜,用手掐住蒜泡与蒜薹的连接处,悠着劲一抽,白亮亮的蒜薹“吱溜”一声便拔了出来。有时由于用力不均或使蛮劲硬拽,一连拔断几根也是常有的事。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用铲子轻轻划开一条细线,将蒜薹剥出,这样就有些费劲,而且不利于大蒜的后期生长。
那时候,到处都有水,有水就是清的。抽出的蒜薹在水里随便一洗,再往衣服上一擦,挎着个草篮子,一口馍一口蒜薹地啃了起来。青嫩的蒜薹,脆脆的,辣辣的,小朋友们个个吃得大快朵颐,津津有味。等到蒜薹大下的时候,一时吃不完,还可以装进塑料袋放在窖里,能过上好长时间,色泽味道都不变。除了窖藏之外,家家户户还都腌上一大盆,随吃随拿,非常方便;腌过的蒜薹,吃起来更加津道、香辣味也更足。记得那时候,我们姊妹几个都爱把刚抽的鲜嫩的蒜薹切成段,拌上盐,略微点上些香油,生调着吃。香甜脆辣的味道,至今难忘。
记得还正吃着蒜薹呢,小麦就开始吐穗扬花了。等到麦梢发黄的时候,就会发现滚滚的麦浪中,有些靑干绿鞘裹挟着一些黑黑的麦条。这些黑色的麦条,就是通常所说的黑穗,我们当地叫它“乌麦”。乌麦其实就是一种坏麦,黑色的麦穗中没有麦粒,但嫩嫩的,津津的,很好吃。在麦未熟的时候,我们下地割草的玩孩子就到处找着吃,而且这种乌麦的麦秆还能用来喂羊,真可谓一举两得。记得那时候还有个俗语,好像叫做:““麦种浸得好,来年乌麦少。”可见,乌麦出现的原因主要在麦种。
现在都讲究科学种田了,选种育种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乌麦根本就没有再出现的机会。话又说回来,在难以填饱肚子的时代,吃乌麦也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如今一年四季,吃不完的白面,谁也不在会想着吃什么坏麦。不过,吃过黑穗的人,回想起当年吃黑穗时的情景,一定还会还感到兴味悠长。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哪怕是痛苦的过去,回忆起来也是别样的美丽,不是有诗人把它叫做“美丽的忧伤” 或“忧伤的美丽”吗?
还有一种东西则更绝,它是在老了老了的时候,高高地挺立起来,然后在顶端用薄薄的膜打个大大的包,青青的蕊头结着小小的白花,掐下来腌上,是一种极不错的菜,这就是韭花。韭花又名韭菜花,也称韭苔,它是韭菜秋天里起梃老了之后生出的白色花簇,一般多在欲开未开时采摘,嫩嫩的花苞里是一丝丝靑蕊,像灯丝一样还有个米粒大小的青豆。采摘后,加入辣椒磨碎,腌制成酱,可以作为食用的一种佐料,微辣中韭香四溢,味道美极了。现在虽然有些地方还有,但已经不是传统的制作方法,失去了原有的味道,或许是人们的口味变了,总之,吃起来感到大不如前了。
说起韭花来,据说还给书法有着不解之缘。闻名于世的五代杨凝式的《韭花帖》就颇具传奇色彩。杨凝式是五代时的五朝元老,官至太子太保,一生狂傲纵诞,人称“杨风子”。有一年秋天,他一觉醒来,已是午后,觉得有点饿,这才想起中午没有吃饭。恰在此时,宫中给他送来了一盘韭花。不知是饿了,还是韭花做得地道,吃起来特别美,格外难忘。
为表达感激之情,杨凝式当即写了一封谢折,其中有“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然后派人送往宫中。谁也不会想到,一盘简简单单的韭菜花,成就了一封不经意的手札,而正是这封手札最后竟成了“天下五大行书”之一,杨凝式因此而名声大振,这种双重的幸运,可谓空前绝后。
随着时代的发展,蒜薹黑穗韭花这三种意外之物,有的已经彻底消失,有的还在延续,有的却大行其道。事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本质性差异,只是人的口味在变,人的思想在变,因为社会在前进,一切都需要随之而变,变是这个世界的永恒主题,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在时代的变革中有时不免回头看看曾经的浪花,心中就会有一种甜美的感觉和淡淡的忧伤。
岁月啊,苦楝和桑木扁担,这些陈年的记忆似乎带有某种悲情和伤感,可仔细想想,没有昔日的苦,哪来今天的甜?只有经历了痛苦的磨练,才能享受得起幸福的喜悦。蒜薹、黑麦和韭花,它们都是先人们在苦难中的伟大创造,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正货和歪货之分,只要我们正确对待,真诚地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永远值得我们回忆。虽然过去的永不再来,让我们行走在消逝中,学会珍惜;在消逝中行走,步履更加从容而又豪迈。
【江南约稿】同期同题第八期《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