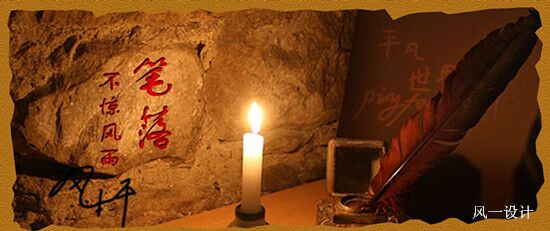【东篱】浇地(小说)
【东篱】浇地(小说)
![]() 太阳在头顶上高悬着,任凭怎么努力,也驱赶不走旷野的寒意。连绵的田野,除了蔫头耷脑的麦苗,满目萧瑟。一条石砌的水渠,自远方蜿蜒而来,流动的水在阳光照射下像跃动的白蛇。
太阳在头顶上高悬着,任凭怎么努力,也驱赶不走旷野的寒意。连绵的田野,除了蔫头耷脑的麦苗,满目萧瑟。一条石砌的水渠,自远方蜿蜒而来,流动的水在阳光照射下像跃动的白蛇。
一
村里辈分最高的永新爷爷戴着绒线老头帽,穿着黑夹袄,腰里捆着一根麻绳,鼻孔下挂着清涕,坐在横放地头的铁锨把上。他佝偻着身子,用黝黑皴裂的手熟练的装填上紫黑锃亮的旱烟锅,侧着身子点燃,先喷一口烟雾,再响亮的擤一把鼻涕,然后把手指在黄胶鞋的后跟上来回几下揩干净。这已不知是他抽的第几袋烟了,烟袋下吊着的烟荷包瘪瘪着,随着风荡来荡去。自黎明破晓,永新爷爷便守在这里捱号浇地,来的时候田野还披着薄雾织成的轻纱,现在上游的地差不多已经喝饱了,渠水在他眼前汩汩地向下游流淌。
今年的天异常干旱,自播种以来,麦子便在绝望中挣扎求生。它们艰难地抽出柔弱的嫩芽,却又在干裂的土地上痛苦地蜷缩,大片的麦田远远望去,就像是稀疏的松针随意插在地面上。水,在这个时节显得尤为珍贵。为了这保命的一遍水,大队里一个月前就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水要想方设法协调上游的水库,否则很难打开库容本就不足的水闸。村北干渠年久失修,那些兔子洞、老鼠窝还有龇牙咧嘴的豁口得补上。更重要的是,水一来,还要派人昼夜分段把守,它穿山越岭、穿村过寨,说不定哪一段就被截胡喽。唉,金贵的水啊!
渠里的水不急不躁,毫不怜惜人如麦地一样的焦渴。眼看着上游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了,等候多时的永新爷爷把麦地的水口开好,耐心地等着水淌下来。太阳一蹦一跳地越升越高,已经过了早饭的时辰。上游的最后一个人终于浇完了,轻快把围堰打开,水便顺着渠欢快地流淌了起来。永新爷爷双手拄着锨杠,眯眼看着水渠里的水越来越近,三十米,二十米,十米……眼看就要流到地头了,一个人影一闪而过,挡住了他的视线。
“大爷爷,你也刚来啊,正好水淌过来了,我先浇了哈。”来的是二孩,他家的地紧挨着永新爷爷的上游。二孩说完,没等永新爷爷说话,自顾自地一铁锨下去,飞快地在地头挖开了水口,转手在水渠里设好了围堰。水刚好流过来,不管不顾地顺着二孩开好的水口流进了地里。二孩惬意地看着水流淌着,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支递给永新爷爷。永新爷爷摆摆手,默默地把烟锅伸进烟袋里装了一袋烟,转过头蹲坐在铁锨杠上吧嗒吧嗒地吸。二孩讪讪地,捏着烟顺着水渠朝下游溜达过去。
二
浇地的人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他们肩上扛着铁锨,迈着填饱肚皮后不慌不忙的步伐,彼此大声招呼着、戏谑着。远远听得见一阵哄笑,宝庆家的像个火球一样顺着水渠滚动过来。她个头不高,长得肥胖,穿着鲜亮的大红毛衣,在窄窄的水渠沿上挓挲着两手走成了企鹅。
正在溜达的二孩看见宝庆家的,便斜着身子站定了笑。“笑什么笑,不认得啊!”宝庆家的冲着二孩喊叫。“昨天还认得来,谁知道过了一夜不认得了呢?”二孩戏弄宝庆家的。“滚一边去。”宝庆家的惦记着浇地没心思给二孩开玩笑,一边骂一边走。“你慌啥,我浇着呢,我浇完了还有永新爷爷。”二孩站在渠沿上挡住宝庆家的说。“哎,你不是在我前头刚来吗?怎么一来到就浇上了?”宝庆家的疑惑着问二孩。“来得早不如来的巧哦,我一来到就赶上水了。”二孩放小了声音说。宝庆家的看了看坐在地头抽烟的永新爷爷,远远地打了个招呼,心里明白了几分。听到二孩的话,故意放大了声音嚷嚷:“二孩啊,你这个不要脸的!你看看永新爷爷等了多久了?说不定连早饭都没吃!你眼瞎啊?你吃饱了喝足了,一来到就浇上了,好事咋就都让你赶上了呢?”“你瞎咋呼啥也,就你能!我看看浇到哪里了。”二孩把烟屁股扔到水渠里,折转身子,边说边往地里走去。
宝庆家的是村里有名的泼辣婆、心眼子包,虽没上过学,嘴皮子却磨得比刀子还利,心眼比箩筛孔还多。她孩子多,家境一般。前些年计划生育超生被乡里罚款,碰上这样的事,一般人都当“超生游击队”去了,她不光不躲,还天天跑到乡里又是缠又是闹,硬是破天荒地给乡里打了欠条。如今孩子长大了,该谋划着赚点钱了,就跟别人学着种上了蔬菜大棚。种了几年,日子总算好过点了。她有一句“名言”:“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养猪卖菜弄点钱,村里人除了手头留点零花钱,都存到信用社生利息。宝庆家的和别人不一样,她手头不留活钱,有多少钱存多少钱,并且一存就存定期。碰上花钱的事,她一点也不犯愁,跑东邻西舍去借。她大娘啊,该死的大丫头非得买个啥,俺家的钱还有一个月到期,先给你借一百,一个月就还给你。或者是她二婶啊,俺娘家谁谁谁病了,过去人家对咱不孬,咱得去看看啊,俺家的钱还有几天就到期,这时候取不就亏了么?先从你这里借二百。久而久之,村里人也都知道她这个德行,看在她有借有还的份上,也不好意思点破她依旧借给她。手头宽裕点了,她还赶时髦。流行戴手表的时候,花几十块钱买了块锃亮的坤表戴在手腕上。她不识字,不会看着指针计算时间。有人问她几点了?她就装模作样地看看表说,昨天那个点啦!时间长了,就成了全村的笑话。
二孩走到地头看了看,然后调转身子坏笑着朝宝庆家的喊:“大嫂子,太阳老高了,你看看几点啦?”宝庆家的一声不吭,随手从地上摸起一块土坷垃,猛地朝二孩砸过去。二孩跳着身子躲闪,一脚踏进了刚刚浇过的地里。下游的几个人把铁锨杵在地里,抱着锨把看热闹,看见二孩拔出了一脚泥哈哈大笑。笑完了,便都不由自主地朝上游水渠里看,恨不得用眼神把渠里的水勾过来。
三
永新爷爷又点了一袋烟,刚吸了一口,抬头看见二孩光着脚板吧嗒吧嗒向上游跑去,一边跑一边叫唤:“谁把我的水截了?我还没浇完呢!”永新爷爷也慢慢地站起身,深一脚浅一脚地挑渠边能落脚的旱地往上游走。渠里的水越来越浅,浅得快看不见流动了。跑到支渠和干渠连接处的二孩大声喊叫起来:“哎,快来人啊,大沟里的堰塌啦!”正在深一脚浅一脚走着的永新爷爷听见喊叫,把手中的烟袋随手丢到地里,朝后边的几个人挥了挥手,吆喝了几嗓子,不再管湿地干地一起朝二孩那里跑。
干渠是东西走向的主渠道,西头连着水库,自西向东七拐八绕地连着十几个村子的农田。轮到哪个村浇地,哪个村就派人把干渠里的水截住,引到村里的支渠里面。水多的时候,干渠里的水不用截死,可以几个村同时用水。今年水少,村里只能把干渠截死,这样才能保证支渠的水流量。干渠的围堰一旦塌了,向下一泻千里,支渠里一滴水也没有。村里截水用的是石块和沟沿上的草皮泥,两种东西混杂交错着摞在一起,形成一道半沟深的围堰。大概是草皮泥被水冲刷掉了,相互依存的石块不再稳固,现在都七零八落地躺在渠底下,无奈地放任金贵的水自由自在地从身边汹涌流过。
“唉!真倒霉,眼看着快要浇完了,最后一垄沟就差半截,你说是堵还是不堵?”二孩沮丧地抱怨着。宝庆家的恨恨地嚷道:“咋不堵?你这还没浇完呢,你就是浇完了也得堵!永新爷爷还没浇呢,满仓哥还没浇呢,我还没浇呢!你还等着大队里派人堵啊?等大队里人来了,水库里的水都淌干了,还浇个屁?”
“堵、堵、堵,把你的嘴堵上!”二孩没有好气,然后又嘟囔:“水淌得这么急,手头又没东西,怎么个堵法?”旁边站着的满仓不等二孩把话说完,就心急火燎地对他说:“石头不是都在渠底下吗?你到地头上抱几捆玉米秸来。”满仓一边说着,一边用铁锨拨动着渠底的石块。石块太大,一动不动。二孩飞快地抱来几捆玉米秸扔在渠堤上。
“看样子得下去,干等着白搭。”满仓边说边撸起裤腿,半边屁股坐在渠堤上,用一只手撑着,试探着放下了一只脚。刚碰到水面,却像伸到油锅里一样,猛地弹了起来,呲牙咧嘴地叫:“冰渣凉,冰渣凉,一沾水凉气就钻到骨头里了。二孩,村里不是有闸板吗?原先堵水都是用那个的。”
永新爷爷正从路边抱来几块石头,气喘吁吁地说:“原先浇地水多大啊?不用闸板根本堵不住!这回哪有那个水势?闸板放在这里,还怕半夜给人偷走喽。上年不就丢了两个?那都是好木料打的,又厚又沉,有的人就是不能看见东西,不赚点便宜就跟吃了大亏似的。这倒好,弄得都不敢用了。回去拿来来回回的,咱的地还浇不?满仓你扶着我点,我下去堵!”
“水冰渣凉,你老人家受得了吗?我跑得快,我回去拿!”二孩紧赶着永新爷爷的话茬。永新爷爷说:“还不到腊月呢,还能多凉?四三年寒冬腊月里,半夜蹚水到河那沿摸鬼子炮楼都没觉着凉。”永新爷爷说完不再言语,把鞋甩到一边,满仓和二孩赶紧上来扶着他,宝庆家的慌里慌张地跑到不知谁家的地头上,又拿了两捆玉米秸。
永新爷爷扛过枪打过鬼子,摸鬼子炮楼那次因为受了伤便留在了村里。他的故事在村里流传的不多,也就上点年纪的晚上凑在一堆唠嗑偶尔说说,年轻人大多不知道。在街坊四邻的眼里,他就是个沉默寡言、忠厚老实、勤劳能干的老头儿。前几年国家对当过兵打过仗的有照顾政策,有人听说了提醒他去上头找找,没料到他老人家竟然来了这么一句:“找啥?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一块打鬼子死了的好几个,连家是哪里的都不知道,我没死还孬吗?要找也该他们找,叫我找我都觉得丢人!”打那以后,村里好多人背地里称他“憨老头”,也有不少人闲聊时感慨:“永新爷爷啊,人家那才是正儿八经当过兵打过仗的!”
正是深秋时节,渠边的杨树枝杈上孤零零地挂着几片坚强的树叶,树底下一片金黄。一阵风刮过,树叶一窝蜂地往渠里跑,浮在泛着寒气的水面上飘向远方。
永新爷爷裸着的腿又干又瘦,上面满是青筋,就像蚯蚓附着在上面。他蹒跚着,将渠底七零八落的石头一块块搬过来,猫着腰垒成一堵石墙,然后贴着石墙把一捆玉米秸摁到渠底下用脚踩平,压上几块平整一点的石头,摞完一层再压一层,一直摞到第五层,渠里的水位才缓缓地升了上来。水涨到了永新爷爷的大腿上部,打湿了他高高卷起的裤腿,他浑然不觉,继续指挥渠堤上的几个人弄草皮泥堵漏。满仓和二孩站在渠边的田埂上挖草皮泥,宝庆家的手忙脚乱地把草皮泥递给永新爷爷,永新爷爷把草皮泥贴着玉米秸用脚踩实。围堰的漏洞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慢慢地只剩丝丝缕缕的渗漏,支渠里的水又欢快地流淌起来。
四
永新爷爷从渠里爬上来,摘下帽子擦干腿上的水,接过满仓递过来的烟夹在耳朵上,坐在渠堤的石头上喘了一会儿。宝庆家的把永新爷爷刚才扔到地里的鞋拿过来,放在永新爷爷的脚底下。永新爷爷没穿鞋,赤着脚拎着鞋慢腾腾地回到地里。二孩的地已经浇完了,他叼着烟扛着铁锹优哉游哉地回家了。水顺着渠流下来,马上就要淌到永新爷爷的地里。
宝庆家的急慌忙促地跑过来,耷拉着手站到正在修整水口的永新爷爷面前,支支吾吾地说:“大爷爷,忒不好意思了。我寻思着早浇完地回去给大棚掀苫子的,没猜思倒是耽误了这么长时间。日头老高了,苫子不掀不行了。”说着,扭头看了下游的人一眼,接着说:“要是回去掀完苫子再来,看这样今天恐怕浇不上了!要不我先浇着?你回去换个衣服别冻着喽!”宝庆家的地就在永新爷爷的下游,中间隔着几个垄沟。永新爷爷一边听着宝庆家的试探着说话,一边把正在修整的水口顺手扒拉几下堵上。宝庆家的眼瞅着永新爷爷手下的动作,喜得眉毛往上翻,害怕永新爷爷反悔似的,忙不迭地往回跑,一边跑一边说:“大爷爷,你可帮大忙了,整个庄上就数你好,等我大棚里辣椒子长大喽,给你送一篮子哈。”永新爷爷轻轻地摇了摇头,不再言语。
渠里的水“三过家门”般带着一丝留恋,在永新爷爷的目光注视下顺流而下。日头已经偏西,远处人声嘈杂,田野不再寂静。他把铁锨平放在地头上,小心翼翼地坐在上面,把湿透的裤腿放下来,接受太阳的照晒。蓝天飘着几朵白云,金色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在黄土和麦苗的映衬下,他像一尊在旷野里打坐的佛。
宝庆家的回来了,她应该是看看她家的地儿浇上水了没有。
满仓笑着问:“你家大棚子里的辣椒子长大了么?给永新爷爷带了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