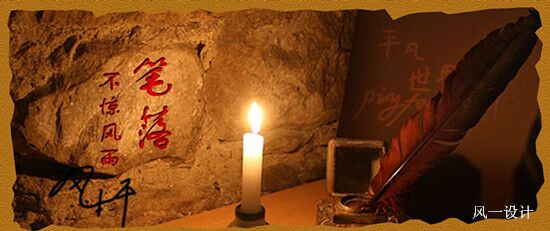【东篱】猪,更新了年味(散文)
【东篱】猪,更新了年味(散文)
一
龙年马上过去,蛇年快步跟来。农村里,年的氛围一般是从杀年猪开始。
杀年猪,是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年俗,据查,至少也有2500年的历史。起初源于古代岁末年初的祭祀活动,祭祀品包括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可因为马要载人载物,牛要耕田耕地,猪和羊就成了首选,渐渐就有了杀年猪的习惯。二师兄——猪,便当上了推进年味的主要功臣。
中国人养猪,历史悠久,从先秦时期的甲骨文的“家”字看,人们就已经开始养猪,岁末“蜡祭”中,猪便是常见贡品,祭祀完毕将其分食。唐宋时期得到流行,《云南志略》中记载“每岁冬月宰杀年猪,竟相邀客,请无虚日”,那时杀年猪不仅仅只是为了祭祀,还成了人们庆祝新年到来、祈求美好生活、宴请亲朋好友的一种方式。明清时期,杀猪更为普遍,但已经在各个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年猪文化特色,如灌香肠、腌腊肉、炕腊肉等。近代,新中国成立初,农户执行“购一留一”的政策,按每家人头多少交给国家购猪后,再自己宰杀年猪过年。
猪,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一部记录中国历史文化的“活历史”。中国的饮食文化,无论南北,也少不了猪的显赫位置。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猪在国人的心目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老百姓的餐桌上,猪肉的出镜率是最高的。过年的大餐,少了猪肉,便没了年味。
猪,生来就是被吃的。因此,杀年猪,冠冕堂皇。大家吃肉,名正言顺。
二
在我现有人生几十年的印象里,杀年猪在不断更新,年味在不断更新。
“大人望插田,小孩望过年”。在我小的时候,盼望过年是写在脸上、挂在嘴边、且乐意表现在行动上的。为了让肩负希望的猪长大长肉长膘,父母会找来世上所有的漂亮话,鼓励我放学后扯猪草、剁猪草、煮猪食、给猪食。为了满足自己贪吃的欲望和五脏六腑沾点荤腥的需求,我是乐此不疲,十分卖力。每天有事没事看看猪,盼着过年的美味不辞辛苦地劳动。父母越表扬我,我越是劲头足、干劲大。
那时候,人也缺吃,猪的生活只能是勉强对付。可越靠近年,大人也着急,人们便越将“三十壮年猪”发挥到极致。极致,也只有给猪吃人剩下的仅有的红薯根、瘪头歪脑的南瓜、死藤冬瓜等。扯煮草尽量扯嫩点儿的,剁猪草尽量剁细点儿,煮猪食尽量煮烂点儿,汤汤水水尽量给它多吃点儿,等等。尽可能地巴结二师兄多长点肉,不过,结果是差强人意。“生嘴的要吃,生根的要肥”——二师兄在背地里说不定不知嘀咕了多少回呢。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九九严寒的开始,北方人这天放肆地宣扬吃饺子、纳百福、祈求交好运。南方人却是杀猪宰羊、准备年货的节点。我家每年养两头猪,大的壮的,只要满了131斤,就当购猪交给国家。自己留小的,有几十百来斤就算不错了,不过还要卖一些肉出去,给我们买几尺布做新衣服过年。孩子们的“望”过年,就是望着吃望着穿。
杀年猪这天,像过节一样。妈妈早早的就打发我挨家挨户的去接客——院子里的族人、关系比较好的人、曾经帮助过我家的人等等,妈妈会交待清楚,并一一接到。约好时间一同吃杀猪饭。那个年代,一年四季也难得吃几次肉,杀猪的这天,可以勉强解馋。我家好几年,都是吃了一顿杀猪饭、卖了一些肉后,就没多少了,过年的肉紧紧巴巴。不过爸妈马上就会说:“明年喂大猪,叫你们解馋、吃腻!”我们就在这无限的希望中一天天长大。
屠夫是我本族出了五服的大哥哥。放出来准备宰杀的猪,见势不妙奔命地跑,可人要吃它,岂肯放过!怎么样也跑不过三五个大汉的围追堵截,很快屠夫的尖钩一下就钩住了猪的下巴,它挣不脱,只能使劲叫唤。人们提尾巴、扯耳朵、搬前腿、捉后腿,你推我搡。汉子们在屠夫的指挥下,将它很快摁倒在事先准备好的门板上,用身子将猪压住,猪头伸向门板的边缘,接猪血的盆快快递来。只见屠夫对准猪的咽喉猛的一刀,用力捅进心脏,猪血随之喷涌而出,猪的叫声由强变弱,由大到小,直至止声,不再动弹。
牲畜在老百姓心中属于“血财”。杀年猪是有很多讲究的,一刀见血,顺顺利利,猪血多,很快喷出,且喷得满盆都是,甚至地下也溅了一些,就预示着来年红红火火,猪财运好,主人会非常高兴,旁人也会恭维送上祝福语。如果屠夫一刀走偏,没将猪杀死,还要补上一刀,血也少,觉得这是不祥的征兆,主人会很不高兴,心中便有了疙瘩,担心第二年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不过,有反应快的人打圆场:“补一刀,灾祸消,日子越来越红火!”主人赶快递来烟袋,叫上抽烟的人,滚上一支喇叭筒的老烟,吞云吐雾,心情会随之好转。你一句我一句,此时只有吉利话搬出,笑声连连。大家看着屠夫烫猪、扯毛、刮毛、用挺竿从猪的腿部开始,将猪身上经络横一下直一下通透、用口吹气、将猪的毛细血管膨大。此时,像变戏法一样,肉眼可见的速度,猪马上变得又肥又大。先前只有百十来斤的猪,瞬间涨大成看起来有一两百斤的大肥猪了。大家满意地瞅着猪,看着屠夫继续将猪身上旮旯部位的细毛清理干净——原来吹气将猪涨大的目的就是这样哦,这也太有智慧了吧。大人说话,我不敢插言,但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也是长了见识。
杀年猪,吃杀猪饭,年的味道越炒越浓,肉香四处飘散。在桌上推杯换盏,将年的氛围渲染,将年的脚步推近。
三
责任下户后,不再交购猪,每家每户的年猪也变大了。外面的野猪草还是同样扯,但自己还大量栽了一些,比如红薯藤、萝卜菜、白菜、青菜等。一般寒露过后,便陆续割红薯藤、挖红薯喂猪,还将田埂、荒坡、池塘边等栽的南瓜摘来,煮猪食时与猪草掺在一起,与糠和匀。有了美味,猪吃食便是拍拍打打连声“咚咚咚”,恨不得将槽底“咚”穿。那时,我读书寄宿在学校,每星期回家一次。每次我都会专注一会猪,看猪大有胃口地吃食。母亲会在旁边欣慰地说:“照这样长,今年可以杀一百多斤肉,自己留一半,卖一半,也不错了。”我知道,卖的一半,是给我读书的。我心中温暖着,对未来充满希望,信心十足,同时压力也在无形中加大加重。
父母专门挑了周末我回家的日子杀年猪,回学校时还给我炒了一大罐头瓶的肉带着,说往滚烫饭里一摁,少许就加热了。我是家中的娇娇女,是名副其实,毋庸置疑。
只几年的工夫,杀猪的工具改进了不少。我家也专门制了个漂亮的杀猪澡盆,用桐油油得是锃光瓦亮的。以前都是借别人的,或者因为猪小,干脆搬出煮猪食用的大锅或者大水缸来烫猪;屠夫的刮刀更大了,屠夫说用力更称手;屠夫的刀多了好几把,不用再到农户家中找刀用;疏通经络的挺竿有长的也有短的。屠宰用具,以前因为不多,用篮子提着出门便可,此时却要挑着行走了。
四
我终究没有跳出农门。成家后,继承了父母的优良传统,辛勤劳作。遵循“富要读书,穷要喂猪”的原则,希望摆脱贫穷。起初,无论家中怎样穷,每年养一两头猪是必须的。没钱,会到熟人家赊小猪。“迟约日子早给钱”是我的做事风格,最迟到下半年卖了猪卖了肉是必须还账的。因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每年,我家都有杀年猪,只是大小不一。炕腊肉,灌香场等也是自己动手,保证一家人的口福。后来买了冰箱,也就很少进市场买肉。
现在,规模化养猪场多了,农户喂猪的越来越少,甚至不少老百姓家的猪圈也没有了。许多家庭不缺钱用,吃肉随心所欲随时可以买。不过,我家一直还养猪,每年冬至过后,也请屠夫到家里杀年猪,有时候还卖一部分肉来贴补家用。
现在的屠夫,也是与时俱进,制作的杀猪工具越发齐全:大澡盆、小澡盆、铁架、门板、夹猪用带有轮子的铁夹车(不用多人捉)、锅炉(农户小锅小灶的多,烧水用)、打气泵(不用挺竿不用人吹)、液化气喷火枪(刮不干净的旮旯里的毛,可以烧)等,是一应俱全。所有的工具用三轮车或者小四轮拉着走,真方便。
当然,大型屠宰场是另当别论。常在手机电视的视频里见,这边的猪,排着队伍摇头摆尾、生龙活虎进去;数分钟,那边的肉,已经是随着传输带出来。老百姓的年肉,有的在农户家订购,有的干脆在市场上买,不费多大的劲。
猪肉,在人们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消减过。哪怕现在的食品多如牛毛,但对猪肉需求只增不减。猪的位置,始终没有被其他动物超越。它始终有着价格优势、供应稳定、营养丰富、口感丰富多样、风味颇具特色、适合加工成多种口味的食品等等优点,而遥遥领先。
猪的优点,以我水平,一句两句也说不清,猪肉、猪毛、猪皮、猪骨,哪一样都是宝,它给人类做出的卓越贡献,不是一篇文就可以说明白的。反正该养猪的还是养,该吃猪肉尽管吃,该请屠夫来杀过年猪的还是继续,这个传统还会将继承,且发扬广大。吃猪肉,仍然会将年味推进,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