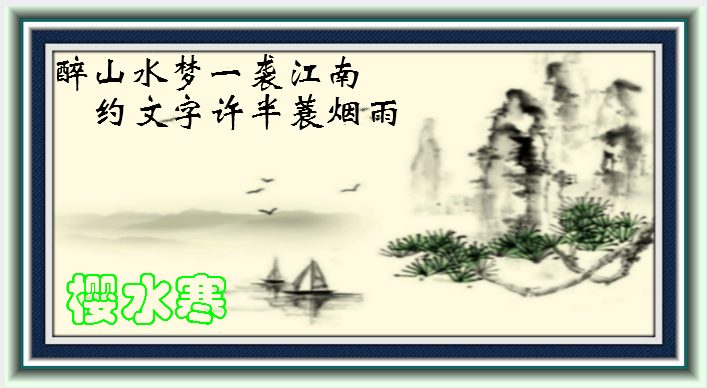【暗香】做糖(散文)
【暗香】做糖(散文)
入了冬,好吃的嘴就不自觉的吧嗒起来。馋两样东西:年糕和炒米糖。这些老味道,已消失了多年,只能网购找个回忆。相比习惯了做主食的年糕,随时能来一口的炒米糖,更让我心心念念。
二十多年前的这个季节,入冬后连着十几天,村里每晚都响起咚咚咚的声音,从各家各户传出来。那是正在做糖,一种我们当地流传了很多年的农家小零食——炒米糖。而现在,也只剩下老一辈的还舍不得丢掉这一口。
“做糖”是我们那里的方言,指的是将炒米,其他辅料和麦芽糖在一起混炒后,放在特定的木格里压实,最后切成一个个小方块。整个过程长,也颇费些功夫。
如今,网购让我闲坐家中,也能吃到全国各地的特色炒米糖。只是,我最想的还是那一口过去时光的老味道——炒米糖给了寡淡冬季里长久的甜蜜和温暖。
村里人做糖用的是辈辈传下来的老手艺,现在流行叫古法工艺。从头到尾都靠手工,时间长还费心思。也许这是那些老味道让人此生怀念的原因吧!除了食材本身的纯粹,还揉进了时间岁月,人对付出与收获的尊重,对自然回馈的敬畏,对祖辈勤劳智慧的感恩传承。
秋收后,爸爸把专门留下来的糯米挑去加工厂脱壳。妈妈淘洗干净后倒进借来的木桶里蒸熟。然后,在簸箕上铺开放凉晾干。这时候,妈妈会满脸笑容地对我们讲“随便吃”——这是我记事起,听到她说的最大方的一句话。背后每一分钱都要计算的拮据,也只有在这一刻,卸了负担。
她还会琢磨出一个个创意小饭团,里面裹着萝卜青菜,白糖……笑呵呵地送到我和弟弟嘴边。昏黄的钨丝灯光下,小饭桌围了一圈的欢声笑语。那是我记忆里最暖的冬夜。
接下来的两天,晚饭后,全家人围着簸箕,把晾干的糯米饭团揉碎成一粒粒,白天再抬出去晾晒——为后面做炒米准备着。
定好了做糖的日子,妈妈提前去村里借来黑沙子,把存了不少日子的熟糯米拿出来。我守在土灶口看火,她在热锅里翻炒。几下后,一粒粒雪白的炒米就蹦出来了,很快像一层厚厚的雪铺满了锅底。有时能听到“砰”的一声,那是某粒炒米忍不住跳出了锅外,捡起来吹干净,再放回去继续“受刑”。专用的歪把子锅铲,把沙子和炒米弄挑筛子里,摇晃几下,黑白分离——几轮重复之后,做糖用的炒米就好了。
麦芽糖的制作很吃经验,是个技术活。这方面我俩姨夫是砖家。每年的这时候他俩最忙,东家西家的都要仔细看看,发现哪里不对要及时纠正,这都是辛苦换来的粮食啊。晚上还要去约好的人家里做糖。那时候讲究个乡里乡情,俩姨父从来不收工钱,递上两三支烟就心满意足了,多少年了一直这样。村里人都尊敬的称呼大师傅二师傅。
我们那里是水稻产区,以前家里人多,均亩数少加上产量也有限,留给种麦子的地都很小。一季下来,能打下两三个化肥袋子的量算是很可以了。除了换点做面条饺子的面粉,剩下的都给了做糖用。
家家都很小心翼翼的伺候这些麦子,从催芽到和糯米饭一起发酵,到最后熬煮成麦芽糖,每一步都要请俩姨父过目指导。哪里要是弄错了,可惜的还不止这些辛苦收获的麦子。等到麦芽糖差不多能挂住锅铲,晚上就可以开工做糖了。除夕夜外,这是我最期待的夜晚。
做糖的当天,爸爸卸下厨房的那个老木门板,从河里担水回来反复擦洗后作案板用。堂屋里收拾干净,支两条凳子作案板的腿,早早磨好的几把菜刀轻轻放好,做糖专用的木滚子斜在木格子里……做好了这一切,爸爸会很严肃地叮嘱我们兄弟俩不要乱动,尤其是菜刀。
晚饭后,俩姨父掐着烟头准时来家。大姨父灶头掌勺,二姨夫案板持刀。多年下来,俩人配合默契,分工明确。实在忙不过来了,兵分两路,各管一家。大姨夫老练的从外锅舀一勺适量麦芽糖稀,手握勺柄在里锅不停搅动,嘴里时不时地叫到“加火,加火”,差不多火候了就倒进炒米,再次不停的用锅铲子翻炒。
我们那里做糖多数是炒米和花生两个口味,芝麻和“杆子”是稀少奢侈品。
炒米是只有单一的炒米这一种料,土话也称“白糖”。花生是看家里收成多少,掂量着往炒米里添加。粒儿多的叫“真花生”,少的叫“假花生”,味道比起来也是天差地别。我和弟弟最喜欢在茶叶罐里翻找花生粒多的糖块,嫌弃味道寡淡的“白糖”。
芝麻糖是少部分人家才有,我自个儿家一直没做过。
“杆子”是用面粉为原料炸出的小长条,最后方体成型。又大又厚还不好下嘴,拿一个啃半天,牙口不好的人吃不来这个,但味道极好。
大姨夫手脚不停,脑子还得转的飞快,要时刻倾听主家的想法:是炒米多点,还是花生粒儿多点,还是根据现料边做边掂量着搭。每家情况不太一样,都紧着手头的东西尽量多搞出些花样。
翻炒好了装进搪瓷脸盆,满满当当。爸爸端着飞快送到堂屋,二姨夫接过去倒扣进木格子里,然后用木滚子来回反复地用力压实压平。拿走木格子,一大块平平整整,线条笔直的炒米糖在案板上分外好看。
二姨夫拿起菜刀,逗我几句:“你喜欢长方形还是正方形,你怎么讲我怎么切,嘿嘿……”
“我喜欢正方形,拿在手上正好。”
“好,那我就切正方形,开刀咯!”二姨夫像电视里那样喊上一嗓子。他拿起菜刀比划了几下,把整块糖切成几个长条子后,再切成一个个小正方形,炒米糖做好了。
那时候,我最喜欢站旁边看他和爸爸切糖。手起刀落,动作利索漂亮,咚咚咚的案板声很有节奏感。他们切出来的糖块大小薄厚看过的人都夸好。
第一批炒米糖做出来后,爸爸点燃堂屋案头的两个红蜡烛,捧一把放案头上,恭恭敬敬地跪下磕头,嘴巴里念叨几句,大概意思是让祖先们尝尝今年新做的糖,保佑来年风调雨顺家人平安。仪式简单,但足以让略懂事的我感受到了庄重和虔诚。过后,他再抓一把送到厨房给大姨夫,最后才笑呵呵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可以随便吃了。”
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一种规矩吧!
我和弟弟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抓起来往嘴里塞,刚做出来的炒米糖还有温热,吃起来软软的,一口下去还能拉扯出丝状的麦芽糖。等过了会儿,温热消退,炒米糖就会变硬,再咬一口有清脆的嘎嘣声,特别好听。
炒米糖全做好后,爸妈用带有塑料内胆的化肥袋子分开来装。红字的装有花生的,黑字的是“白糖”的,最小的那个是“杆子”。然后用绳子把袋口扎得紧紧的。以后我们想吃糖了,爸妈就把袋口解开,从里面各抓几把放进四方的铁罐子里。我和弟弟嘴馋的时候,抱着铁罐对坐在大门口,一遍遍地翻找花生粒多的那块。糖块碰撞铁皮的声音吵得爸妈经常生气:“翻什么翻,里头有金子啊,再这样翻,以后不要再吃了……”
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姨家的炒米糖,整块的都是花生粒,极少的炒米,嚼起来特别香甜。我每次去,她都捧出一大把让我吃个够。那段岁月,整个冬天里,随处可见大人小孩手里都攥着几块糖,嘴巴里嘟囔着咀嚼的声音,仿佛村子里的空气都是香甜的。
现在,老味道不在,香甜的就剩下过去的经历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