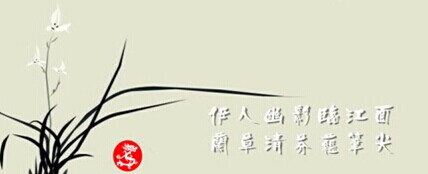【江山·见证】【宁静】小住沙溪(散文)
【江山·见证】【宁静】小住沙溪(散文)
![]() 一
一
行旅的脚步总是匆匆,即使一再提醒自己慢下来,还是朝来暮往地奔赴下一段路途上的风景。终于,在沙溪古镇我停下匆匆的脚步,小住六日,爱其静幽、风雅的气质,还有令人流连的烟火气。
“小住”一词,出自《后汉书》。据说,东汉时有一个名叫蓟子训的方士,在某地秀了一把神异之术。当他驾驴车准备离去时,围观群众高喊:蓟先生小住。“小住”可以直译为“稍作停留”,也有挽留之意,后来引申为暂时居住一段时间。宋代陆游诗云“小住初为旬月期,二年留滞未应非”,清朝秋瑾的词《满江红•小住京华》,都是这个意思。
大理三月的风,吹得云朵像一溜小跑似的,我便追着白云来到沙溪镇。中午时分,寺登街口的青石板路上人来人往,街道两旁小吃店、客栈、食杂铺里的老板迎来送往,或是低头盯着手机莫名地笑,没有人喊我:小猪她爸先生小住。我拎着行李箱走进一家民宿大院,很喜欢这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颇有“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意境。老板娘笑盈盈地问我,住几日?我回道,两日。又赶忙补充道,也许会多住几天。那时,我还惦记着去临沧一游。
这间民宿的位置颇佳,出院门右转就是寺登街口,左转则是一个集市,各种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我不急着去古镇里,而是左转来到集市里,点了一碗牛肉米线。米线是荞麦制作,嚼劲十足,汤底由牛骨熬制,搭配新鲜牛肉,少许辣子、香菜,味道鲜美。我品咂着米线的味道,咀嚼沙溪古镇古往今来的岁月。
沙溪镇隶属于云南大理剑川县,南眺是大理古城,北望是丽江古城,文化历史悠久。二千多年前,沙溪先人就创造了古老灿烂的文化,开启了云南青铜文化的先河。到了秦汉时期,沙溪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三条干线交界点上的重要贸易集散地。与唐宋相伴的五百多年间,沙溪因平坦的地势、丰饶的物产,成为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重镇,南来北往的马帮、客商云集于此,汉、藏、白、彝、纳西、摩梭等各民族间的物质、文化、宗教、艺术得到广泛交流,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记。2001年10月,沙溪寺登街这座“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被世界纪念性建筑保护基金会纳入“值得关注的101个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在这一目录中,中国的建筑占了两个,另一个是绵延万里的古长城。
随着茶马古道历史使命的终结,沙溪渐渐失去往昔的风采,沉寂起来,像一块翡翠掩埋在岁月卷起的尘埃中。二十年前,当地政府启动了“沙溪复兴工程”,对古镇核心遗产进行抢救性修复,坚持“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理念,推动“轻开发、深体验”的文旅融合发展之路。据统计,去年沙溪古镇共接待游客三百多万人次,旅游总花费四十多亿元。
沙溪犹如古树绽新花。热播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将古镇作为外景地之一,伴着爱情主线推出的一个个镜头,展示出小镇“里巷传仁德之懿,父老有述古之风”的风貌,沧桑古旧与唯美浪漫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年轻人端着香浓的咖啡低语,老年人盯着翘角飞檐出神,各有所爱,各取所需。
集市外熙熙攘攘的人群,打破了古镇的幽静。我回到民宿休息,等待大波游客退去后,再寻觅小镇的古拙,或许还有更唯美的意境。
二
下午四点多钟,阳光明媚,天阔云蓝。我踩在乌青光亮的青石板路,伴着轻风漫步在青瓦屋檐下,伫立雕花窗棂前,从那些精美的图案里寻觅悠悠古意。
古镇的老宅多是明清留下的建筑,以欧阳大院、杨家大院、赵氏家宅等院落为代表,三十多处保存相对完好的民居错落在小镇街巷上。木质门窗已辨不出本色,时光早已把它们涂抹成黄褐色与青黑色,斑驳而老旧。沧桑就是时光的具象,古宅里老奶奶守在窗口兜售传统手工制品,老屋中年轻女孩精心调制一杯香浓的咖啡……岁月向来如此,一路地由古至今,留下一路的印痕,“节同时异,物是人非”。
沙溪镇很小,一条主路连接几条小巷。我用了二十多分钟就转到了四方街,惊讶于古戏台的建筑之美。戏台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三层楼魁星阁带戏台,木结构抬梁式建筑,青瓦叠角,层层斗拱盘旋而上,十四个檐角如翼轻扬,好像燕尾飞向四面八方,庄重不失轻盈,高大又不缺乏灵动。
台基高筑,三面敞开,台口朝向四方街的小广场,形成一个天然而成的观演空间。我坐在一棵大树下的台基上,望着典雅的古戏台,仿佛能听到锣鼓声声,汉族戏曲、白族调子,马帮汉子、商旅行者的掌声、喝彩声,混杂交织在一起飘散在石径窄巷里,像一首乐章中的和弦,跳动着茶马古道上热烈而生动的文化符号。
回首就是兴教寺,大门两侧的哼哈二将并没有领情“以戏娱神”的传统,呲牙咧嘴一副威猛的样子。走进寺门,却不见香火缭绕和供奉的神像,清幽的像一个寻常人家的大院。原来沙溪人将这里改造成一座小巧的“博物馆”,两侧房间化身展室,图文并茂地叙说沙溪故事。雄浑凝重的兴教寺建于明永乐十三年,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它是滇西鲜见的明代密宗阿吒力佛教寺院,寺内保存的明代壁画融合了中原绘画风格和藏式色彩、白族绘画艺术,弥散着独特的文化韵味。
从古戏台左边的窄巷顺坡路向下走,就是古镇仅存的东寨门。青石砌筑的墙基,黄土夯实的土墙,厚重结实,半圆形拱门上方,斜屋顶铺排着青瓦,四角挑檐,给人一种落落大方的稳重感。几百年来的风雨,磨掉其锋芒,蚀其筋骨,但它依旧斑驳地向东挺立,守候着平坝上的家园。
城门外,黑惠江蜿蜒流淌。江岸绿草如茵,一红一白两匹马低头吃草,悠闲自得。江面上鸭子成群,七上八下地扎猛子,寻觅可口的小鱼小虾。岸堤之上鲜花盛开,花香与老屋里飘来的茶香、咖啡香混合成独特的香气,扑入鼻息间,令人肺腑舒畅。抬头向南望去,黑惠江的曲线上拱起一道优美的弧线,那是玉津桥苍然横卧的身姿。
玉津桥是一座单孔石拱桥,造型简洁粗犷。青石筑起桥身,红砂石板铺就桥面,没有繁复的装饰,却美观大方,圆润流畅的拱形圈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斜阳下,远处青山葱茏,近处绿树红花倒映潺潺流水中,探入江中的沙洲把黑惠江弯成一道玲珑的S弯,溪水浸泡的青石布满青苔,风雨侵蚀的桥身透着岁月流逝的质感,携来沧桑之美。
尽管桥头标志牌写着“玉津桥——茶马古道古桥”的字样,实际上桥与古道关联不大,因为早年的铁索桥损毁后,直到1921年才重建成单孔石桥,也就是说玉津桥秀立于此,静观流水,默数百年春秋。走上玉津桥,桥头有一座微小的山神庙,没有供奉神仙,轻烟缭绕。桥栏尽头雕刻的神兽已经模糊不清,风雨剥蚀了它们的眉眼,却依然保持着威严守候的姿态。桥面石块被磨得十分光滑,坑洼不平的彼此相连,似在叙说车来人往的过去。站在桥上环顾四周,桥与山水、桥与古镇和谐地构成一幅水墨画,人就像游走在画中:
石可成桥,从此不唱公无渡;津真是玉,到此方知水有源。
岸边传来一阵歌声,便循声而去。高大的榕树下,一位女孩正弹着吉他轻声歌唱。歌声柔柔地飘过黑惠江,时间好像一下停滞了,只有傍晚的山风还在轻轻地吹拂。
三
清晨,我从鸟儿的鸣叫声中醒来。三月的沙溪,早晚比较寒凉,尤其是呆在房间里寒意更重,而室外则是另一种天地,暖阳,和风,花香。
我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院子里,老板送来一杯汤色红润的普洱茶。我开始散文《品味建水》的写作,没有立即动笔写沙溪,是因为习惯于沉淀以后再落笔。写到太阳再度斜照的时候,我收起电脑,出发去黑惠江东岸的北龙村,那里有诗歌塔和先锋书局。两公里的路程,可以坐村民的“三蹦子”过去,但我觉得穿过古镇、沿江看景更有意思,便徒步在乡间小路上。
诗歌塔和先锋书局伫立在半山坡上。所谓的诗歌塔是早年村民的烤烟房,而先锋书局则是过去的谷仓,精心改造后,成为文意悠悠的好去处。我顺着螺旋式楼梯向上攀登诗歌塔,塔内垂挂着一个个透明牌子,牌子上刻满了中外经典诗句,诗意盎然。站在塔顶向西眺望,山峦围拢田园,黑惠江蜿蜒,玉津桥掩在绿树中,沙溪古镇坐落其中。
书局是先锋书店在云南的首家乡村分店,它不仅是沙溪游览的文艺地标,更是连接历史与现代文化的精神驿站。书店保留了谷仓原有的土木结构,粗大的木梁贯通在高挑的屋顶下,斑驳的夯土墙与高耸至屋顶的书架形成鲜明对比,现代化的灯光设计,巧妙地将谷仓的古朴与时尚的阅读体验融为一体。
我选了一本关于沙溪的专著,端着一杯云南小粒咖啡,坐到阶梯式的座位上,细细品读沙溪的老味道。读着读着两个身影映入眼帘,一位是杨慎,一位是徐霞客。明朝嘉靖三年,杨慎因为惹恼了明世宗被贬至云南永昌卫,也就是今天的云南保山市。在滇期间,杨慎游历了大理、剑川等地。有没有去过沙溪,史料文献没有确切的记载,杨慎这一时期形成的诗文也无直接提及沙溪的文字。但这并不妨碍沙溪人以杨慎贬谪云南作为文旅叙事,说他曾在沙溪小住,就住在兴教寺里。毕竟沙溪与丽江、大理很近,杨慎小住沙溪也是有极大可能的。旅游不是考古,更不是厘清历史的真实,在黑惠江岸吟诵“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不仅应景,也应和了杨慎的情怀,他正是在贬谪滇西时写下了令人荡气回肠的词作《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徐霞客是真的到过沙溪,他在游记中记录了沙溪的地理位置以及风土人情,但没有小住。那一天,徐霞客匆匆走在沙溪的田野里,偶遇兴教寺的主持。两人一搭话,主持便盛情挽留徐霞客到寺中小住,并邀请他考察石宝山。这不奇怪,当时的徐霞客要比现在的“网红”还火,堪称实力圈粉。然而,徐霞客婉拒主持的邀请,要赶到洱源县与朋友相会,不敢耽误行程。徐霞客与沙溪打个照面,匆匆一别,不承想错过了石宝山上的石窟。
我合上书本,离开书局,沿着黑惠江往古镇走。傍晚的阳光,柔和地透射到江面上,波光粼粼。伴着晚风习习,不由得哼唱起杨慎作词的《三国演义》主题曲: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四
又是一个清晨,我和沙溪从夜晚的静谧中醒来。原打算去石宝山,但老板娘说,今天是周五,镇上每逢周五都有集市。我便改了计划,去赶集。
镇子上的一条街,一改往日的冷清,好像全镇的人都来了,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买卖兴隆。穿着民族服装的大姐守在摆满腊肉的摊位后,大块的是猪腿,小块的是猪舌,红瘦白肥泛着诱人的光泽,看着就想咬一口,仿佛咬住阳光与烟火熏制的时光。一股焦香味飘来,不用看就知道那一定是烤牛肉粑粑。沙溪的烤牛肉味道鲜美,特别有嚼头,但他们烤的特大牛肝,我始终不敢问津。蔬菜类的案子主打一个“野”字,各种植物的花与茎都可以叫卖,野菜的种类多到令人眼花缭乱。想起去年六月底在丽江吃过的野生菌,便感慨如果能在雨季再来沙溪赶集,一定会寻到见手青菌子,生食有毒,熟吃鲜美。
一扭头,看见一个小美女,打扮得非常精致,后背上一个小背篓格外吸引眼球。她显然是一名游客,和我一样这瞧瞧、那望望,只是那个小背篓让她多一分乡土气息。当地人也背着背篓,里面装满采购来的物品,沉甸甸地展示着赶集的意义。我买了几个柑橘,一小盒草莓,还有一袋切成块的甘蔗,算是赶集的成果。至于那些美味的炸洋芋粑粑、烤饵块,像我这样很少吃零食的人,只能闻闻香味而已。赶集对现代城市来说,已经是一个很久远的词汇了,沙溪的周五让我回到从前。
避开中午的太阳暴晒的时段,下午我去了沙溪古镇东南约五公里处的白龙村,当地人心中“龙潭圣地”。群山环抱下的龙潭很是小巧,潭水清澈如镜,像一块嵌在山谷里的翡翠,湛蓝碧绿。潭上横卧一座五孔石桥,以极其简约的造型给绿潭平添一道风景,桥上无人,潭面倒映悠悠白云,幽静的质感令人不愿高语。潭边矗立着数十棵黄连木、栎树,看那树形估计是百年古树,裸露的树根盘曲着,与潭水相映成趣。白族人视龙潭为“龙神居所”,遇到干旱的时候,会在这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文旅叙事免不了要扯上马帮,传说着马帮常在此汲水休整,渲染一番茶马古道上秘境碧泉的故事。我倒是独爱这里山野清幽,乐享自然之美。
夜幕降临,灯火渐次亮起,我坐在民宿大院里。老板娘的两个小孩,还在院子里玩耍,他们似乎有无穷的精力。仰望天空,繁星满天,沙溪的一天就这样慢悠悠地过去了。
五
石宝山山门外的停车场上,几只猕猴在觅食,它们看上去体态要比峨眉山的猴子小很多,见到游人还流露出几分胆怯。看来到石宝山游览的人不多,还没有把猴子宠成“打劫猴”。
近些年来,沙溪古镇越来越火,但游人很少踏足十五公里外的石宝山。石宝山石窟距今已有千历史,因其地处滇西,鲜为人知,被称之为“被遗忘的国宝”。石宝山现存十七窟、一百三十九尊造像,分布在石钟寺、沙登箐、狮子关三个地点。目前供游人参观的只有石钟寺,也是石窟最为精华的部分,可以一睹南诏、大理国的佛教石窟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