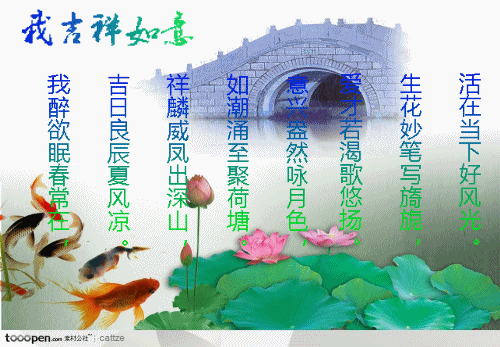【好韵】归去来兮(小说)
一个秋天的早晨,梧桐叶子都黄透了,Z老师踩着湿漉漉的石板路往N小学赶,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刚到校门口,就看见老张头正忙着给新换的校牌刷红漆。“县第五小学”几个大字在晨光里闪闪发亮,照得他鞋帮上的泥点子格外显眼。
“哎哟喂,这不是Z主任嘛!”老张头一抬头看见来人,赶紧直起腰杆,顺手把刷子往油漆桶边沿上敲了敲,“A校长刚才还在这儿转悠呢,说是在小会议室等你,好像是要给你钥匙啥的。”
Z老师闷闷地应了一声,那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的。三个月前那个热得人发昏的下午仿佛就在昨天,村小操场上黄土飞扬、A校长拍着他肩膀说的那句“组织上就指望你了”,到现在想起来耳朵还嗡嗡作响。记得当时他衬衫领子上还粘着几个捣蛋鬼蹭上的蒲公英毛絮呢。现在倒好,西装内袋里那张聘书早就被他捏得皱皱巴巴的,边角都被手汗浸得发软了。
会议室那张长桌擦得锃亮,A校长随手把铜钥匙往上一扔,叮当一声脆响。“老Z啊,这可是咱们学校的宝贝疙瘩。”他手指头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面,“瞅瞅这房梁上的雕花,都是清朝那会儿传下来的老物件。现在教育局那边催得紧,说是要评优的话,整栋楼的水电都得重新折腾一遍。”
Z老师盯着钥匙串上那把最大的铜钥匙发愣,月牙形的凹痕格外显眼。听老同事说,这凹痕是前任总务主任用了十来年才磨出来的。看着这把钥匙,他突然想起在村小教书的日子。那时候的钥匙可真是寒酸,就两块生锈的铜片,开个破铁皮门都得费半天劲。那扇门也够呛,风一吹就吱呀吱呀响个不停,怎么都关不严实。
他手抖得跟筛糠似的,那把钥匙都快被他捏弯了,嘴里还不停地抱怨着“这破钥匙……真是见了鬼”。我注意到他手指关节都发白了,整个人紧绷得不行,一看就知道紧张坏了。
Z老师这人挺有意思的、总喜欢挑总务处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往窗外瞄几眼。操场边那棵老槐树的影子在他教案本上晃悠、比村小那棵歪脖子柳树的影子跑得快多了。他手里翻着采购单,心里却想着:现在填表都得正儿八经写“固定资产”,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说“破桌子旧板凳”了。最烦的是每天下班前还得一层层拍照检查电闸。想想在村小多自在啊,电路总闸随便找根木棍一撑就完事,哪像现在这么麻烦。
那年冬天冷得邪乎,雪说下就下。Z老师猫在仓库里翻腾了大半天,好不容易从犄角旮旯拽出三床发黄的旧棉被。那股樟脑丸味儿冲得他直揉眼睛,不知咋的,眼前突然冒出村小那些娃娃们冻得通红的小手往他棉袄兜里蹭的画面。正愣神呢,A校长领着个裹得跟粽子似的小年轻推门进来:“这是新来的F副校长,局里刚派来的,以后,后勤这块儿归他管了。”
F副校长伸手过来时、我意外发现他手心特别暖和、指甲也修得干干净净。他眯眼一笑,眼角堆起几道褶子:“老Z啊,最近忙坏了吧?我刚看完仓库那边的单子,这批课桌椅的招标材料还得再改改。”
Z老师随手把被子往旁边推了推,给F副校长腾出地方放文件。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F副校长的头发上,泛着淡淡的光。他低头瞥见自己袖口已经磨得起了毛边,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那天Z老师正猫在三楼修那个滴滴答答漏水的龙头,手上还沾着肥皂泡呢,就被A校长火急火燎地喊去办公室。这才刚开春,教育局的调令说来就来,连个缓冲的时间都没给。“局里基建档案这块缺人手,指名道姓要你去。”校长把调令往桌上一撂,钢笔在纸上轻轻敲着,“F校长才上任没几天,这事儿他那边也点头了。”
Z老师捏着那张调令、手指微微发颤。纸上“借调期一年”几个红字特别刺眼,让他一下子想起昨晚熬夜赶的食堂招标方案——桌上那堆文件还乱糟糟地摊着呢,压根没来得及收拾。
“天哪,我得赶紧溜了,总务那边还有一堆烦人的破事等着我去收拾……”
“哎,局里那些破事儿还没搞定呢。”A校长不耐烦地摆摆手,外套从椅背滑下来都没顾上捡,“学校那边有老王它们盯着,能出什么幺蛾子?”
教育局办公室那台老掉牙的空调一到下午准点歇菜,Z老师冻得直搓手跺脚。这人平时开会总爱整些统筹规划之类的官腔,可怪有意思的是,每次经过校门口那家文具店,他总控制不住要买几支带橡皮头的铅笔。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乡下娃娃们就稀罕这个”。
那天周五下午,Z老师正收拾办公桌准备结束借调期,F校长突然推门走了进来。他看起来憔悴了不少,整个人瘦得厉害,头发也白了许多,手里提着个塞得满满当当的旧布袋子。“老Z啊,该回来了。”他把袋子往我桌上重重一放,里面搪瓷缸子哐当直响,“现在学校忙得团团转,党建、学籍管理这些事都堆着没人管,还有那个‘双喊’政策也得落实到位。对了,宣传工作这块还得你来负责。”
Z老师靠在窗边发呆,眼睛盯着教育局院子里那几株开得正旺的玉兰花。这花开得可真够热闹的,他心里想着,比思旸一小那棵足足早了十来天就凋谢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脑勺:哎哟,新长出来的头发茬子摸着比以前密实多了。
“校长,实在不好意思这时候找您,有件事想跟您聊聊……”
老F校长往椅子上一坐,随手把那个磨得发白的布袋子撂在桌上,搪瓷缸的校徽边角都露出来了。“局里那边我都帮你打过招呼了。”他拧开保温杯喝了口茶,说话慢条斯理的,“下周一拿体检报告的时候,记得让医生给你量个血压。上次瞧你老揉太阳穴,这事儿可不能大意。”
那天回学校、发现Z老师居然穿了件崭新的衬衫、连褶子都熨得一丝不苟。走到总务处门口才发觉情况不对、门锁全换成新的了。新来的小杨干事慌慌张张地摸出钥匙,脸憋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那个……Z主任、F校长让您以后在二楼办公。”
二楼的办公室朝南,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把文件柜的影子拖得老长。桌上堆满了各种材料,乱糟糟的都快成小山了,最上面那本党建学习计划旁边还压着张纸条,一看就是F校长写的:“记得每天下班前把工作汇总一下。”
那天晚上Z老师难得加班到这么晚,走廊尽头的灯坏了很久也没人管。他摸黑想找工具箱,结果“砰”的一声,膝盖狠狠撞上了楼梯拐角的暖气片,疼得他直抽冷气,原地蹦跶了好几下。正揉着腿呢,手机突然在兜里震个不停,掏出来一看是老婆发来的消息:“闺女这几天总说想听爸爸讲故事了。”
他蹲在那儿发了好一会儿呆,手指蹭到暖气片上的灰时,不知怎么的,脑子里突然闪过小时候村里学校那盏墨水瓶改的煤油灯。
那天开教师例会,Z老师正低头记笔记,突然钢笔漏墨了,墨水在纸上洇开一大片。他揉了揉发酸的太阳穴,抬头看见前排同事的后脑勺,心里猛地一沉——自己这发际线什么时候比F校长还高了?散会时小杨鬼鬼祟祟地塞给他一面小镜子,“Z主任,您这头发……”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对着镜子拨弄额前那几撮总是不听话的头发,镜子里那张脸憔悴得吓人,眼窝深得能放硬币,鬓角的白发像撒了层盐巴。“唉,工作忙起来谁还顾得上头发啊。”他随手把镜子丢回抽屉,指尖碰到冰凉的镜面时突然一愣——教育局那些铁皮柜子摸起来也是这种扎手的冷。
窗外的雨下个不停,已经整整一周没见着太阳了。Z老师正埋头整理文件,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他瞥见是F校长的来电,连忙按下接听键。可办公室里雨声哗啦啦响成一片,电话那头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走廊尽头,总算断断续续听明白了:“我明天就要回老家了,工作交接得赶紧办。”
“校长……”走廊窗户渗进来的雨水已经把他的裤腿浸透了,可他还是像根木头似的杵在那儿。
“学校那边以后就交给L校长负责了。”电话那头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对了,他跟你还是同一届的呢,这人性格挺随和的。”
电话刚挂断,Z老师就站在窗前发起了呆。雨下得特别大,路灯的光被雨水打得七零八落。他不知怎么突然想起F校长第一次来仓库时的场景——那件羽绒服口袋里露出半截药盒,跟他现在每天吃的降压药一模一样。这个发现让他心里咯噔一下,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那天校园里的桂花香得特别浓,刚好碰上L校长来学校。他穿着件很普通的夹克,拎着个帆布包就来了,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一进门就特熟络地拍着Z老师肩膀说:“老Z啊,你还记得师范门口那会儿吗?每次吃饭你都要抢我碗里的红烧肉。”这话一说出来,感觉特别亲切,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学生时代了。
Z老师突然怔住了,接着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说真的,回学校这么些天,办公室里那股子压抑劲儿好像头一次没那么让人难受了。
“我跟创建办那边都打过招呼了。“L校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帆布包的拉链咣当撞在桌腿上,“下周你就回来上班吧。党建和宣传这块还是你来负责,至于学籍管理和双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就让年轻人多锻炼锻炼。”
他随手从背包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牛皮本子、哗啦翻到中间那页。我凑过去一看,好家伙,上面歪歪扭扭画着学校的简易地图:“你看这儿,”他用手指戳了戳图纸上的位置,“要是改造老教学楼的话、那些雕花木饰可得留着……”
Z老师不经意间瞥见L校长写字时笔尖划过纸面的痕迹,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位校长的鬓角白发居然比自己还多。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从窗外洒进来,桂花树的影子随风轻轻晃动,斑驳的光点落在他们交握的手上,仿佛镀了一层细细的金箔。
2025年初春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校园里,暖得让人犯困。Z老师弯着腰在那儿捣鼓新栽的玉兰树,水壶里的水哗啦啦浇下去,溅起的水珠在叶片上打滚儿。他正想过去搭把手,突然瞥见公示栏那儿多了张红头文件,教育局的通知单贴得歪歪扭扭的。这时候L校长晃悠过来了,随手扔给Z老师一瓶冰镇矿泉水“听说要搞什么集团校了,咱俩这清闲日子算是到头咯。”他这话说得轻巧,可那眉头皱得都能夹死蚊子了。
水珠沿着瓶身慢慢往下淌、把Z老师的手指都打湿了。他靠在操场边的栏杆上出神,望着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从前。那时候天还没亮透就得往村小赶路,裤脚总是沾满蒲公英的白毛毛。现在看着地上飘落的玉兰花瓣,恍惚间觉得跟记忆里那些毛茸茸的小东西特别像。
“校长,”他仰头猛灌了几口矿泉水,冰水滑过喉咙的瞬间,整个人立马清醒了不少,“宣传稿的事我再琢磨琢磨,肯定能改得更好。”他转身时习惯性地摸了摸后颈项冒出来的短发茬,对面写字楼的玻璃窗反射着刺眼的阳光,让人不得不眯起眼睛。这些年校门口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连校门口的牌子都更新了好几回。时间就像粉笔灰一样,不知不觉间染白了他的鬓角,磨粗了他的手指关节,最后全都静静地留在了那些泛黄的教案纸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