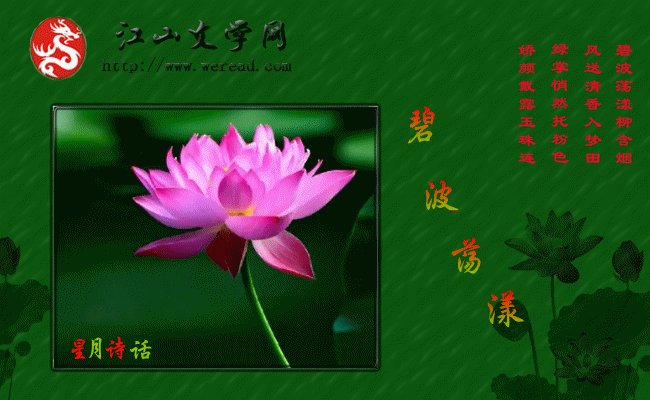【星月忆】殇随风逝,爱在流年(散文)
【星月忆】殇随风逝,爱在流年(散文)
![]()
岁月装帧着风景,微笑与泪水交叠。瞳孔收缩着生命沿途的殇,放大的却是爱无限。有种永恒根深蒂固,那是走过岁月河畔之后的重组,它叫珍惜。
一、黑发,白发
街灯已经亮起,暮色中行人匆匆,总有一盏灯为你点亮,家的呼唤,涤荡在每一个人的心扉。
我躺在沙发上翻看着宋词,电视节目播放着,母亲不知忙着什么,从厨房到客厅,从客厅到厨房,不太利落的双腿画出温馨的轨迹。她的腿上似乎永远绑上了一条爱的“带子”,仅仅够延展到这个室内,那是爱的长度和宽度,还有热度和温度。永远那么清晰,像头上的白发在灯下耀眼。
不知何时,母亲坐在我的身边,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说:“雨儿的头发多好啊,又长又黑又亮......”我顺势将头枕在了母亲的腿上,就在抬头的一刹那,我再度真切地看见母亲那满头的白发,被客厅的光映照得白的唯美,但是也白的沧桑。我的鼻翼突然很酸,将头往母亲怀里扎了扎。母亲依然抚摸着我的头发边看电视边说:“雨儿的头发多好啊......”此时,手中的宋词也婉约不了我的心情,哀伤还是愁,我不知道。没了平仄没了格律,乱了上下阙。
母亲年轻时,是有名的“长发美女”,那瀑布般的头发,黑黑的,亮亮的,顺顺的,令人艳羡极了。我时常盯着母亲的黑发,偶尔的用手摸一摸,用鼻子轻嗅着发丝间的味道,看它像云一样飘来飘去。
做饭时,母亲将长发编成了两条大辫子,煮饭切菜,满是油烟味的厨房也因此多了一份别样的美丽;灯光下,母亲为我缝补衣服,躺在被窝里的我,看着母亲满头的黑发斜披在肩上,黑夜也多了一份柔情;上学时,母亲站在家门口,我几步一回头,看着母亲的黑发在风中跳舞,这一路,我微笑地前行;生病时,母亲抱我在怀里,再痛的我,被母亲的黑发抚慰着脸庞,温柔降温了高烧。
于是,从小在我心中,我就梦想着能有母亲这样一头长长的黑发,在生命的每一天,迎风飞舞,生命那些花事,也终成芬芳。
一年年,母亲为我留起了长发,但是,怎么也没有母亲的长。母亲说:“雨儿的头发多好啊,又长了很多了,快了,快了……”每每听到这样的话语,我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想象着我一头长发披肩,在田野上随风旋舞,在人生路激情四散。
直到15岁,我依然不会洗头发,母亲很娇惯总生病的我。她不允许我做这做那,甚至面对这满头长发,她也替我打理。伏在母亲手上,母亲用心揉搓着头发,生怕弄掉了一根......然后,为我梳顺了,擦干。我说:“妈,快赶上你头发长了吧?”母亲微笑着说:“快了快了,不过啊,你头发长了,妈也就老了。看看,也有白头发了哦......”那一瞬间,我突然想,不要再长什么长头发了,宁愿换取母亲年轻黑发的多姿。
清浅时光,如水岁月。我的黑发一天天变长,风中飞舞,雨中湿滑,如一瀑布,延续着生命的美丽。而母亲的白发也渐渐交织在黑发间,很少,但是已成为了鬓角的点缀。
我上高中了,一个星期没有洗头发,周末回来,终于在母亲的指导下,自己亲手洗了头发。我上了大学,母亲一次次打电话:“雨儿,头发又长了吧?洗头时不要太用力哦,头发不要在阳光下暴晒啊......”
每次回家,母亲总是抚摸着我的长发,笑着说:“又长了,又长了,多好啊......”吃饭时,看着饭桌对面的母亲,头发剪短了很多,白发已多了很多,曾经的黑瀑布消失了;饭后,看着在厨房忙着收拾的母亲,已不再像云一样飘来飘去,笨了不利落了;返校时,我几步一回头,看着母亲站在巷口,风吹乱她的头发,不再像跳舞,而是沧桑的无言与不舍的牵挂。
黑发与白发,就这样交替在红尘的时光中,经年的相册上,摄下了我的成长和母亲爱的付出。万千发丝,万千爱,万千的一世母女情怀。
也许,命运总在捉弄人,以无法承受的悲痛压在我与母亲的肩上。那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母亲的黑发一夜间变白,白的如冰冷的无血色的哥哥的脸……黑发穿越岁月的时空,被流年的沧桑晕染上如雪的白,发如雪,行走在红尘的阡陌上。
再也看不到母亲黑黑的长发了,再也看不到母亲明亮的眼神、听不到温柔的话语了。而我,也淹没在自责的心湖中,任黑发肆无忌惮地飘散在风中。我知道,黑发的故事只能由我演绎了,而母亲的白发将承载着伤痛在灵魂的舞台上凄美着离别。可是母亲,你知道吗?我的黑发一样自责着万千痛楚,我的黑发也书写着浸骨的殇。那是因为我存活下来却是用另一个人的生命交换的,我心有多自责,母亲我无法与你诉说啊,就像隐藏在我黑发里的隐约的一些白发,只不过不容易察觉或者故意掩藏罢了。对,黑色掩盖了,囚住了,所以,你没有察觉。
“哎呦,好疼!”随着墙上的钟声一响,我的头发被拽疼了一下。母亲忙说:“唉,看看我的手,这茧子粗糙了,把雨儿的头发弄疼了……”
我起身和母亲挤在一起,在她的背后,轻轻为她梳理着满头的白发,白了,白了,如雪,离殇……
“妈,你看看,你这白头发里还掩盖着好多根黑头发呢,在捉迷藏呢,嘻嘻……”
一滴泪,伴着我的话语和微笑,落在了母亲的白发间,母亲回手轻轻攥了一下我的长长黑发。如果我的泪,是染发剂的一滴,那我宁愿每天滴一滴。
是的,还有黑发,还有黑发,还有我的爱,还有黑发白发的故事伴着爱继续在生命的旅途传唱。
二、母亲的魂,陪儿子入眠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读着美丽的诗篇,激荡恒久的情怀。然而,就在诗人海子25岁生日的那天,他却横卧铁轨,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他的母亲早在生日的那天早晨,在乡下的炊烟中就煮好了一锅红米粥,以这样传统的方式在为儿子默默庆生……
抛开悲与痛,抛开生活的残酷压力和无奈,转换视角,我看到了海子的自私。铁轨可以碾压一个年轻的身体,可是一个母亲的心,怎经得起如此碾压?再没有什么比在生日之日结束生命更能让一个母亲心碎了……海子,将一首最疼的诗篇印刻在了母亲心房的血笺上。读者,永远是痛至骨髓的母亲。
每每读到关于海子的文字,心揪起来的疼。我就会想起我的母亲,还有我死去的哥哥。如果说在春季怀念一个年轻的生命,是对母亲挖心般的残酷,可是我的母亲却在一年四季,平静的、无声的,但是却潜在地怀念着她唯一的儿子。没有眼泪,也不那么伤痛,就像和一个影子说话、和一个灵魂相处。然后,释怀般地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我曾经担心,这样一种情郁之中,是否会无情地剥夺她的寿命?可是我发现,怀念,成了母亲生活的希望和动力。风烛残年,母亲知道,如果自己离开尘世,那么连怀念的机会都没有了。对儿子的一种怀念,成为生命每一天的风景。心底有多少的爱意呢喃,是我所不曾听到的,给了岁月,给了母亲心底唯一的听众。
母亲就坐在老房子的床沿上,目光透过窗子,投向东北角。就在不远的那片墓地,儿子长眠于地下。从此,母亲的人生方向里,只剩下了东北角。是否刮风,是否下雨,是否温暖,是否寒凉……母亲的双眸里,浑浊中掺杂着沉甸甸的念想。
房前的小园里,母亲最喜欢种辣椒。当一棵棵辣椒小苗在风里摇曳的时候,母亲就会蹲在垄沟里,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这些小苗。然后,自言自语着:“朝儿,今年的辣椒长得真好,辣椒酱的味道会更好啊……”然后,母亲就会长长舒一口气,似乎有了更多的力气,在小园里穿梭忙碌个不停。哥哥喜欢吃辣椒酱,母亲永远铭记。那一年车祸发生的当天,母亲正在菜板上,用菜刀将一个个精心挑拣的红辣椒细细切碎,准备做一大罐的辣椒酱让哥哥带回城里。辣椒的刺激味道,将母亲弄得满脸的眼泪,可是,她却在微笑着,说着自己的辣椒酱如何的美味。可是她唯一的儿子却再也没有品尝到母亲的爱心,她使劲地剁着剁着,红红的辣椒像儿子身上的血。这一罐辣椒酱足足被母亲死死地抱在怀里无数个日子,滴入了太多眼泪,可那辣味儿,丝毫没有减少一点儿。此后的日子,母亲的饭桌上,永远有一小碗的辣椒酱,每吃一口,母亲会嘴角笑一笑。我知道,母亲品尝的是一种岁月给她的经历,无论是沧桑还是甜蜜,母亲都会咀嚼出只有她自己才懂的味道。然后,在心里沉淀,告慰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梦。
诗人海子的母亲怀里永远揣着去北京时儿子给她的三百元钱,那是这个贫困诗人找人借来的。海子的母亲说去世的时候这钱足够上路了……这是母亲世界里伤痛升华的极致。我的母亲,总喜欢穿一条黑色的绒裤,那是唯一的儿子曾经买给她的生日礼物。夏天,她会拿出来在太阳下晒一晒,然后细心地折叠好,放在柜子的底部;秋天,她会早早地拿出来,穿在身上。洗衣服的时候,我要帮她洗洗,她却总是不让。我就会看见她自己一点点的将绒裤泡在水盆里,细心地揉搓,从不让我将其甩干。有一天,我看见母亲在灯下带着老花镜缝补绒裤,膝盖处有了一个小洞。我轻声说:“妈,我给你再……”我猛然收起我要说的话,因为我知道,我就是再买无数条绒裤,也没有这条温暖备至。我也不能将其换掉,那等于是在拿走母亲年复一年积累的源自唯一念想的寄托。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我曾想这样会让母亲走不出儿子死亡的阴影,可是我错了。漫漫岁月里,我的母亲将这种凭吊化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每一次看见母亲坐在床上,她的手不停地在绒裤上抚来抚去,就像小时候抚摸怀里的儿子。有时候,老茧会不小心的将绒裤上的线挂起一点儿,她就会像孩子一般吃惊地伸一下舌头,然后,赶紧将其抚平……隔着门缝,当我看见这一幕,我知道,其实对于母亲来说,她的儿子并没有离开,这温暖,永远伴随着她。
那一天我胃疼,母亲慌忙说:“快去买那个白色小粒的药,吃了就好了,你哥哥曾经给我买过的……”我说:“妈,那个药早就没有了,都多少年了……”话刚一出口,我很后悔,我知道我是在将母亲无数美好的梦,直接地拿走了一个。“哦,没有了啊,不生产了……”母亲喃喃地说,脸上掠过一丝失落。我赶紧说:“这新生产的更好使,就是在原来基础上研发的。”母亲笑了,说:“我就说嘛,你哥哥买的药怎会错呢,就是好……”是啊,就是好,就是好。对母亲来说,凡是与哥哥有关的能在记忆里存在的,那都是美好的。腌鸭蛋,母亲会说哥哥喜欢吃不太咸的,就会早早提前拿出几个,煮了,自己慢慢地吃着;看报纸的时候,遇上不认识的字,她会查字典,同时会说哥哥上学时最不爱查字典;下雨天,她总会嘱咐我带伞,然后外加一句“你哥就是总忘记带伞……”母亲的语言,母亲的行动,母亲的希冀还有母亲的梦,一切,都在她的儿子离开的那天,从此专属于一个人了。母亲的魂,早就伴随儿子入眠了,生命的每一天,其实我看见的只是一个躯壳,为了怀念和再度重复曾经的梦,这躯壳存在着。
当一个生命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生命就已经和母亲的心连在了一起;当这个辛苦孕育的生命残酷地离去,母亲的心就碎得无法拼接。看不见血痕,因为痛到极致似乎已变换为苍白。我在想,爱母亲,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母亲不需要儿女有多大的财富,多高的成就,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平安活着的孩子。哥哥的离去,我亲眼见证了什么叫“一夜间白了头”。这不是夸张,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每一次,当母亲的白发在风中飘动,我就会痛得难以呼吸。时光无法倒流,岁月的长河有一朵浪花就那样搁浅在河床上,那是永远的离殇。
那一天,母亲说看见我有了一根白头发;那一天,母亲说我不要再熬夜了,有眼袋了;那一天,母亲说少穿高跟鞋吧,膝盖本身就不好……原来,母亲才是天底下最心细的人,她可以捕捉到孩子每分每秒的变化。可是孩子呢,你又关注过母亲几许的无奈伤痛?即使不关注,能否,善待自己的生命,好好活着,这,就是对母亲最好的回报。
我常常将母亲的故事讲给我的儿子,他总会专注地看着我的眼睛。某一天他突然说要看看我肚子上剖腹产的刀口,我让他看了。我的儿子轻声问我:“妈妈,还疼吗?”我笑了笑,说:“不疼了,只是当时很疼。”儿子突然抱住我,把脸贴在我的脸上。“妈妈,我会好好孝顺你的,你永远不会疼……”不知怎的,我眼里热热的,两行热泪不听话地流下来,但是心,却开出了幸福的花朵。“儿子,有一个好身体,好好地活着,就是对妈妈最大的孝顺和报答。”我平静但却有力地说,我相信我的儿子听懂了这世界上所有母亲的心声。
母亲的魂,是陪儿子入眠的。那么,为母亲写一首诗吧,不要有殇的格律,不要有痛的韵脚,不要选择别离作为诗的主题。写一首幸福的诗吧,像春天的花开在母亲最柔软的心房。春暖花开,才是生活最美的诗歌啊!
我想,我会的;我想,我的儿子,也会的。
后记:黑发白发,上演的故事夹杂着痛也串联着喜。单纯局限于殇是生命的消耗,懂得将心魂托付给过往美好从而继续顽强地活着,这也是一种依托。生命存在的意义恰恰是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点,旁观者也许不懂,当局者又是多么痛的领悟!惟愿母亲,华发之年,能安享。因黑发的我分饰着哥哥的角色,将爱写满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