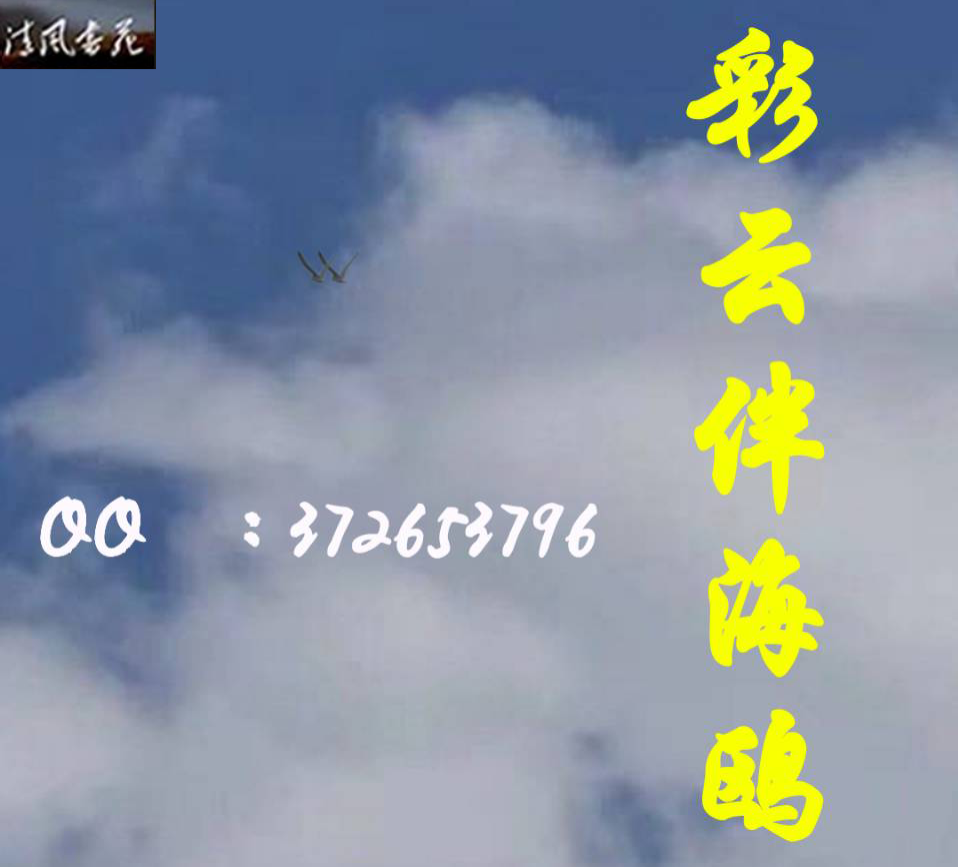【檀香.某人杯】梦锁梨园(散文 征文)
【檀香.某人杯】梦锁梨园(散文 征文)
![]() 认识李君,是在一个友人邀约的品茗聚会。记得那天是个初秋寒露的傍晚,阴沉沉的天际,豆大的雨滴,彷佛龙王拿着大抓笔,向北京西直门胡同内,一间旧式大杂院所改造成的会所,泼墨般肆无忌惮的挥洒着笔劲。淅淅沥沥洒豆入盘般的落雨声,不时在屋瓦窗台滋意妄为的舞动跳跃,彷佛为会所内围炉煮茶的文人雅士,敲打出一室清谈间的韵律。古人聊到酣时往往弹剑做歌,今人论到深处则听雨伴奏,一屋的欢然,满室的温厚,颇有“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意境。
认识李君,是在一个友人邀约的品茗聚会。记得那天是个初秋寒露的傍晚,阴沉沉的天际,豆大的雨滴,彷佛龙王拿着大抓笔,向北京西直门胡同内,一间旧式大杂院所改造成的会所,泼墨般肆无忌惮的挥洒着笔劲。淅淅沥沥洒豆入盘般的落雨声,不时在屋瓦窗台滋意妄为的舞动跳跃,彷佛为会所内围炉煮茶的文人雅士,敲打出一室清谈间的韵律。古人聊到酣时往往弹剑做歌,今人论到深处则听雨伴奏,一屋的欢然,满室的温厚,颇有“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意境。
屋外渐浓的暮色,勾引出屋内悄悄燃起的紫禁宫灯,将屋子衬托的古意优雅,摇曳朦胧。中式建筑确实就是要刚好的搭配,才能在一屋的古典中增添颜色,而动人的故事也要有听故事的人,才能让一夜的忙里偷闲饶上趣味。几个人围着一张老檀木长桌,就在翻滚的茶水蒸气中,听着李君诉说着一段动人过往。
李君是前清皇家的后裔,剑眉虎目,声音雄浑,略显沧桑的面容,象征着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正巧有一桌历经千山万水的文人雅客,正兴意盎然的等着交换人生的悲欢喜乐。于是话匣子就在主旋律登场后,原本七嘴八舌的清谈,渐渐在李君沉沉的嗓音中,自动降低了调门,让一室的好奇,在云雾蒸然的屋内,让李君悠缓的独白,将大家带往遥远迷离曾经的“民国”。
李君的家族是京剧世家,历经三代都是梨园子弟。看他的模样,本以为他的家族,应是当年在马上纵横天下,骋驰疆场的八骑铁骑。但没想到,接下来从他略带台湾普通话的口音中,带出来的故事,是那般离奇转折如粉墨登场般的戏说人生。房内炉火上的茶水依然翻滚着,彷佛配合李君要说的故事般,也是由一个翻滚的故事开始。
“记忆中…”李君低沉的嗓音,广播般的缓缓揭开了故事的序幕。中国第一部自摄的电影,也是中国第一次尝试拍摄的影片《定军山》,是由京剧的名角谭鑫培,在北京开拍。二十年后,同样在北京大吉巷胡同里,祖父李老爷子,以独门的翻筋斗身手,后翻往前两个转身的翻滚方式,在胡同里开创出了一种新的翻筋斗技法,而且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云里翻”。但也因如此,街坊奔走相告下,“胡同里的云里翻”这样的名号,开始在大街小巷中口耳相传,名声鹊起。于是“鸣春社”京剧团,在愈来愈多慕名前来学艺之人中渐渐创立,也就是“新华京剧团”的前身。
“丈夫是京剧的武生,妻子自然也巾帼不让须眉”,李君替自己斟了一杯茶,略为品茗后,边饮边说。祖父虽在曲艺界闯出名号,但约己治家,还得靠女人。所以记忆中祖母就是个持家的高手,知道从菜米油盐中,找出实际的人生。虽然旧社会的观念中,男女有别,但北方人不分男女,皆性格豪迈,不拘小节,而祖母就是个地道的北方女汉子。所以有句话说:“北方娘子霸气,要打就打江山,要抢就抢官银”这样豪气的谚语,形容的就是北方女子,要做必做大事,绝不屑做偷鸡摸狗,上不了台面的事。而且祖母眼光独具,发现戏服不但可供粉墨登场,还可从戏服中流淌出银子,因此就利用戏服不用的空档,做起租赁戏服的买卖,慢慢在一分一毫攒出了家底。
各位都知道纳兰性德《云如初见》中的词句:“顷我一生一世恋,来如飞花散似烟,醉里不知年华限,当时花前风连翩……”李君翻了一下炉火,忽然吟诗般的接着说,后来李氏家族传到大伯,情况已有变,而这首词的意境,最能说明当时大伯接手家族事业后的遭遇及家族由盛而衰的写照。听父亲说,那时大伯由于天资聪颖及祖父刻意栽培下,很快的就成了当时的京剧名角。大伯唱的是花脸,扮的是关二爷,当时只要戏班挂出大伯的戏码,还没出场只要在戏台后叫个板,就能赢来满堂停不下的喝彩。当时不但名满京城,而且彷佛如同现在的明星般,一场戏唱下来,光扔到戏台上打赏的金银首饰,就可买下当时在北京天桥附近的楼房。但也因太过出名,名利双收下,成了当年盘踞北京的日本女汉奸份子,诈取金钱的目标。日本女汉奸的目的是钱,因此常以热衷艺术的名义接近大伯,而大伯当时对戏曲已是爱戏成痴,分不清人生如戏的真假,只是一味的顷注毕生为戏的爱恋。以为可以藉由艺术熏陶,感化误入歧途的骨肉同胞。
但在几次名为艺术,实为诈财的应酬后,大伯虽后来及时醒悟,与她们开始划清界线不再联系。但这段说不清的过往,已让他背负了叛国十字架的恶名。因此当日本战败,政府开始清扫汉奸下,不但让大伯百口莫辩,一切家业尽成灰,还因此被下放到蒙古,几十年后才赦回家园,只不过那时蓦然回首,已是家财散尽,两鬓飞霜。没想到从北京故居“翻”出来的基础家业,到家族繁盛的独享风华,曾由铺满现大洋步道,撑起的锦绣屋瓦,一夕之间,朱颜夕改,成了一袭过气的华服,只记得梦中的瑰丽身影,梦醒的百孔千疮。每当想到这里,耳畔依稀还可以听到父亲当时的叹息,大伯一生爱戏成痴的后果,换来的竟是这般“顷我一生一世恋,来如飞花散似烟”的人生。
李君放下茶杯,看着一室意犹未尽的寂然,停顿了一下,彷佛努力回想着过去,又给自己斟了一杯茶接着说:1948年,当初的“鸣春社”已改名为“永春社”。该剧团赴沪演出时,当时台湾已光复,回到祖国怀抱,因戏班名满天下,所以专门来员邀该社赴台演出。因当时国共战况不明,不敢前往,但在台员力邀下,祖父再三斟酌,为避免得罪当道,不过也不敢孤注一掷,只好由三伯及父亲先随马派名角前往,以观后效,但孰料一去,从此海峡梦断,骨肉分离,兄弟未再团聚。
16年后,家族第三代的我,诞生在台湾北部的家。但当时我是早产儿,在那个医疗不发达的年代,早产儿的存活机率原本不高。后来在当时台湾的国防部长知道后,他刚好也是戏迷,而且当时社会的认知京剧是国粹。于是只说“名角之身,岂能无后?”一句话,就将我拖出阴曹地府,从阎王的手中抢回。从此不但将我勾离生死簿,也让成年后的我,依然进入台湾的演艺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艺术。这样的人生出场方式,只能说在人生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不生今世生何世?!
故事说到这里,已是满室欷嘘,没想到李君的人生,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出世。但李君似乎依然沉甸在记忆里,扳着手指头计算着时间,继续诉说着过往。时间来到1986年,两岸终于放下恩仇,开放探亲。50载的骨肉分离,终于走到团圆的关口。其实人生的际遇大多事与愿违,譬如有很多机会相见时,却总会找借口推脱,但等那天真想见的时候,机会已经没了。而有些话,也有很多机会可以说,但却总想着以后再说,但等到真有话想说的时候,又已经没机会说了。
所以在两岸分隔的年代里,父亲房中偶会传出,胡琴咿咿呀呀的声响,在万籁寂静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彷佛诉说着悔不当初,没能多说几句,那失散的手足,与数不尽的乡愁。后来两岸对立的关系渐渐改善,在母亲四方奔走下,终于把远在老家的大伯,以探亲及结合两岸演出之名,来到台湾与两个亲兄弟,共同演出了当年在台湾,造成盛况空前的戏曲《桃园三结义》。
梦里不知身是客,错把他乡当故乡,骨肉离散五十载,一年能几团圆夜?李君有点感叹的说:半个世纪的等待,换来的依然是翻转后的人生,只是人生是翻转,戏也是翻转,与原著不同处,在于兄弟以京城离散始,以桃园结义终。分离后的相遇,只是久别重逢,台上义结金兰的同时,台下满场的泪眼婆娑。
李君放下了茶盏,看看窗外,斗转星移夜雨已歇,一室的寂静中带了些许淡淡的哀愁。多愁善感本是文人雅客的专属,只是面对如此动人真实的过往,大家心中都希望接下来,听到的是多一点令人高兴的事。但李君似乎了解在座的心境般,并没有如大家的意,持续说着跌宕起伏的人生…。进入演艺圈后,虽表演方式不同传统,但浅碟式的新媒体艺术,成名却意外的快。出道不久,我已是街头巷尾的明星人物。但人生的顺遂,常让人忘记悲苦,以为门外浩荡的明媚春光,皆是为已而设,直到恶耗打上门来。
从小到大,父亲扮武,母亲善画,一文一武,夫妻恩爱,如鼓琴瑟。所以无论天涯海角,在世上那个角落奔波,家给我的那份安适感,就是父母俱在。
父亲骤逝消息传来之前,我在百里之遥的南方拍戏,夜半父亲入梦,安详慈爱,温情款款,如沐春风,但似乎欲言又止,梦醒起身,泪湿枕畔,犹有余温,心知不祥,但江阔天远,归乡已迟。我常以为人生很长,年轻有的就是时间,但当父亲离我而去,我才知原来在死神面前,最不希罕的,就是年轻。也许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一不留神,已天人永隔。
原本担心母亲,因夫妻情深,孤凤难鸣,但母亲出奇的安静,只淡说了一句,“父亲没留什么给你,只把祖传三代的全套戏服及唱本放在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是祖父传给他,现在他传给你,这就是家族以后的传辈之物,你要好好保存发扬。”说完将箱子交我后就转身回房,提笔练字。当下我不理解,为何母亲脸上看不出一丝哀伤?直到我悄然进屋,看进母亲双眼无神,只是低头不语,默默写着“半世情缘东逝水,一寸相思一寸灰”才剎时明白,原来大悲无声,真正的哀伤,不是嚎啕大哭,只因痛到深处,无声无息,只好藉字解忧,从一笔一划中,一个字一个字的救出自己。
故事到此,情真意挚一室凄然,李君虎目也彷佛洴出泪花,往事似乎触到了他内心最深层的伤痛,但大家都知,既然话已说到深处,就不如让他诉尽悲苦。因为人在诉说着哀伤时,默默的当个听众,或许就是对当事人最大的安慰。因此举坐默然,仅是帮李君斟满杯中的茶水,翻滚的茶香似乎冲淡了些许忧伤,缓了口气后李君接着诉说翻滚出来的故事:人总以为明星过的幸福,其实人是在接近幸福时倍感幸福,在幸福进行时却患得患失。父亲留给我的“箱子”,其实我明白就是一份延续家族传统艺术的使命。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尤期是演艺圈,到处都是污泥浊水阴谋诡计,这般沉重的使命,一个小演员何能奢求幸福?但即使如此,明谋暗算潜规则得来的幸福,也不值出卖灵魂,无需留恋。虽然成名要趁早,晚了,滋味就不同。但人生如戏,过眼即逝,虽也曾独领风骚,但父亲骤逝,激起反思,所托付的延续传统艺术的使命,更是沉重。所以直到历经生死,几经辗转,才知家族世代荣宠的传统艺术,早如根深柢固的骨髄血液,牢牢深植遗传基因中,而对传统的眷恋,是不知几时起的爱意?早已如此分明,只是自己难辨。
只是突如其来的生离死别,虽容易让人大澈大悟,但时间太短,还无法立即明白过来,只是觉空虚,不知失落了什么?直到了解至亲至爱之人真正对我的期望,对整个家族传统艺术的执着,才瞬间顿悟,彷佛蜕变前的挣扎,直到破茧而出,深埋在心中那份家族传统艺术因子,才终于幻化成蝶,开花结果。
“原来李君终日为传统艺术奔走付出的原因在这!”大家心中忽然明白过来,难怪今夜友人一定要邀他前来,因为一屋子都是传统艺术的爱好者,不是戏迷就是票友,传统艺术没落也常是朋友闲谈之间忧心的话题。因此虽时至深夜,骤雨已歇,但月明星朗,一室的情绪显然被李君牵引出了惆怅及期望,于是大家都打起精神,听着李君似乎还未说完的故事……大伯来台演出的震憾,加上父亲后来的骤然离世,从那开始,彷佛有个声音,不时在心中燥动。后来也曾回大陆探亲,但当循着地图一步一问终于找到故居后,却发现故居已是一片残砖碎瓦,满目的杂乱荒芜,儿时心中的故乡,怎成这般不堪?
走进破败倾倒摇摇欲坠的前堂后院,拾起几块掉落地上的残砖破瓦,瓦砖上镂刻的花纹彷佛诉说着曾有的繁华,百感交集中蓦然抬首,彷佛回到梦中祖父“云里翻”的场景,及父亲银盔白袍的英姿,在锣鼓声中,黺墨登场。瞬间明白,原来此生最爱依旧在回眸近处,就是父亲留给我的“箱子”,象征家族传承的国粹艺术。因为世上有一种东西,它就是对的,就是好的,只因它原本如此。电子媒体再发达,演的是皮相,但真正内心深切处,还是那份家族血液骨髄中流淌的传统,于是一种复兴家族及传统艺术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因此探亲完回台湾后,在使命感的驱动下,觉得传承是迫在眉睫的事,于是向台湾戏曲学校,申请了在职专业先修班。希望能带领学年青的一代共同深造,为台湾未来传统艺术播下希望的种子。后来继续攻读硕士班,与年轻的学子接触多了,才发现原来年轻的孩子就像初阳里的新枝,或刚刚会得吃食及嬉逐的小猫小狗,以为人生的幸福,就是学校上方的天空,但外面的世界,却是一无所知。
21世纪新媒体的浪潮如排山倒海,不但将原本的电子媒体冲垮,传统艺术更是日薄西山,后继无人。在这样艰困的媒体环境中,这群如初阳般的新兴艺术学子,将何去何从何所依?有很多人希望我们这一辈的演艺人,对传统还有坚持的人,能留在学界教育下一代学子,但演员只能做戏,教书却是做人,要演员教书,等于要做戏又要做人,如何堪此大任?所以教育的断层,才是传统无法传承的主因。
仿佛找到答案吐尽了心事后,大家也有心头的沉重终于放下的轻松感。掷地有声的论点,虽不时让在坐的友人频频赞许,但大环境变了,这样的坚持能坚持多久?“接下来你要怎么做?”一阵沉默后,友人向李君提出了疑题:“三生石之约的佛经故事,大家都知道吧?”李君彷佛早想好答案般不急不徐的说:其中所说的前世,今世,来世,就是回应先前我说的,为过去,现在,与未来所铺陈的理想做的总结。因此第一步就是先充实自身的本职学能,所以我先去念修了硕士。然后接下来我已向台湾当局申请成立了一个“戏曲交流协会”,目前已有几场两岸青年戏曲交流演出,正紧锣密鼓的筹办。最后就是要靠在座爱好传统艺术的前辈,也帮忙宣传推广传统艺术的重要性,毕竟国粹式微大家都有责任,团结力量大,我几乎就是抱着抢救的心情,也希望能藉此抛砖引玉之势,吸引在座或更多爱好传统艺术人士,共襄盛举,以毕生之力,振兴梨园。
而且我将以“三生石上旧精魂,此生虽异性长存的”的言出必行,守信重诺的“三生石之约”故事精神自勉。希望能为传统艺术发扬传承,提携后进,尽绵薄之力,虽然我知在当前网络新媒体如爆炸性的影响下,复兴传统艺术之路依然艰难遥远,但我也坚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坚持心中对传统的热爱,努力付出洒下希望的种子,总有一天我的热诚,会有如“精卫填海”般感动影响更多重视传统艺术的人,大家说对吧?
李君的问句虽然表明的是一份对传统艺术的热爱,但“我觉得你这样的理念,不只像精卫填海,更像愚公移山!”在座友人悲观的说出了现况,但李君只微笑了一下说:如果问我传统已死,这份热爱可能不值,我只能说,爱,就是不问值不值.虽然说的好像做得了主似的,但你说像“愚公移山”倒是贴切,但世上总要有些傻子,而我恰是。
清朗的笑声,总算将整夜的忧伤带回了欢乐。世上确实有许多傻子,但如此傻的可爱又令人可敬的真得不多。日渐污浊的世道里,何其有幸还还能遇上一个愿坚持理念的人,这样的人虽不多,但要是每人都能为正确的事多一点坚持,或许世上就能少一点令人扼腕叹息的事……
月影西沉,夜色转深,人车渐歇的城市里,不一会儿,又将迎来充满希望的晨曦。
喜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