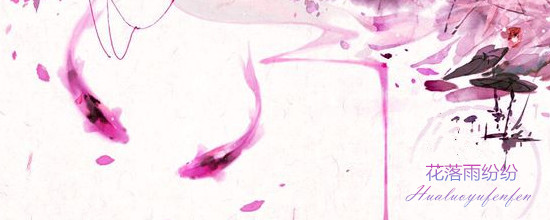【桃源道】鸡蛋过道儿(散文)
【桃源道】鸡蛋过道儿(散文)
小镇地狭,却因了千百年来制瓷业的繁盛而人口集聚。小小的镇子之内,人口却集了有数万之众。人多了地势偏又不开阔,各家院落、房屋也就因了地势建得高低错落,你家房挨着他家屋,他家门楼又搭在别家院墙之上,就那么挨挨挤挤地一片连着一片,一总儿地集在那如锅底般的狭地之内,如煎炖着的一锅豆腐。
就连本该是作为镇街骨架存在,那些通往各处的道路,反倒几乎就成了房舍的附属品,绳线样穿着这家连了那家,来回扭动着随房屋设置在镇街内摇摆。方位感不强的外地人,来了镇子行走根本摸不着头绪。
这样的一种房屋布局状态,就决定了镇内的街巷杂乱且狭窄。除了作为南北纵轴线存在的市场街之外,你很难能找到一条直路出来。
镇内原来算得上马路的街道,归总起来也勉强能算得上三纵三横,就这大多还都是穿寨破墙后才修起来的。至于除马路之外的那些个胡同、过道儿、门洞之类的小路,则是多得数不胜数,枝枝杈杈地将那些马路相连通,如小镇身上长出来的毛细血管。
而在小镇众多的过道儿之中,有真正属于自己名字的并不多,能够被人经常行走,却又老挂在嘴边儿有名字的过道儿,自非“鸡蛋过道儿”莫数!
鸡蛋过道儿,原是被夹在伯灵翁庙西侧围墙与望嵩寨西墙根儿之间的一个通道,宽不盈五米,长不及百步,专司联通行政街与北寨街两条道路之职。其实,这两处道路原本分属两个不同的寨子,南边的叫望嵩,却被人称为东寨;北边的寨子寨墙和寨门早已经被推倒,而少有人能记住其旧名,终被乡人通俗地称了“北寨里”。
这鸡蛋过道儿既被称为“过道儿”,便说明其地位仅是一条小路而已,本不负担连通南北的重要功能。然在1957年,那座修建于明永乐三年,连通“天保”“望嵩”两寨,横跨于肖河之上的驺虞桥,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而被冲毁,从而致了两寨间南北大通道的中断。
原本东边望嵩寨的人们是从桥上过来,经天保寨内的一所大桥再行向北入市场街。这驺虞桥一断,东边寨子的人西行不再方便,就只好经了原本是一条小过道儿的鸡蛋过道儿过来,向北入建设路,由建设路向西之后复向北行,才进了镇内南北方向的市场主街。这样,一条原本作为小路使用的鸡道过道儿,便承载了东寨居民进入市场街的主路功能。同时,这鸡蛋过道儿又成了北寨居民经由此处进入肖河洗衣、看河道发洪水、跳水玩耍的主通道,其交通地位就变得十分重要。
关于这鸡蛋过道儿名字的由来,因其原本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人们并无专门刻记,着实是让人一时无据可考。我曾因此向父亲做过求证,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大家都一直这么叫着,并无人专门数说过它名字的由来。据说是以前常有人挎着篮子于此处售卖鸡蛋,因而得名;也或许这过道儿中间稍粗两端收窄,近了卵圆状如鸡蛋,由此而名也未可知。但仅就我个人来说,觉得前一种的可信度较高。我也的确是小时候见过有人在此售卖鸡蛋,人们以此命名当是不足为怪的。
因我家住在桥南的河边,而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外婆家,我们那里管外婆叫姥娘。)则住在北寨里。我若是想要去姥娘家,则必要过了肖河经由东寨门进入行政街,尔后前行约二十步左拐,由鸡蛋过道儿向北进入北寨里。这样,鸡蛋过道儿便成了我去姥娘家的惯常行走之路,对它自是多了份记忆和关注。
鸡蛋过道儿南端,所正对着的是镇内的老电影院。说是电影院,却是解放后所建的露天影院,自我记事起就已经废弃,成了别人家的院子。里面有狗,我们自是不敢随便入内的,也就不晓得它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只是知道那影院的墙十分地高大气派,充满浓郁的革命气息。
过道儿的北端,则是穿了建设路就直入北寨街。这临了建设路过道儿口两侧,就常有挂着“温家烧鸡”和“清真”字样招牌售卖熟鸡肉、牛肉的摊点儿在摆着。且不说能否吃得起,就仅是看那肉食的色泽和嗅那飘来的香味,就使你常常垂涎三尺。再加上旁边那个卖火烧儿的摊主,不时地将他那火烧坯饼往鏊子上“啪啪”地摔着,用声响来招揽食客,常就诱得我将自己的口水往肚子里是咽了又咽。
然而,就在这过道那不足百步的长度里,却也隐着两处院落,一处东北,一处西南。
居于东北的黄墙灰瓦,系一处老宅院,不深却旧。门洞与一间门面相连,门是那种旧式的竖排木板门,营业时一块儿一块儿斜着摘下来,门洞大开,内里货柜、物品一目了然。印象里那铺子常售些日常零碎、副食、酱醋茶酒,也卖炮和小鞭,习惯上我们将这些售卖东西的地方叫做“代销点”。
我曾去这个以旧式瓦屋作门面的代销点打过几次酱油,五分或是一角钱一提子的那种。如今已经记不清楚确切价格,只知那提子便是量器,竹筒或是铁皮制成,标准或不标准不得而知,但却是以提计价。从那盛装酱醋的酝子里,舀出一提就是一提的价钱,依你所拿的钱数或添或减,童叟无欺。倒是省了许多称量和计价的麻烦。
我也曾用爷爷给我的二分钱,去这店里买过水果糖,花色蜡纸包裹的那种。蜡纸里包着的是泛着棕黄透明的那种硬糖,一分钱一颗。具体是什么果味儿我吃不出来,只知那上面画着个简单线条的香蕉和菠萝,质硬且甜,咬着吃时会发出“嘎嘣”声响。只是我极少会舍得去用牙咬碎嚼着吃,而只是用嘴含着,让那甜蜜在嘴里留得尽可能久一些。毕竟,这样的幸福不常有。
过道儿西南一隅,则是一处新修小院,依着寨墙走势所凸出去的部分砌出一个长三角形宅院,院门向东而开。因其墙高且院门常闭,内里究竟若何,终不得见。但因是新盖院落,院墙都是用砖砌成,全不似小镇它处建筑的砖柱石砌灰抹,便暗想了这家许是有钱,不然是断不敢在房子修建上如此花费的。
后来,也终是印证了我初时的判断,曾见过他家门口许多次都停了桑塔纳轿车,且是“9”字开头的私家车牌,这在当时是极少的。也正是因为对这家院子主人是有钱人的判断,我自就觉得矮小了许多,常就绕到他家对面的路边行走,恐他家会有大狗出来,误就把我当了叫花子来咬。
前些年,我再回去,却见了肖河上有了新修的驺虞桥,虽不古朴,却也使东西两寨行走起来便捷许多。桥头所立《重修驺虞桥记》,自是要记述一番此桥的由来、毁坏及重修出资人的功德等等。但不管怎样,既有了桥,这东西的通道便已打开,人们再要经由鸡蛋过道儿去市场街的就会少了许多。于是,那鸡蛋过道儿便又复归了它过道儿原本的功用,只在人们需要时才经此顺路而行,不再作为南北主通道使用。
去年,再回故乡,和好友志刚一起带着孩子去了南山,回来时经由驺虞桥入了东寨,去吃那里一家极具传统风味的酥肉、条子肉蒸碗。那家小店便开在老电影院一角,几乎就直对了鸡蛋过道儿,我们也就经由那鸡蛋过道儿去建设路上买了火烧儿。许是因时已过午的缘故,又逢夏日炎热,街上并无多少人行走,那鸡蛋过道儿里也更是鲜有人过,只余了我们两大两小的四人并排而过,这过道儿便显得格外地落寞了许多,再无了往日的人来人往。
前段时日,有些许空暇,便想着用自己的笔作语言,多写些故乡的民俗风物给大家看。在写有关鸡蛋茶和月子待客送米面中的红鸡蛋时,无意间竟联想起了镇内那个叫“鸡蛋过道儿”的街巷小道儿,就觉得自己该把它也写出来,以纪念那条小镇人所熟悉,却又时常被漠视掉的鸡蛋过道儿,也算是对它曾留给我童年许多记忆的一种答报!
今夜,我苦苦思想半晚,一番字句斟酌后,终是做到了,兑现了自己对鸡蛋过道儿的文字纪念。此后,便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