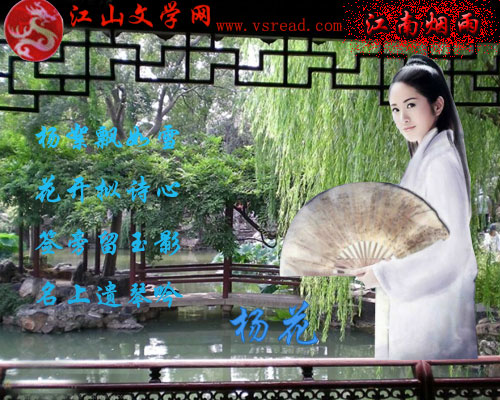【江南传奇】 啊,中秋,中秋!(散文)
【江南传奇】 啊,中秋,中秋!(散文)
一
1967年,是一个疯狂燥热的年头,与世人深陷歌如潮、旗如海的红色飓风中“执迷不悟”一样,老天爷也赶来凑“热闹”,秋旱连伏旱——整个暑季39度“高烧”经久不退。
9月18日,是中秋节。
这天,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身着当时颇为“时耄”的蓝白相间的“海魂T恤衫”,肩挎黄色小书包,足蹬一双半新旧的解放鞋,踢踏着露珠与碎石,沿溯一条不知名的小山溪,经潭口,进周洛,疾疾行走在进山的一条碎石黄尘小道上。
夹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峰峦叠嶂,飘渺的晨雾尚未散去,山道上杳无人迹,清新的山风不时将竹林深处斑鸠的咕咕叫唤与树枝梢尖黄鹂清丽悦耳的啼啭声传入耳鼓。行走途中,间或有横跨溪流的高高小木桥和依山伴水的秀美吊脚楼在眼前一闪而过;透过薄薄晨曦,山崖脚下那一大片错落静谧的陈家祠堂上袅袅升起的炊烟依稀可眺,姚家老屋场中遥相呼应的声声犬吠隐约相闻。我无暇顾盼眼前这水墨画般的山间晨光美景,只顾忙不迭地迈着脚步,向上,向前。一为着壮胆、二为排遣内心的孤独,我嘴里低声地、一遍又一遍地轮番唱着当时极为时髦流行的毛主席的诗词语录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越往上走,路越来越窄,溪流也越来越激荡。待到火辣辣的日头透过重重峰峦照射在山道正中央、我身上的海魂衫也被汗水浸湿了时,一个巨大的,吱呀、吱呀作响,幌荡、幌荡旋转着的打水筒车出现在眼前——脚下的路没有了。
一座大山劈面突现在面前。
我仰身举目,只见眼前灌木稠密,林木葱茏,稍高些更是云遮雾障,青烟缭绕,莽莽苍苍根本无从望见峰顶,低头瞧去,前面不远处的荆棘草丛中,一条长着些许青苔的崎岖石板小道若隐若现地蜿蜒而上。
是不是就是这条山路?我竭力分辨着,试图还想从身旁其他地方找到一条类似的山道加以比较。要知道,“望山跑死马”,我是输不起时间来回折腾的。
正当我徘徊几度拿不定主意时,一位中年樵夫“哼哧,哼哧”地挑着满满一担柴禾从前方这条弯弯山道上一步一滑蹒跚而来。
“借问大叔,往东乡是从这里路过吗?”
待他走到跟前,我迎了上去,满面虔诚地向他问道。
中年樵夫一脸困惑地瞧了瞧眼前这位赤手空拳、稚气未脱的少年一眼,答非所问道:“后生,你今年多大了?就你单身一人过山岭?”
当得知年仅18岁的我不得不独身翻越这人迹罕至的山岭时,他转过身去,指着前面说:“确实,这就是连云山!进山后,经‘百兑庵’,上‘十八盘’,过‘三窝’、登‘五坡’……大叔一连串说出几个小地名后接着又道:再往上走十好几里路,就可到顶了,过岭背就是你们东乡,当然,下山的路好走一些,但也还要走‘岩前’、穿‘大光洞’走上三、四十多里山路才可以到达沿溪桥。”
我连连向他点头称谢。
待我正打算试探着分开没膝深的草丛向其间的石板路上迈出第一步……
“回来!”身后的樵夫叫住了我。
我应声回望过去,只见樵夫放倒肩上的柴担子,脚踏柴担,用双手从中奋力扯出一根比肩般高、酒杯粗细的桎木棒,抽出随身斜挎在腰上所带的锋利柴刀,三两下除掉枝桠,随即将它一头砍削成尖头的“鎍标”后,递交到我手中并不无关切地说:“山高林深路滑,用这个一来防身壮胆,二来还可探路防跌倒……”说完,不待我再次道谢,只见他摇摇头,弯下腰、“嘿”的一声挑起了柴禾担子,晃悠悠地离我而去。
望着樵夫渐行渐远的身影,刚刚他所说的话还在耳畔回响,面对身前这巍峨挺拔、空旷幽森、深邃莫测的高山峻岭,孤身一人、手执桎木棒的我,相比之下显得那么猥亵藐小。
不知为什么,对下一步的行动,我开始有点犹豫不决了。
如何办?是继续往上,还是从原路返回?我几番踌躇,不敢轻易造次提足向前——要知道,迷失在荒无人迹的大山中,后果只有一个……
以往,下放江永的兄长曾向我叙说过:江永高泽源林场一位知青迷失在莽莽大山中,方向尽失地在风雪弥漫的深壑幽谷中盘桓了三天三夜、最终没能走出深山老林而冻僵饿毙的凄惨结局,更加深了对眼前这危崖高耸,绝壑连绵的次原始大山的无比恐惧。往回走,来回仅仅多走了四十多里的冤枉路,不过生命的安全系数可能会大一些。然而那样,我的人生道路却可能面临另一番选择。
二
恍惚间,昨天所发生的一幕又清晰地映现在我眼前。
因为年龄幼小,身体羸弱,不堪繁重的农业劳动,又因我的一贯“表现”突出而得到队上贫下中农的特许,几经辗转,寻访到地处平江与浏阳两县交界的大洛公社拜师学习木工手艺。
昨天午后,在接受过十数天身心疲惫的准学徒生活的“考验”、刚好举办完正式拜师酒、签名立下“如有寒暑各负其责”之类话语的投师状之后,几位戴着红袖标、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以清查“盲流”人员为由,凶神恶煞地出现在我面前。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人与人之间将一切亲情友情全部抛弃殆尽,剩余的似乎只有一种敌对与仇恨的关系。面对所出现的陌生人仿佛都是青面獠牙的“帝、修、反”与阶级敌人似的,因而脱口而出的每一句问话就像是审问犯人,而从口中说出的每句话仿佛扔在地上的手榴弹——充满了火药硝烟味。
“出身、职业、家庭住址、有无证明?”一位五短身材、长着一脸横肉、看着像一位为首的头目模样的人物咄咄逼人地向我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从前,可不像当今,每人都有一张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证”便可放胆行走于四方,而且不必向他人自报纯属个人“隐私”的“出身”;而且,一般人外出之前,都要在“户口”所在地的大队去打上一张足以证明自己“出身”、现实表现以及行动去向的证明。并要盖上“大队革命委员会”大红印章才能生效。
望着这帮气势汹汹、耀武扬威的“活阎王”,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证明……”我望了望师父顾左右而言他地说:“我出来的时候,大队管公章的人不在,所以没有带。”
“没有证明,那……你就带上自己的行李,随我们到司令部走一趟!”
望着他们个个荷枪实弹一副不容置疑地神色,想起不久前在湘南一个叫道县的地方所发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任意将当地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当作“地、修、反、封、资、修”的“残渣余孽”以最原始的锄头,砍柴刀乃至直接推下几十丈高的天坑等方式惨无人道地屠杀成百数千无辜民众,并将屠刀鸟铳很快指向“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使之也横遭屠戮而惊动了中央文革的惨剧时,心中感到阵阵发怵,腿肚子也禁不住打起哆嗦来……我无奈亦无助地再次望着师父。
站在一旁的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每人给他们递上一支“红桔”,面带笑容地说:“都是本地人,好说,好说。我担保:×司令——我这个学徒成份虽高一点,但从这几天看来还像是一个老实本份人,绝对称不上是什么坏人,至于证明嘛……要他回下放所在大队打一张回来,要得啵?”
“那好吧,就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三天之内将证明带来,交给我们验证,否则最好不要让我们再看到你!”点燃香烟之后,来人口气松了一点,但态度仍然冷冰冰、硬梆梆的,绝无回旋余地。
“妈呀,三天打来回?这简直比登天还难!”我差点从心底喊出来。
要知道,两地公路距离有三百余公里,因为需要经过县城而不得不绕一个大弯,中途需转乘两三次车、按正常情况要四、五天时间才能来回,加之文革中势不两立的“两派”之间,最近在县城武斗正酣双方均死伤不少,而通往各地的公路要道上,交战双方早已重兵对峙,森严壁垒地各自把守着所有过往路口关隘,开始还仅仅严令禁止一切不同观点的车辆人员过往通行,最后干脆将公路全部“封锁”。
“三天要我打来回”,这分明是不准许我在此地继续下去。然而,从内心来说,我还真割舍不下这一好不容易寻访到的、自己今后赖以生存的机遇及想成为鲁班传人的梦想。
看着我垂头丧气、一筹莫展的样子,待这帮人前呼后拥地扬长而去,师傅一把将我拉到门外,指着远处的一条黄尘小道说:顺着小道、沿着旁边的那条山溪径直朝周洛山冲里走,待走到路的尽头,就是连云山,山上有一条古驿道。早先没有官道不通班车时,田少人多的北乡村民都相邀结伴从这条古道翻山越岭,前往你下放所在的东乡帮助田多人少的村民们插田扮禾,凭力气挣些零花钱,不过……由于修筑了公路,通了汽车,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走了。”一口气说完后,师傅回头望了望我,那神色似乎在对我说,有没有这种勇气?就看你自己的了……不待我回答,师傅继续道:“只要你能吃得下这份苦,早起晏宿,翻越大山后,说不准三天之内能返回。”
于是,第二天——9月18日,也就是中秋节的这天一大早,接过师傅递给的两个熟红薯、身怀二元钱与半斤粮票,我“雄赳赳、气昂昂”地上路了。
显然,临分手时,师傅他并未将翻越大山的困难说得这么详细具体,是担心一开始将翻山越岭说得过于艰难我早早地打退堂鼓?还是希望我这位出身于城市中的学徒能克服困难走出困境,成为他今后的赖以向外人炫耀的得意门生?我思前想后,不得而知。
“门前两条辙,何处去不得?”
踌躇中,蓦然,我脑海中蹦出这豪气干云的古训。为了自己能如愿“生存”下去,暂且借眼前这座高耸云端的大山作为自己人生的一次历练吧,说不定坎坷之后是坦途。一时间,单身穿越崇山峻岭的想法占了先机——年轻气盛的少年将一切恐惧与懦弱抛向了身后。我弯下腰去,饮了几捧清冽的山溪水,摸了摸斜挎在身后装有红薯的书包,抖擞精神,分开草丛,向深邃的大山迈出了第一步。
三
所谓“十八盘”,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之”字山路。只不过眼前这一条由块块石板垒砌完成的、超过45度坡度的“之字路”,每条“之”字的边长约有几十米。当我用自己的脚艰难地一步一步“丈量”、“数完”百十级青石台阶铺设所组成的一个巨大“之”字时,透过浓密的竹梢树枝藤蔓,探头朝脚尖下方刚才走过的路望去,其垂直距离依稀有五、六层楼高。我咬紧牙关,低着头在心中默默地记着数:一个、两个……
显然,“十八”也只是一个概数,就像人们通常用“九”比作数量极多一样。我一边攀登,一边还不得不打心眼中佩服朴实的山民——将无数个艰难卓绝的“之”字,轻而易举地归之于“十八盘”中。
愈往上行,山势愈陡峭,随着上行高度的变化,行进中的我,愈感气喘嘘嘘,大汗淋漓。然而一旦转到山窝中的背阴处,便顿时感受到一种清冷阴森之气扑面袭来笼罩于全身:明明已近中午,四周却像薄暮时分,树木遮天蔽日,雾气重重,竹梢树枝还不时有滴滴水珠往下滴到头顶,石板山道上积满了厚厚一层枯黄腐朽的树叶,走上去蓬松松、湿漉漉,滑溜溜的,一股股陈腐淤臭的气息直往鼻孔中钻,行进中不时要上前走三步往后退上一步,方能站稳脚跟不致滑倒跌落于山涧之中,阵阵山风过后,漫山遍野的松涛所发出的撼天震地、犹如熊吟狼嗥的滚滚松涛声,更加彰显空寥沉寂山林的荒凉与恐怖;在盘根错节弯曲虬枝如巨蟒匍匐的枯藤缠绕密不透风的丛林深处,不时传来黑鸱鴞“哇、哇”三两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尽管脚步逐渐沉重,我亦不得不奋力加快脚步。
当然,只要走到当阳的南边山岗,还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密匝匝的树枝竹梢的遮蔽,似火的阳光即使穿透进来也柔和了许多,浓密的树盖映荫下的山道上闪烁着扶苏点点,黄莺斗嘴,蝉儿恬噪,间或出现在道旁的丛丛烂漫山花,招惹群群粉蝶漫舞其间。行走中,成串的暗紫色的山葡萄与毛茸茸的猕猴桃不时出现头顶上方,引得我禁不住驻足流连其下,想法采摘下来大嚼一番。此时,我全然忘记了独自登山的艰难与烦闷,乘兴对着空旷幽静的山谷大声唱起“十送红军”来,歌声从对面山崖峭壁上不断地反射回来:“介支个……介支个……再回山……再回山……”
随着时间的逝去,我渐渐适应习惯了独自行走于清新凉爽、空旷山林的寂寞。除感到些许有点孤单之外,好像并没有遇上什么真正的危险。
此时此刻,如果读者和我一样,认为樵夫大叔的话似乎有点夸张或言过其实,认为就像在宽敞的城市街道上惬意舒心地闲庭信步,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经意间,一次生死时速的生命考验在向我悄悄逼近。
登行到半山腰一处当阳山坡,见地上撒了一层黑红色的早已干瘪萎缩了的杨梅核,我举头看到身子正上方的荆棘灌木丛中,一棵依山傍墈、旁逸斜出地伫立着一棵杨梅树,望着果实全无、枝叶依旧浓郁繁茂、枝粗干高的杨梅树,心想,若是早几个月的小满前后打这经过,眼前这棵杨梅树肯定满挂着红灿灿熟透了的杨梅,不管怎样都要想方设法爬上去,置身于枝繁叶茂的树干上,对着前后左右上下八方、酸酸甜甜的杨梅果大快朵颐,心动时,嘴角唇边早已唾液涌动,好像已经品尝到了鲜艳可口的杨梅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