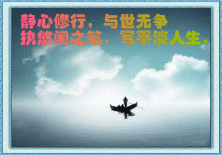【晓荷·天地事】旋木艺人老父亲(散文)
【晓荷·天地事】旋木艺人老父亲(散文)
父亲今年七十五岁,是个农民,确切地说在旋木玩具行业,父亲是个德高望重、技艺精湛的民间旋木艺人。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民间工艺多姿多彩,老家鄄城农村旋木工艺儿童玩具已有300余年历史,旋木材料绿色天然,旋木手艺多姿多彩,蕴含着丰富的民俗内容,不仅在艺术风格上体现了浓郁乡土文化气息,在深层次上也体现了中华文化深潜的文化心机。小小旋木玩具里藏着大世界,更藏着我最美好的记忆。
老家刘庄村在明朝时,家家户户都加工出售“哗啦棒槌”,故有“哗啦棒槌刘庄”之称。起初旋木玩具只是给孩子当做玩具,旋木艺人在农闲时旋制而成,以圆或椭圆为主要造型,圆的是响蛋,椭圆带把的是哗啦棒槌,通体染成黄色,在加上红绿道道的图案,十分醒目;里面装上几粒小石子或沙子,然后安上把,堵住孔,摇起来哗啦响,工艺特点很鲜明,十分好玩,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老家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孩子哭,找他娘,他娘买个哗啦棒晃一晃,逗得孩子小嘴一咧喜洋洋。”后来,这种手艺逐渐成为村里人赚钱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我们村也被冠以“旋木刘庄”之美誉。
旋木伊始,品种较为单一,主要旋制各种实用刀把、木碗、花啦棒槌等。又由于当时旋木设备简陋、技术保守,还有传男不传女一说。致使这一工艺虽发展了几百年,但直到解放时,工艺及品种均没有大的突破。解放后,随着旋制刀具的改进和旋制技术的提高,旋木品种不断增多,这一传统民间工艺才得到发展。经过几百年来的发展演变,旋木品种逐渐发展到60多个品种,通过因材而异的加工,取得各种不同的效果。1979年,鄄城旋木工艺品厂建成,我父亲等三人被聘为该厂技师,1980年又聘上海工艺设计师来厂指导,旋木玩具开始批量生产,才得以让家乡传统玩具艺术的风采展现在大江南北。
父亲说,做旋木玩具的木材选择有一定的讲究,要选取二至三年以上生无果节和虫眼的干木。老家当地盛产杨柳、梨、枣、槐木,一般是以这些树木较粗点的树枝为原料,剥去外皮风干,过干坚硬难以加工,过湿则容易导致干裂变形,功亏一篑。
父亲制作的传统老式旋床,加工原料适用长度为50厘米左右,其粗细可在1.5厘米之间自由调节。因旋木轴头碗直径为4.5厘米左右,所以,要根据需要加工的工艺品大小、粗细、长短,将木材用锯截成一段一段的长短不一的条块,再用斧子砍成圆柱状,粗于轴碗的原料在旋做时要将原料的一端砍削至适用,卡在旋床上的轴碗上;细于轴碗的原料在旋做时要将轴碗用木块填死,再用钻刀钻出适合原料粗细的孔,才能安装原料开始旋做。
老式旋床的动力由人脚踩提供,在旋轴中段缠绕三圈指头粗细的麻绳或更细些的皮条,绳的两头下垂分别系住两根木棍的前端。木棍的后端则搭在机架座机板下的横杆上。旋木者坐上座机板,靠双脚上下依次踩动两根木棍,拉动皮条使旋床旋转;旋木者面对所旋原料,腰前顶一根木棍做支杆,支杆的一端钉有铁钉,穿在支架上的园孔内。旋木者右手持刀,左手辅佐,旋刀要放靠在支杆上,防止刀的抖动,也利于旋木者控制刀具。来回变换使用刀或钻或挖刀进行切削、钻眼、挖洞成型。
村里通电后,父亲经过不断实践和改进后,推陈出新制作出新式电动旋床,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新式旋床的出现使旋木者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原料限制也大大放宽。旋木原料长度可放至80厘米甚至更长,原料粗细也可在25厘米至2厘米之间自由调节。
旋木玩具因其靠旋转切削、钻、挖,基本成形后组合而成,所以造型以圆球、椭圆、圆柱、圆锥形为多,造型独特。旋木制品具有造型精巧别致、图案多系吉祥如意的龙凤花草图案、形象逼真、色彩艳丽、生动传神、乡土气息浓郁。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勤劳善良要强,是个受人尊重的民间旋木艺人。父亲心地纯朴,常常把对亲人的爱用默默的行动表达出来。记得我小学毕业后,不想读书了。父亲沉默许久,亲手传承给我精湛的旋木手艺,不多久哗啦棒槌、拉拉牛、捻捻转、刀把、笔筒、茶叶盒、梨木花瓶、衣架、盆架、木陀螺、、书画轴头、轴杆、彩蛋座、教学模具等等,都是我信手拈来的旋木拿手好戏。特别是哗啦棒槌、拉拉牛、捻捻转是一些孩童看了便拔不动腿的“稀罕”玩意儿。当时,我骑着父亲的大金鹿自行车,因为个子矮够不着脚蹬子,只好骑在自行车大梁上去鄄城的什集、临卜、凤凰、郑营赶集,临街占片地,就地铺下个包袱或塑料纸,兜售自制的各种玩具,瞬间便会聚集一圈拽着父母衣角缠磨着要买的小孩子,讲价讨价中,我一般是贱了价卖出去,快乐了不少孩子的童年。
记忆最深的是那年乡村干部陪着县里领导,并有记者跟随来我村采访,还专门采访了我,后来听说写了个文章“金堤脚下旋木村”。同时,在那一年里我跟着父亲学会了地里不少农活。在领悟了那时落后农村的贫乏和艰辛无奈,又重新激起了我对知识的无限渴望,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一年后,我重新背上书包走进了学堂。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像我父亲这样的一代旋木艺人渐渐老去,又缺乏继承新人,这种民间旋木工艺制品正逐渐消失,淡出人们的视野,最终将成为仅存于人们心中的美好记忆。
传承旋木工艺的父亲年岁大了,身体状况远不如从前,可他总不肯闲下来。他用心在老家专门腾出一间较大的屋子,将他用过的老式旋床和新式电动旋床都完好保留着;几十年前的旋木玩具和旋木工艺品都依然保留完好。隔些日子,他都会小心翼翼的把它们摆出来通风晒晒太阳,这些都是父亲一生心血,最得意的旋木工艺品,看得比他的生命都重要。
偶尔父亲也会重新操作一下老式旋床,旋出几个儿时最喜欢玩耍的木质玩具来,在他老人家乐哈哈“不满意、不满意”的自言自语里,我依然觉得这是最美的旋木工艺品。现在整个村子都已经不生产这种旋木玩具了,这种带着浓浓乡情的旋木玩具,现在在市面上已经很难看到,随着岁月的流逝怕就要成为文物啦。
除了在老家坚守着他的旋木情结,父亲每年坚持在院子里空闲的二分地大小的菜园里,种些黄瓜、茄子、辣椒等蔬菜。收获的季节除留够自家吃的,其余的全部分送给左邻右舍。再就是义务烧水供给乡亲喝。闲时,父亲会把枯枝木头劈成条条块块,码放整齐堆起来,每天提出烧水的小炉子在大门口,备好茶叶和一次性杯子,义务为左右邻居烧开水或供路人喝。
如今我们早已在父亲的呵护下长大成人,父母亲却也在日渐衰老。从远离偏僻的家乡小村到繁华的大都市读书,再到留在城市参加工作、成家立业,经年的忙碌中很少回家,不经意间,沧桑岁月催老了父亲母亲的容颜!我想,对于从不贪图什么物质享受的父母亲来说,也许做儿子的陪伴和看到旋木手工艺得以传承,应该是父母最深切的等待和最深情的期盼吧!
父爱无声情深深,带着对老家民间旋木传统手工艺的深切记忆,怀着对老家传统村落的无限惦记,隔段时间,我都会回趟老家小住,体味家乡的风土人情,向父亲学习并一起交流切磋几近失传的旋木手艺,在父亲深情厚爱充满期盼的目光里,我深深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正在心里生根发芽。一定会的,我一定会用心用情让父亲牵挂的旋木手工艺得以传承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