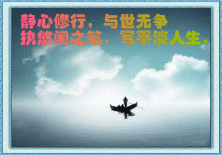【晓荷·天地事】一座不倒的精神家园 (征文·散文)
【晓荷·天地事】一座不倒的精神家园 (征文·散文)
![]() 很多时候,以为风景都在远方,从来没有想到离南昌市区如此之近的新建大塘乡还保留着汪山土库这样规模宏大号称“江南一绝”的迷宫般的家族式院落。我们不仅为建筑之美所倾倒,更为在这院落里生活学习过人们的人生跌宕起伏所惊诧。都说富不过三代,可是土库家族从一门同时出现三个红顶子,被人们称为绝世奇观开始,追随着时代的步伐,在中国从晚清嘉庆年间到民国近现代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却延续辉煌了一百五十多年,几乎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领域都有他们留下的深深的脚印。我不知道要铸就这样一个庞大而持久的文化群体,需要怎样一种坚毅和勇气?需要怎样一种隐忍和大度?需要怎样一种克制和牺牲?需要怎样一种责任和担当!这种顽强不屈精神的源头又来自哪里?土库现象在史学家们看来已经成了一个文化奇迹。后来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原来意义上的土库没有了,但是他们的后人带着长风般的翅膀过尽千帆后飞向了更远,散落在了世界各地,在那里继续开花、结果。
很多时候,以为风景都在远方,从来没有想到离南昌市区如此之近的新建大塘乡还保留着汪山土库这样规模宏大号称“江南一绝”的迷宫般的家族式院落。我们不仅为建筑之美所倾倒,更为在这院落里生活学习过人们的人生跌宕起伏所惊诧。都说富不过三代,可是土库家族从一门同时出现三个红顶子,被人们称为绝世奇观开始,追随着时代的步伐,在中国从晚清嘉庆年间到民国近现代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却延续辉煌了一百五十多年,几乎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领域都有他们留下的深深的脚印。我不知道要铸就这样一个庞大而持久的文化群体,需要怎样一种坚毅和勇气?需要怎样一种隐忍和大度?需要怎样一种克制和牺牲?需要怎样一种责任和担当!这种顽强不屈精神的源头又来自哪里?土库现象在史学家们看来已经成了一个文化奇迹。后来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原来意义上的土库没有了,但是他们的后人带着长风般的翅膀过尽千帆后飞向了更远,散落在了世界各地,在那里继续开花、结果。
——题记
不知什么时候,脑子里有了“汪山土库”这个名词。是从网上那些靓男俊女发上来的照片里得到的信息吧。这些照片有的是在春天的暖阳里,一色青葱的少男少女站在一大片金黄的油菜花地里,显得那样水灵;也有那梳着一个发辫的清纯少女倚在一扇古色古香老房子门前留下的倩影。想必这就是汪山土库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吧。哦,一座民宅。心里好像并不那么在意。“乱世逃命,盛世建楼”似乎已成了历史的一条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对许多古村落采取了保护性抢救恢复措施。这几年很多古代建筑民间老宅并没少去,如,江西的安义古村落、最美乡村婺源,深圳的大鹏所城。所以看到这样一座民宅也没太在意。
去年春节和兄弟家一起,两家人开了两部车子去看新发现的震惊全国的海昏侯墓。到了那里才知道,该墓已经被一个临时搭建的房子围住,外面并不能看到什么。只有打道回府。这时儿子说,到汪山土库去。儿子是从外地回来过春节的,对南昌的事居然这么熟悉,不得不佩服现在年轻人的脑子灵光。去看看这个地方也不枉此行,心里也就欣然同意。于是两部车子旋即调转了方向向土库驶去。
土库离海昏侯还真是不远,一会儿就到了。
土库外面看不出什么,平淡、平凡。走进去才发现就像进入了一座迷宫。一个占地七万多平米的豪宅,里面阡陌纵横,犬牙相错。每一个结构,每一种装饰都极有讲究,富含寓意。每一幅雕刻、每一块匾额都有禅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是歌德说的。因为它保存着人类文明中那些最动人心魄的旋律;金字塔的永恒、古希腊廊柱的经典、古罗马穹顶的宏阔、巴洛克建筑的雍容,无不证明这个论断的无比正确。北京的故宫,从正阳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到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直到景山,沿长达七华里的中轴线展开,十几个院落纵横交错。有前奏、有渐强、有高潮、有收束,几百所殿宇高低错落,有主体、有陪衬、有烘托,雄伟壮观的空间序列俨然一组“巨大的交响乐”。
再往里走,三个红顶子的画像赫然摆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要认识的三个重要人物,因为土库的故事就是从他们身上开始的。三个红顶子分别为程矞采、程楙采、程焕采。他们当年科第高中,官至总督、巡抚,在晚清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叱咤着风云,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一门三督抚,五里六翰林”,这是历史的一笔记录,族人因此引以为耀。为了将这些荣耀变为一种意志,成为一种家风遗传下去,三个红顶子决定由他们出资来建造这样一个土库,通过严格的祖训家规来统一全族人的意志。这看起来有点残忍,但古人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土库人觉得有责任将老祖宗的东西传播发扬下去。继三个红顶子后,从这里又走出了4名进士,11名举人、遍布清朝各部各省官员100余名,受封为“总督”、“尚书”、“一品夫人”的有十几位。
参观时,发现一直在屋堂里忙着收拾什么的那个人有点像是这个家族的后人。于是上前和他搭话。问:这房子看起来这么恢弘霸气,享有“江南小朝廷”之美称,怎么取个名字叫土库呢?他笑着作答:因为它座落在“汪山”,又因鄱阳湖滨湖地区常把规模大的青砖斗式瓦房称为“土库”,自然就叫“汪山土库”啰。听了他的回答我也笑了。现在很多开发商给楼盘起名字喜欢讲噱头,似乎越牛叉越好,什么世界名人苑、丹枫白露、盛世经典、地中海阳光等等。而真正的豪宅却又叫土库,真是让人有点不可思议啊。那人又接着对我说,这房子的图纸出自一位设计过圆明园、北京故宫等宫廷建筑的设计师的后人雷氏之手。我说,我看过介绍了,说它糅合了皇家宫廷建筑、徽派建筑、苏州园林、赣南围屋和南北民居之精粹。他点点头。否则怎么会显得这样精巧、合理、大气呢,对吧?他又点点头。
虽说是一幢豪宅,却并不奢华。足迹所到之处,闻到的是阵阵书香。土库是没有绣楼的,唯一能满足的就是书,看得最多的也是书。土库的女孩要和男孩子一样,“幼承庭训,上私塾、读经史,工诗词。”她们中也有漂洋过海,也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成为一代女杰的。记得余秋雨先生在他的《风雨天一阁》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也有人说过,读书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土库当年的学子们一定也和照片上那些让我对土库留下最初印象的青年男女一样,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着期盼和憧憬。但他们更多的是把功课做到了实处。在土库,有供学子们读书用的“稻花香馆”、有鼓励后人勇于登攀的“望庐楼”、有官宦们回家以后自觉反省的“退思堂”;更有无处不在鼓励学子们奋发上进的楹联对联:“春风大地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万卷诗书教子弟文章报国,一言忠厚建功名道德传家”、“游宦一身存正气,归家两袖带清风”、“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醒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恃大体,思事事皆国计民生所关”,读起来真是让人荡气回肠呀。
自孔子以来,历史上就产生了一个独特的“士”阶层。这个阶层在中国延续了二千五百多年。“士”忠于道,追求君子、圣人人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士”阶层的存在、“士”精神的张扬,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文明古国先后覆灭,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这其中必然包含其他民族未曾拥有的坚强精神。当文天祥在过零丁洋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当于谦在鞑靼铁骑吟诵“粉身碎骨不怕死,留得清白在人间”时,他们的声音,他们跃动的精神已经跨过了时空,跨越了具体的时代。成为人类只要存在就不会过时的精神财富。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种中国的“脊梁精神”在汪山土库无处不在。程懋型是三个红顶子之一程焕采的第四代子孙,生性敦敏,读书一目十行。二十岁东渡日本,学成回国后在省里任电学教师,一时俊彦多游门下。他的才学得到高层的赏识,进入了仕途。职务不断地迁升。1945年刚过完五十岁生日,程懋型被调任粮食部参事。不久日本投降,江西省政府复归南昌,程懋型又荣膺新命,受任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这时的江西已经是元气大伤,民生颠沛,饥馑流亡。程懋型深以为忧,为谋一裕国苏民的方略常常是焦虑万分、寝食难安,以致常常咯血。此时内战开始,各地军需催缴公粮的命令又十分紧急,数字比以前还要加倍。程懋型总是因完不成征粮任务常常遭到上面的苛责。无奈之下,程懋型只有扶病亲征,督促各地田粮人员大力运购。可青黄不济时节,农民已生饥荒,此时向百姓征粮如何下得了手?程懋型进退维谷,忧愤交集。征粮任务没有完成,政府又广告职责给了他更大的担当。既不能强迫农民,自己又完不成任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以死殉职。他给妻子留下了一封长长的遗书交代了一些相关后事后,携随从一人,步行至吉安白鹭洲江畔,自沉殒命。终年五十一岁。程懋型的死令业界震惊,万民悲痛。省、市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四周挂满了挽联。“逝者此斯夫,己溺竟先天下溺;千秋有公论,官悲不及路人悲”是百姓对他最公允的评价。
土库里还有一副楹联重复镌刻在了好几个显眼的立柱上,这是林则徐撰写的。内容为“湖山意气归词苑,兄弟文章入选楼”。当年土库中的第一个红顶子程矞采和林则徐同榜录取,同成为朝廷的一品大官,因而成为好友、知己。后来徐又与第二个考上进士的程楙采同在翰林院中共事;再后来程矞采的胞弟程焕采考试时林则徐又是江西乡试的副主考官。徐与程氏三兄弟可谓有同学、同事、师生的情谊。林则徐十分钦佩程氏兄弟的学识、文采。在嘉庆庚辰(1820)程焕采中试二甲第53名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便亲临汪山土库祝贺。他在这里看到了巍峨的庐山和浩淼的鄱阳湖,感慨万千。特意索来笔墨为他们兄弟题写下了这副对联,成为他们兄弟仨和林则徐友情结交那段佳话的一个佐证。当我徜徉在这样的一座宅子里的时候,恍若走在了一个隔绝了一切浮躁的世外桃源里,只感觉一股清风扑面而来。
人们说,即便汪山土库被夷为平地,不复存在,在汪山这一垅土地上,仍有一座不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数百年来被汪山程氏发扬光大的家风。
这时由于天色已经向晚,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带着一些迷惑,一些疑问便匆匆离开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华夏文明几千年的绵延传播中,汪山土库的现象并非孤立存在。只是他们没有汪山土库走得这么远。在我们江西,最典型的有和汪山土库相隔不远的新建魯江村曹氏家族、有婺源坑头的潘氏家族和号称千古第一村的乐安流坑。这些老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村里出了个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在当地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给村子里带来了福利。人们在羡慕的同时也争相效仿,用现在的思路来说,就是一带一路。但大多到了近代便退出了历史舞台,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位于新建县的曹氏家族,在早于汪山土库一百多年的乾隆年间,出了一个和纪晓岚齐名的人物曹秀先。曹秀先宦海50年,和纪晓岚两人先后担任四库全书馆总裁。任礼部尚书,最终成为帝师。在曹秀先的影响下,小小的鲁江村、小小的曹氏家族(直至清末,也不足百户),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开始,直至清朝末年,出仕为官者竟然有一百余名,其中进士出身者36人,而且大多为两榜进士;举人出身者有三十余名,秀才一百七十余名,成为华夏奇观。嘉庆皇帝曾御封为“江南望族”。但到了近代就很难觅见这个家族的踪影了。现在,昔日的古村落已被夷为了平地。成了一个经济开发区。所剩古董只有原来曹秀先老宅门口的一对红石回头狮。其凄惨、凄凉之景令人潸然落泪。
婺源坑头的潘氏家族历史上曾经出了九个进士,明代进士潘潢曾先后在四个部当过尚书,相当于现在正部级啊,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因此村中有副对联:“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地方官吏只要一见这幅对联,武官下马,文官下轿。这个村至今还能看到有三十六座半桥。桥的来历是这样的,根据这里的风俗习惯,每出一个官就要建一座石桥,一共做了三十六座半桥。其中一座桥之所以称为半座桥,是因为有个官衔是一个商人花钱买的。当地人不买账了。认为买来的官不算数,最多只能算上半座桥,于是就有了三十六座半桥的说法。这也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反腐拒腐吧。如果走下拱桥,贴着水面向远处看去,桥桥相连,活像是龙的脊梁,龙头就在潘潢的故居。
号称“千古第一村”的古宅位于乐安县的流坑。也许是交通相对闭塞的原因,村里历代民居大多都保存了下来。这里最早的村民来自五代,一董姓家族因避乱迁入客居于此。自那一天起,他们就将这个地方当作了故乡,在这里繁衍生息,因此村里清一色姓董。宋朝的时候这里出了一个好玩的人叫董德元。董德元自幼读书勤奋,少时工诗,16岁考中秀才,20岁时参加乡试,获魁首。后来总是累试不第。于是作《柳梢青》词一阙:“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尘埃。直至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功名已是因循,最恼恨,张巡李巡。几个明年,几番好运,只是瞒人。”让人读起来颇为诙谐沉痛。绍兴十七年(1147)丁卯秋试时,已经51岁的董德元,进取之心已失,不想赴考。无奈诸考生强拉他同行,才勉强上路。途经临江(今江西樟树市内),地方太守彭合对他不以为然。并说“老榜官何足道!”用我们现在的话简单一点解释就是,你这个老是榜上无名的考场老油子,都多大年纪了还考什么功名呀!于是不给资助路费。谁知,董德元当年预荐时选中。第二年,即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科中进士,居第一。与理学名家朱熹同科。董德元中第之后,授左承事郎,任镇南军(今江西南昌市)节度判官。归家时,又路过临江。彭太守赶紧迎接,设宴招待。宴席上,董德元即赋诗一首:“黄牒初开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迓,便是从前老榜官。”让彭太守好生尴尬。后来,董德元为相时,捐弃旧怨,启用彭合为户部郎中。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