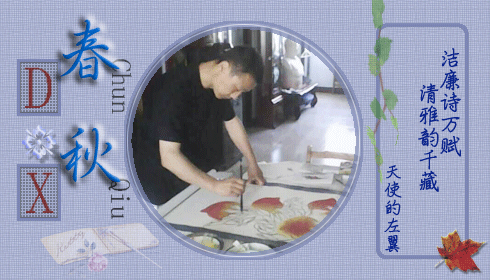【丁香花语】走失归来的孙其保(散文) ——一篇散文的后续之作
【丁香花语】走失归来的孙其保(散文) ——一篇散文的后续之作
![]() 五保、痴呆老人孙其保(小名碾子)在我家乡的养老院走失,当地政府立即组织人马沿着国道、省道“追寻”,并在本县网站发布“寻人启事”,但三天三夜过去了,却没见人影。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在省会郑州。我与孙其保是“发小”,当然关心他的失踪事件。三天后,当地政府调整“追寻”思路,派出大量认识孙其保的人,由乡政府做圆点,进行“辐射”式搜寻,最终在30华里外的本县“新里镇”的大街上找到了。
五保、痴呆老人孙其保(小名碾子)在我家乡的养老院走失,当地政府立即组织人马沿着国道、省道“追寻”,并在本县网站发布“寻人启事”,但三天三夜过去了,却没见人影。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在省会郑州。我与孙其保是“发小”,当然关心他的失踪事件。三天后,当地政府调整“追寻”思路,派出大量认识孙其保的人,由乡政府做圆点,进行“辐射”式搜寻,最终在30华里外的本县“新里镇”的大街上找到了。
孙其保老人为什么会穿过繁华的“马集镇”,来到偏远的“新里镇”?多数人,也可以说全部搜寻的人都不得而知。唯有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去那个不起眼的小镇。但我也是事后诸葛亮,所以,我写了一篇散文《出走新里镇》,试图追溯孙其保“出走新里镇”的源头。四十多年前,我曾经与孙其保一起去新里镇,用大米换红薯。那时,孙其保便是“智障人士”一个,他跟我一起“换大米”,完全是做苦力的,一切都是唯我的马首是瞻。为了躲避“市场管理”人员的缉拿,我们被一位奶着孩子的少妇掩护起来,中午,我们在少妇家里吃了一顿蒸红薯。这是孙其保平生第一次“坐桌”吃饭,少女给他剥红薯皮,热情有加。(详情请见我在本网的投稿《记忆深处》http://www.vsread.com/article-755907.html)
机会终于来了,1日15日,我二弟乔迁新居,我于14号赶往老家帮忙,晚上,我让女儿和外甥女去接碾子出来,但此时,敬老院已开过晚饭,孙其保也上床休息了。她们给他买了一些零食。据说,孙其保走失找回后,养老院对他管理很严,谁带他出去,必须签字画押并保证送他回来。
15号早上,二弟骑电摩将孙其保接出来,饭前,我和孙其保有短暂的交流,我叫了一声“碾子”,他对我笑笑,说:“白完了,白完了。”他发音模糊,似是而非,我问:“啥子白完了?”他说:“头毛,头毛。”我问:“你是说我头发全白了?”他说:“嗯嗯。”接下去,我问他为啥要到新里镇?他只是微笑而不答,问了三遍他才说:“蒸红芋。”我问:“你想吃蒸红芋?”他又只笑不答。我问:“你去新里还想见见那位给你吃蒸红芋的大姐?”他还是笑而不答。问不出结果,只好作罢。不过,我可以肯定,碾子出走新里镇,是奔着那顿蒸红薯而去的。
为了验证孙其保是否痴呆,我带他去了老宅,说起老宅,我与孙其保是真正的邻居,我想让他给我指出我们当年居住的地方。老宅距二弟所在的居民点约一公里,我们很快就到了。老宅确实老了,大约还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家。所以,过去逼仄的村户,现在宽敞多了。走近村口,就走进了一片寂然和空阔中。深长的村巷里,奔跑和游走着土狗和觅食的鸡群。一些乡村无聊的风鼓励着各种颜色的塑料袋滚来滚去。老年人在冬天里最喜欢亲近阳光,背风处,常有白头发的老翁和老婆在那里枯坐。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村边的树呢,都是落光了叶儿的 ,一律枝丫向天,在野风中作一些叹息。
这个村庄沉浮着我太多的往事。而最严重的就是贫困与饥饿。当初,我以悬梁刺股的韧性逃离了这个村庄,至今少说也有三十八年了。而碾子离开这个村庄去养老院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但孙其保似乎对老宅没有记忆了。转了几圈,就转到我们曾经一起当饲养员的“牛屋”遗址,这里只是废墟,三间饲养室早已倒塌,成了某些人的堆放垃圾之处。孙其保在废墟了站着,像寻找着当年的记忆。我记得我们四个人饲养二十多头牲口,组长是生产队长的二弟。每天夜晚,组长就把牲口吃剩下的黄豆秸装在背箕里,让大家轮流偷偷地背回家烧锅,但轮到孙其保时,他拒绝往家里背,这不是他有多么高尚,而是在他心里,没有“偷”这个概念。
我们俩正在转悠,有一位苍老的婆婆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说这不是某某吗?这位老人是前生产队长的夫人,我应叫她“大奶”,我毕恭毕敬地答话:“大奶,是我。”她啧啧地叹息说:“头毛都白完了。”我说:“是白完了。”然后,她又喊碾子,问碾子为啥跑“新里镇”去了?碾子不答,我说:“可能那里有他亲戚吧?” 大奶说:“没听说他有亲戚在哪呀!”又说:“碾子比俺还享福呢!天天吃现成的,俺八十多了,还不拾闲哩!”我说:“您八十多了,身体还这么好!”大奶说:“哪呢?眼跟耳朵都不好了,牙也掉一大半了。腰还疼!”这时,一位说普通话的年轻人过来,问:“这是孙其保吧?”大奶说:“啥保呀?他叫碾子,你不认识他了?”年轻人说:“他是孙其保,小名碾子。”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老头写的文章《出走新里镇》,所以我才知道他的大名。我说:“不瞒你说,文章是我写的。”年轻人很惊讶地望着我说:“您是我们村庄的人?”大奶插话说:“你还跟他叫爷的呢!”
年轻人很兴奋,说他前天才从上海打工回来,他在上海经常上网看家乡的事,没想到我们庄上出了个作家!我说:“啥作家?只是爱好玩文字而已。”年轻人要留我吃饭,我婉言谢绝,带着碾子告别我的“大奶”和“孙子”,走出村庄。
村庄凋敝了,看不见绅士一样慢慢行走的猪了,只有两条狗在冬天的阳光下追逐嘻戏。鸡还有不少,公鸡追赶母鸡的姿态没有进化,它们在村庄到处蓬勃着生机。
离开村庄,我的双眼有点模糊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再回到生我养我的这个小村庄。而孙其保则袖着手,一副茫然的样子。我想不出他对这个村庄怀有什么样的情感和记忆。
开饭时,我们一桌都是自家人,我给孙其保安排一个座,喊他上桌吃饭,他仍是那年吃蒸红薯的样子,光笑不动,连喊三遍,他都不来,我只好把他拉上桌。吃菜时,他只夹面前那一碗的,不觊觎别碗的幽香和美味。我就每碗挖一勺子,组成一碗杂烩,他就吃这碗杂烩,看样子,他比那年在少妇家里吃蒸红薯时更显得拘谨了。
应该说,孙其保确实是幸运的,一个孤寡、智障老人,能有今天的生活条件,连上帝也无话可说了。据说,他的父母离世的时候,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了。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告慰孙其保的父母了,你们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