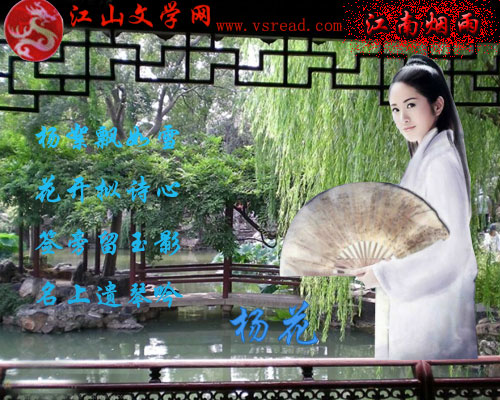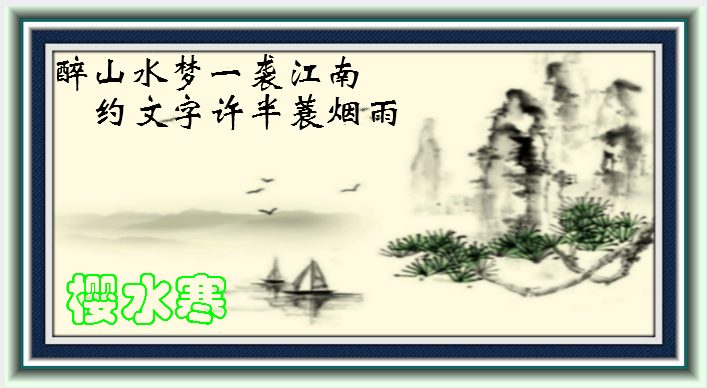【江南】保国寺寻幽记(散文)
【江南】保国寺寻幽记(散文)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如此清晰地听到木质沉香的声音,也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的心清凉得仿佛盛夏的一树绿荫。除了那座古寺。
古寺名叫保国寺,位于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洪塘镇,既有“深山藏古寺”的幽静,又有“院中观海曙”的开阔。令人惊奇的是,保国寺内连一座供奉的佛像也无,它之所以闻名于世,自然不是因为其宗教文化,信徒虔诚,而是其精美绝伦,举世无双的木质建筑。保国寺并不仅是一座寺庙,它更像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静坐在光阴深处,等待着我们来访,听它讲述一段与木质建筑相关的故事。
初入景区门,便有石刻迎面而来:江南古刹,文物精华,法式例证,建史奇葩。十六个大字,盛赞了这座千年古寺在建筑史上的地位。木质结构的事物本就容易腐朽,这座寺,却硬生生留下了“鸟不栖,虫不入,蜘蛛不结网,梁上无灰尘”的千古之谜,怎不令人生发出一探究竟的好奇?
继续行,被道路两旁高耸的香樟树惊艳了眼眸。任何一种颜色堆积,都能给人一种惊艳之感,其中又以绿色为最,固有积翠叠锦之说。当满眼都是翠绿、浅绿、深绿、暗绿、明绿等层层叠叠的绿时,仿佛有青绿色的诗句,爬过我的眉眼,整个人都是澄澈清凉的。那种感觉,仿佛于世俗中突然了悟,原来所有的繁荣忙碌都变得无关紧要,此刻唯有宁静,唯有清心,想必这便是所谓忘机。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我不知道眼前的小路到底是通向一间禅房,还是一首诗,只是随意走着。此时已过半晌,清晨的露珠早已从叶尖滚落,不知道有没有僧人在千年前,采了林间露水煎茶。不算炙热的光线,透过树木的枝叶洒落下来,斑驳的光影流淌在青石板上,每一脚踩下去,仿佛都会在碎金流成的河里,踏出波纹来。
行过刻着“同登解脱门”的墙壁,再绕过那株枝叶遮天的古树,才真正到达保国寺的山门。一副“山门寂寂惟留风月,觉路迢迢不到尘嚣”的对联,道尽古寺意趣,与周遭幽静清雅的环境融为一体。只是不知山门留过多少次的风与月,又有多少人在尘嚣中凝望着迢迢觉路。门前有经幢两座,为唐时所立,其一保存完好,另一座却在岁月中残破,时光游走的痕迹,可见一二。
初入寺门,便是净土池。据寺志载:该池长四丈八尺,宽二丈二尺,深丈许,种四色莲花,水量旱涝不减,是为一大奇观。周围游人都在看着池中游鱼嬉戏,而我却只为池壁上题着的“一碧涵空”四个字所呈现的意境所倾倒。干干净净的碧水映照着天空,日光和星月都曾在碧水里涤洗,或者也有僧人临水自照,涤荡过一颗佛心。多么美好的画面,多么美好的词!
在庭院中,有汉代遗迹骠骑井。据传,保国寺的前身为灵山寺,东汉世祖时,骠骑将军张意与其子中书郎张齐芳隐居在灵山,后舍家建寺,因其位于灵山之麓,遂名灵山寺。世事多么无常啊,曾经战场杀人的大将军,最终放下屠刀,建起了一座佛寺,从此将尘世的血腥名利尽数抛了,潜心侍佛,“淡泊资禅味,清凉养道心”,只做灵山一隐士。只是后来,唐武宗灭佛,这座汉时的灵山寺,毁于一旦。直到唐僖宗时,才在可恭和尚的努力下重建,并得赐名“保国寺”,后又被毁弃,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木质大殿则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所建造。历史兴衰流转,于一座寺中可见一斑。
保国寺最大的名声,便是来源于它的大雄宝殿了。其独特的木质结构,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水平,有着极高的历史意义。说起来它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甚至是一种“偶然”的缘法。1954年暑假,由戚徳耀、窦学智和方长源三位学者组成的小组对杭州、绍兴、宁波一带的古建筑及民居进行调查,却在一次偶然中,得知宁波鞍山乡洪塘有一座唐代的无粱殿。这一消息让三位年轻人无比欣喜,之后经历许多周折,才走进这座寺庙,最终揭开了保国寺的神秘面纱,为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的指引才让这座古寺最终展现在人们眼前,但是我愿意相信,那些沉寂了千年的木头,用它们独特的性灵指引着这三个年轻人,来一次铭刻史册的邂逅。
我不是建筑学家,走在保国寺,读不懂那些建筑结构的精妙,但是站在这座古寺中,看着那些精美的图案,嗅着穿堂风隔着千年光阴吹来的木质的香,我的心宁静到了极点,清凉到了极点,也震撼到了极点。闭上眼,仿佛灵魂可以穿越到千年前,看到在德贤法师的带领下,一根根木头被搭建起来,每一块木头,都被充分利用,所有的智慧都被凝结,最终才有了这座“甚奇,为四明诸刹之冠”的保国寺。
保国寺虽然在建筑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却终究不为太多业外人所知。与游客往来不绝的灵隐寺、少林寺等名寺古刹相较,保国寺更像是口袋里塞满了夜明珠,却只在山间玩耍的少女,干净,纯粹,谨守着禅寂的意趣。于我而言,保国寺最大的妙处便是这种禅寂的氛围,这种寂静,让人觉得身心都是空的,而精神却又是满的,这种满有着佛寺特有的慈悲,从红尘深处将我打捞出来,暂归净土。目光掠过大殿、藏经阁、云居楼、厢房等诸多古迹遗址,看飞檐翘角与诸多古老的树木相对安详,听着千年不变的风声缓慢划过。也有小猫,从檐角墙头慵懒走过,阳光碎碎地洒下来,却被墙壁一分为二,光与影,明与暗,仿佛两个世界。
我最喜欢的,却是钟楼和鼓楼。走上去,钟已经不允许敲了,从此声哑,而鼓成为了人们许愿的一种方式,心里的愿望随着鼓声的厚重,渐响渐远,不去管佛究竟能否听到,自己已经是尘心顿洗,俗念都捐。我不知道,在万籁俱寂的光阴里,有没有突然响起一串钟鼓声,接着是不绝于耳的禅唱,盛大而幽寂。晨钟暮鼓咽管弦,想必那是最动人的一种声音,是天地之间的鸣奏。“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这种境界,只能躲进古诗词中去找寻了。
离开保国寺的时候,已是午后。走在下山的道路上,安静得只有丝丝缕缕的风拂过耳畔,我却仿佛听到了木质沉香的声音,保国寺,这座千年的木质古寺,用悠远的目光和岁月沉淀的香遥送我们下山,道路两旁的树,枝叶轻摇,犹如挥手告别。我在心里默默想着,保国寺,你等我,等我下次从红尘深处逃离,再来寻你续一场旧约。彼时,你赠我山间的风与月,赠我青翠的绿和晶莹的露珠,而我,赠你一个清凉纯净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