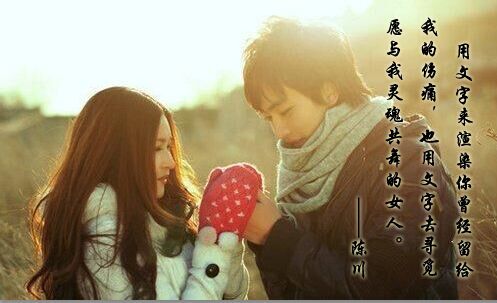【百味】永恒的情人杜拉斯(书评)
【百味】永恒的情人杜拉斯(书评)
1914年,杜拉斯出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后来的越南西贡/胡志明市)。父亲是数学教师,母亲是当地小学的教师。她有两个哥哥。15岁半那年,她在那里遇见一个中国男人,他成为了她的第一个情人。
五十多年后,杜拉斯将这段深埋在心中的往事,写下来,视为《情人》。在中国,《情人》最受欢迎和好评的是王道乾的译本。翻开《情人》,一开头,我们就深深迷醉其中了: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侯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的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就是杜拉斯。她用独属于她的深沉的感情、细腻的心思、妖娆的文笔,一下子就捕捉了你。你只能跟着她,爱她,别无他法。
杜拉斯写,写在码头的初次相遇,写那个羸弱的中国少爷,写母亲、可怕的大哥、可怜的二哥,写他们夏天不曾停歇的做爱,写贫穷、自尊。她写了一切,我们也看到了一切。她像她活着那样去写。不写,她可能早就死了。
杜拉斯后来写:身处于一个洞穴之中,身处于一个洞穴之底,身处于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
所以,在杜拉斯那样激烈、叛逆的生活之外,其实是写作拯救了她。她的孤独谁人懂呢?只有写下来。写下来,就逝去了。懂不懂已经无所谓了。
然而回忆一直都在。那是情窦初开、初知情欲的年纪,那是15岁半的杜拉斯。那时,她身上穿着磨损得几乎快透明了的真丝的衣衫,穿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高跟鞋。头上戴的帽子,是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就是那样一个形象,在一个没有四季之分,一直炎热的国土上,她遇见了那个风度翩翩的中国情人。
他向她打招呼,用他的车送她回学校。后来又去学校接她,把她带到他的房间里。那是城内南部市区的一个单间房间。在那个房间里,他要了她,或者说,她要了他。
“他一面哭,一面做着那件事。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
他们就这样痛苦着,也就这样快乐着。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
后来他们又要了许多。两个人都为着一些东西,在要着,在爱着。那是不堪贫穷,不堪孤独,不堪单调。彼此需要,只能如此。
然而不能在一起,两人之间有太多不一样,太多隔阂。都明白,这样的爱是无望的。而且,到底是不是爱呢?
到了最后,她要离开西贡了。她在船上,看着他那黑色长长大大的汽车停在那里,车前站着穿白制服的司机。车子离法国邮船公司专用停车场稍远一点,孤零零地停在那里。车子的那些特征她是熟知的。他一向坐在后面,他那模样依稀可见,一动不动,沮丧颓唐。
船开走了,直到她再也看不到他。那辆车也看不到了。
后来,黑夜开始的时候,甲板上有人奏起了肖邦圆舞曲。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听着,后来,她哭了。她在想,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远了。一切,都远了。
杜拉斯如此把少女往事写了出来。那样年轻,又那样迷离,那样无奈,又那样世俗。她怀着真诚在写,我们怀着真诚在读,我们都为之叹息,为之伤怀。
正是这本《情人》,让杜拉斯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使她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语作家。一九九一年,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又成功地把这部名噪一时的自传体小说搬上银幕,又使得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女作家之一。也正是《情人》这部电影,才使得中国读者熟悉她。
我们或许应该幸运,因为《情人》是杜拉斯掩埋珍藏了五十多年的感情。杜拉斯没有在她十几岁二十几岁渴望成为作家的时候把她写出来,没有在她中年已经出了书之后写出来,而是一直到了七十岁。那时候,回忆起来的,都是最珍贵的,写出来的,都是最深情的。
那时候,千山暮雪,都是诗。
而我们,作为读者,或多或少地,都醉在了她的回忆里,醉在了她的文字里。她是那个,也只能是那个,我们永恒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