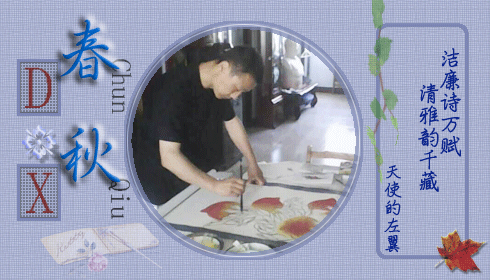【丁香青春】老贫协家的高楼(散文) ——----南垣村之一
【丁香青春】老贫协家的高楼(散文) ——----南垣村之一
![]() 中秋节过后,一场风,一场雨,树叶黄了,落了。突然脊背感到飕飕的一股凉气,找来秋衣秋裤,厚衣服穿上。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想起孔乙己那件“几十年没洗也没补的长棉袍”,想起闺土提着干豆角瑟瑟索索的身影,想起祥林嫂泡的通红的手与劫走她的乌篷船。鲁迅笔下的众多小人物一起涌进脑海。鲁迅不愧是大师,他刻划的人物出神入化,镌刻于脑海,几十年来,每每想起,都如在眼前……
中秋节过后,一场风,一场雨,树叶黄了,落了。突然脊背感到飕飕的一股凉气,找来秋衣秋裤,厚衣服穿上。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想起孔乙己那件“几十年没洗也没补的长棉袍”,想起闺土提着干豆角瑟瑟索索的身影,想起祥林嫂泡的通红的手与劫走她的乌篷船。鲁迅笔下的众多小人物一起涌进脑海。鲁迅不愧是大师,他刻划的人物出神入化,镌刻于脑海,几十年来,每每想起,都如在眼前……
瑟瑟秋风中,我又想起中秋节回故乡,又想起邻居“老贫协”。解放前,他家三代贫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因家寒,四十多岁娶同村一寡妇为妻,还带来一闺女。第二年,妻子生下一儿子。老贫协老来得子,喜得合不拢嘴,风水先生为其取名石柱,寓意儿子长得结实,顶起董家一片天。
我们每天上学时都路过他家门口,高高的台阶,院子里有一幢威风的三层楼,像乔家大院那样的古建筑。那会儿,我们一群不懂事的小青年,担任起宣传毛泽东思想,背毛主席语录,唱红色歌曲的神圣使命。每天晚饭后都会登上这幢三层楼顶,或演出,或朗诵,或唱歌,这里是全村的制高点,高音喇叭声可以传遍全村。
我一直纳闷的是,高楼空着,并不住人,总是闲置着,而他们一家四口却挤在那间低矮、破旧、黑暗的南房里。或许是老贫协住惯了南房,住高楼不习惯?或许是怕老东家回来讨要,住的不踏实?问过大人们,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年中秋回董庄,看到村里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好多人家都盖起了新房,一排排青砖平房,整齐划一,门楼上有“紫气东来,万事如意,耕读传家”等字样。原来的土路变成柏油路,邻家大伯说:“村村通柏油路了,下雨也照样骑车子。”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家家粮食满囤,新衣满柜,不少人家大彩电,皮沙发,安上鍋炉,享用上了暖气,乡亲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
隔壁侯家,儿子因贪玩摔坏一条腿,多年没娶到媳妇。侯大伯老夫妻为儿子的婚事求过神,拜过佛,可怜天下父母心,二老临终没有见到儿媳妇。人们说起这件事,无不摇头叹息。
晚饭后,在老窑里,叔叔让婶婶泡了一壶酽酽的大叶茶,不一会儿孟家伯、孙家叔、曹家哥围坐了一大圈。各自谈着今年的收成,七嘴八舌,好不热闹。
“今年棒子长的好,籽粒饱满,压称,昨天有收棒子的上门收购,俺家几亩地的棒子,愣是称了两千多斤。价格也好,每斤1块3毛,三千多块钱呢!”孙叔得意得狠吸一口旱烟,在厚实的布鞋底上叭叭的磕着铜烟锅。
“老孙头,三千多块看把你美的,你们猜猜我种的笋见了多少钱?嘻嘻。”吴家大哥眯着一双小眼情,看着大伙儿,慢吞吞的抿一口茶,摸着光光的下巴等着谜底。
“五千?”“八千?”“一万?”人们眼晴都齐刷刷转向吴家大哥。大哥摇一摇头,抿着嘴笑。“不会上两万吧?”老孙头眨巴眨巴眼晴疑惑地问。
“让你种笋,你不听劝,非要种棒子,说笋费事不好出手,这不人家一卡车都拉走了。三亩地见钱两万块,哈哈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哪。”
老孙头一脸懊悔,拿起铜烟锅要打吴大哥:“我还长你一辈呢,还老人言,让你美。”大伙急忙拦住。
这时隔壁侯家院子里响起鞭炮声,大伙好奇,一块涌向候家院。一个十多岁的英俊男孩站在大门口放鞭炮,当院桌上放个大彩电,正播着电视剧,电视机前两排凳子,有点儿当年露天影院的样子。我忙问婶婶,这小孩儿是谁家孩子?“那是小蛋的儿子啊。”“小蛋不是残疾了吗?不是没娶到媳妇儿吗?”连珠炮一样的问题从嘴边往出嘣。
“老黄历了,小蛋可出息了,你看这房子多气派。他装了假肢,骑个电驴子到处揽生意,收二手汽车,整修后再卖出去,挣大钱了。”
我多年在外,根本不知道小蛋儿娶妻生子,发家致富的事儿,候家大伯大娘九泉有灵也该笑出声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漫步在董庄学校的柏油路上,那个给我启蒙的校园,那一片我流过汗、流过泪的热土,每次回村都必定看看她。路过老贫协家门口,那幢记忆中的高楼变矮了,变破了,还剩一层?门口蹲着一位瘦弱的男子,灰头土脸,穿着单薄的衣服,秋风瑟瑟中,对着我嘿嘿地笑。“您是?”石柱啊,我惊讶地张大了嘴。
老贫协的后代石柱,我记忆中的那个虽瘦弱但活泼的石柱怎么成了这个形象哪。我急忙问他近况。他回答说,爸妈走了,姐也嫁到外村去了,父亲在世时为生计,卖了一层楼。爸妈走后,石柱孤身一人,为了生计,又卖掉一层。
“为了生计?”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哦,老贫协的口头禅,那是忆苦会上的话“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为了生计,爹挑着担子,逃难来到董庄村,为了生计,又给曹家当长工。”老贫协的泪吧嗒吧嗒地掉,群众也哭成一片,有人喊口号“打倒反动地主!打倒xxx”的声音震耳欲聋。那万恶的旧社会,逼得“老贫协”一家走投无路,弃乡背井,来到董庄村,给地主扛长工受剥削,光棍打了多少年。
东方红,太阳升,盼来救星毛泽东。政府给“老贫协”分了全村最高的楼房,最肥的田地,当了贫协主席,娶妻生子,共产党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
现如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勤劳致富的标语鲜红光亮,家家盖新房,奔小康,老贫协的后代石柱,怎么还是为了生计卖房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去年中秋回董庄,看到“老贫协”家的楼成了平地,一打听才知道,石柱卖完了最后一层楼,还是“为了生计”。
今年中秋回董庄,在“老贫协”家的楼房的地基上,盖起一个超市,商品琳琅满目,进进出出的人还不少,这是谁开的超市?答案是,曹家的曾孙买下了这块地基开了超市,唉!历史真会开玩笑。石柱,卖完房产,住进集体遗留下的库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