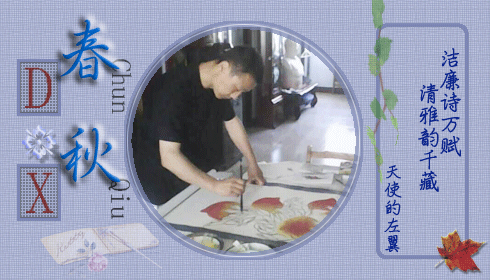【丁香青春】让我们的村庄留下痕迹(散文)
【丁香青春】让我们的村庄留下痕迹(散文)
![]() 人生的道路很长,沿途的风景令人欣慰,更令人流连忘返。有的风景一掠而过却令人伤神纠结,村庄里的乡情,是人生一道最美的遇见,时时念起,让人倍感亲切,更有一份挥之不去的村庄情结。
人生的道路很长,沿途的风景令人欣慰,更令人流连忘返。有的风景一掠而过却令人伤神纠结,村庄里的乡情,是人生一道最美的遇见,时时念起,让人倍感亲切,更有一份挥之不去的村庄情结。
我出生的村庄在渭北旱原上,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她不像国内的一线二线大都市那么很有名气,也不像省城西安,人人都知道它是十三朝古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居住的村庄,在中国地图上是很难找到的。我们的村子位于咸阳市彬县的南原水口镇西南,这里沟壑纵横,原面很窄,世代以农业为主,祖辈们以传统的农业耕种为本。
虽然说大车村,人都称她是“南原的白菜心,能成人在大车村”。只能说明大车在南原的位置好点,二是大车村的村风好、人能干。村东和村西都是岭,东边是奓红岭,西边是红崖岭,土地比较保墒,土地也比较肥沃,旱闹保收。到底这能成人是谁呢?还有待考究。大车村也确实历史悠久,村子里有龙头岭,有古城,有堡子,有庙宇,有文昌楼。具体这些建筑,是何年何月修建拆除,古城和堡子是何朝何代,还有待查证考究。仅从村碑文上看,大车村秦朝以前就有村落,当时不叫村,叫大车路,就是大车村的牛车、马车,比其他村子车辙宽,秦朝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从此,大车路变成了当今的大车村。但是,在这里没有出过历史名人,也没有太大的历史事件,因此她很不起眼,很不为常人注意,实在是太普通了。
可她再普通,再不起眼,也是我的出生地,也是生我养我的土壤,我和我的父辈、还有我的子女们都成长在这里,黄天厚土的养育之恩,今生难以忘怀。
我们小时候,我们大车村跟着全国已经进入公社化时代,那个时候的村称为大队,全大队六个生产队,现在的一七组俗名韩家店为一队,二组俗名堡子为二队,如今的三八组俗名新庄子又称文昌楼店是三队,四组俗名庄合为四队,五组俗名韩家沟圈为五队,六组俗名旧堡子为六队。七十年代的大车村有一千多口人,到了九十年代差不多也就是不到两千口人。虽然,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时候,村子里已经姓氏复杂,人口发展到了空前庞大,但是整个村子民俗民风淳朴,人们勤劳勇敢。祖辈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辛勤的劳动,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田园生活。村子里有学校、有医疗站、有磨坊,各个生产队有自己的饲养室、储备粮库、保管室和队部等,大队部就在二组和六组,也就是堡子和旧堡子村口交界之处,大队部也曾经建了村上的储备粮库,这里是大车的村中心。多少村上的活动、演出、会议都在这里或者在大车完小聚集举行,加上村上还有一个大车粮站,我们的村子当年其实人气也很旺盛。
因为那时候,孩子念书小学都在村上或者乡镇,成年人们几乎都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耕作,外出务工的很少几乎没有,除非是走亲戚,或者考上大学或者在外工作,他们才很少回家。所以,村上家家户户没有不知道的,乡村邻家之间,谁家发生芝麻大点事,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真可谓当年那句话:“有千年的邻家,没有千年的亲戚。”当然这些林林总总的美好回忆,都离不开新中国的成立,离不开新政府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沐浴。
由于村子很大,我对其他小组确实不是很熟悉,过去就听村上爷爷辈有人讲过,我们大车村本户都是黄姓,黄姓主要分布在二、三、四、六组、其他姓氏都是明末清初的移民户。我们小队是三队,也就是现在的三组和八组,位置在大车村的最西边紧邻底店村,和西北方向的王堡村庄合硷紧邻,北边和永平乡隔沟相望,南边和屯里村隔沟相望,大车东边奓红村紧邻。过去村名新庄子也叫文昌楼店。新庄子村名,据老人说来源于我家新修的庄基,解放后分家时分给大伯三伯居住,我家、二伯、四伯住老庄基。两千零五年以后,新庄子和村上的所有庄基窑洞一样,人们都盖了新瓦房,居住在沿公路两边,门前的百年大槐树和皂角树被砍伐了,窑洞被已经被移为平地,由村上组织,全部平出的土地栽上了核桃树,核桃园满村子到了夏天,一片郁郁葱葱,核桃树都已经挂果,每当白露过后摘核桃吃核桃时候,不免让人想起庄子上的老屋和已经变成回忆的美好童年。
文昌楼店村名,是来自于清代村口建筑的那座文昌帝庙,估计是祖爷辈们修建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仅仅是个传说,等我有了记忆,文昌楼遗址只是一片瓦砾,就在八叔的自留地,和三角坟墓紧邻。文昌楼遗址当年有两米高土地基,地基差不多有一亩三分地大小,地基东头有一颗高大的洋槐树,生产队时候文昌楼遗址附近还有很多老胡杨树。树上有很多喜鹊窝。1990年修农田水利,文昌楼遗址被平地时推成平地,仅仅保留一个小山包一直至今。虽然文昌楼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文昌楼确实是父亲辈的美好童年的回忆,是祖辈先人对后辈村子子民的殷切希望。
为什么说文昌楼是祖辈先人对后辈村子子民的殷切希望?这当然要从文昌帝说起。据文字资料记载,原文如下:“文昌帝“文昌帝君”,有天神与人神两种不同的说法:文昌两字既为星名,又为神名,也就是中国民间惯称文昌星、文星神。文昌帝君又称为梓潼、文昌帝、济顺王、英显王、梓潼夫子、梓潼帝君、雷应帝君。有关文昌星的说法,《史记‧天官书》所载:“斗魁戴匡六星,日文昌星,一日上将,二日次将,三日贵相,四日司命,五日司中,六日司禄。”《星经》中载:“文昌六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其六星各有名。”文昌六星为上将(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命(主灾咎)、司中(主右理)、司禄(赏功进士),各有专司,掌管天下文运禄籍,所以自古以来就受到士人学子的崇拜。文昌帝君,一般认为他是主管考试、命运,及助佑读书撰文之神,是读书文人、求科名者所最尊奉的神祗。其受中国民间的奉祀,从周朝以来,历代都相沿制订礼法,列入祀典。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文昌星尤为文人学子顶礼膜拜,有谓文昌“职司文武爵禄科举之本。”因文昌星和梓潼帝君同被道教尊为主管功名利禄之神,所以二神逐渐合而为一。文昌星简称文星,或称文曲星,系星宿中主文运者,如杜甫诗:“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又《东观奏》:“初日官奏文昌星暗,科场当有事。”由此观之,学子应与文星有关。到了明朝景泰年间,景宗皇帝在北京新建一座庙宇,每年二月初三,遣人举行盛大的祭典。清朝年间,更加崇奉此神,嘉庆六年,仁宗皇帝也勒命礼部,把此神编入祀典。”由此不难而知,祖先修建此庙的用意,确实可谓用心良苦,祖先们就是期望我们小村人声鼎沸,人才辈出吗。
我们文昌楼点村的形状近乎是一个圆型,马槽沟南北向横在中间,从马槽沟沟顶端,改革开放后承包到户政策分成三组和八组,除过本户黄姓,几乎都是移民来的李姓人家,李姓分为三大户,基本都来自于本县水口镇西留村,至于西留村李姓的来源,确实到如今无可据考。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山西大槐树移民而来,一说甘肃陇西李家,不过据史料记载,甘肃陇西李姓也好像是移民而来。当然这些都有待考证。马槽沟水源注入黄涧河,黄涧河注入泾河,经河注入黄河,源远流长向东悠然而去,经久不息。我们小的时候,也就是七八十年代,村子里也就四五百口人,记得父辈们在一起劳动,一片土地不论是上肥料还是收割庄稼,人多力量大,也就是半晌的功夫,生产队的小麦垛子在场合里一排排,男女老少,有说有笑,劳动中欢歌笑语,耳音不衰。一百多年前,我们在村子里是客居,一百多年后我们成了村子的主人。我们从父辈手中接过了劳动的镢头、铁锨、锄头,接过了土地,在劳动的过程中,大家结成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血缘关系,我们成了亲戚,成了邻家,好一个美好的大家庭啊。
那时候我们还很小,在村子里逢人就称呼祖爷、老爷、爷爷、叔叔,总一直跟着父辈后边问父亲,为什么我的辈份这么小?到如今再回到村里,父辈们已经屈指可数,长辈们都已经去了,自己的称呼也随之已经变了,如今逢人大多数都是兄弟、侄子、孙子,自己能称呼长辈的却再也不见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流年轮回的更替,时代变了加上移民搬迁好政策,青年人进城务工了,他们在城里开始上班、工作、生活,有条件的人家,孩子也随着进城念书了,村子里仅剩下了老弱病残,留守妇女和儿童。别说村子里已经没有了窑洞的影子,就是修建好不到一二十年的平房,也是人去楼空,细数村子里的人家,门户开着的就那么几家,门户已经全权交给了铁将军把守。
按理说,人们的生活富裕了,年轻人进城了,耕种全部机械化了,确实是件大好事,我们农村人乡下人不就盼着这一天吗?可是我就是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每一次回家,心里不免总有那么一点点悲凉和忧愁。
分分合合,聚聚散散。虽然说聚在一起经常为地畔吵吵闹闹,经常会闹些小小的别扭,可如今真正要说走散,那每一张亲切的面孔确实令人觉得有点不舍。一百多年后,我们又一次走散了,村子里每一户将要根据自己的不同条件分布各大中小城市,在那里去寻找自己的未来和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么,我过去的邻家,过去的乡邻梓里,你有没有想过,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在村庄这块曾经养育我们的肥沃的土地上,留下一点村庄的痕迹,让孩子们有一点点乡恋之情。
让我们的村庄留下痕迹,留下深刻的记忆。几十年以后相逢的你,是否还能想起我们的村庄,是否还能想起我们深埋地下,久眠黄土之下曾经受苦受难的祖先?
你是否还认识村子里的每一位,你知道你应该怎么称呼吗?
初稿于2017年11月13日青海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