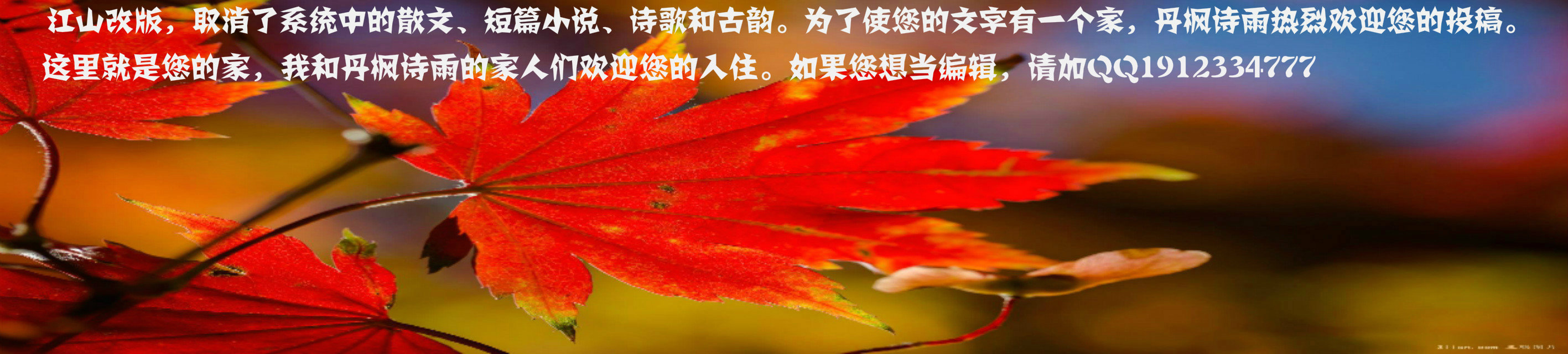【山水】犁(国粹·散文)
【山水】犁(国粹·散文)
![]()
一、初见木犁
六岁那年,在外公家,第一次遇见它,只觉得神奇。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怎样聪明的人才能设计出的?它会有怎样神奇的故事呢?
它弯弯的“脊梁”,好像大象的鼻子,在“鼻尖”钉着一个铁环,被磨的锃亮。底座是一块约摸长四十,宽十五,高十厘米的方木条,中间用的是两块木板交叉成十字形的支架,作为连接肢体的躯干,在木条底座的一端斜向上装着一根木质犁臂。不知是风雨的侵蚀,还是大地的腐蚀;是岁月的刻画,还是扶犁人的不爱惜,那底座早已褪去原本它该有的颜色,好在镶嵌在底座前端的尖头三角铲没有太大的变化。沾满缝隙的泥土是为了给它抚平岁月留下的创伤,无奈也在为它惋惜。
那时候,外公才五十出头,胡子拉碴,黝黑的皮肤告诉我,他与土地的亲昵程度。在我印象中,他的个头不高,算得上矮小了,但这并不影响他劳作的本领。或许在乡下,“老人”这个词就该赠给那些七十岁以上步履蹒跚的人们,因为五六十岁的人都是不服老的,他们仍然还在劳作,上山下地,砍柴放牛,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我的外公,就在其中。不论刮风下雨,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村西口的牛栏里把他的牛孩子放出来。他曾说过,牛也是他的孩子,他说你要对它好点,干活的时候它就会卖力些,要是照顾得不周到,它干活的时候,就该偷懒了。我想,牛,也是通情达理的吧!
这里是大山深处,是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小山村——鹅眉畈。这里的山贴着水,水缠着山,头顶空出一小片天,罩着沿河两岸为数不多的泥瓦房。等到初春时节,农人们开始新一年的劳作,你会看见,在山脚下一环绕着一环,一层挨着一层的田间,随处可见着人与牛与犁的组合。人右手牵牛,牛低头拉犁,人又在犁后面用左手扶着犁臂,这是一个奇妙的循环组合。人得跟着牛的步子,扶着犁,一步一步,走在待翻新的田野,一点一点,一圈一圈走完。牵引与摩擦,画下他们走过的路径,好像岁月的年轮,收集着他们的汗水,记录着山里人们的故事,年复一年,不曾落下。
大概需要五到十天,整个村子的荒地都会长一岁,披上一层泥土色的新衣,沐浴在农人们从上游引来的水里。他们躺在水中吐着气泡,似乎在欢呼庆祝着什么,又好像是在谈论春的故事。当水将所有的稻田都浸洗了一遍,又回到属于它的河里,翻腾拍打,欢快高歌,赞颂人们的智慧。顺流而下,两岸的芦苇长势甚好,青绿的新叶都很脆嫩,是牛孩子最喜的食物。早些时日,外公砍了几捆回家,就堆放在廊前,还没来得及搬去牛栏给他的牛孩子,我便偷偷的抽出一根,替他的孩子们尝过了,嚼在嘴里,渗出微微泛甜的汁液,弥漫着青涩的气息。我还来不及慢慢品位,外公看见了,极快跑出来抢走我手中的芦苇条放回堆里,还骂我坏孩子,乱吃东西。那时我还小,不懂事,还以为外公更疼他的牛孩子多些,不够疼我,所以,我哭了。
我哭着跑到河边,因为外婆在那,我想外婆肯定会疼我。外婆见我哭着跑来,连忙放下手里的刷子,过来牵着我手,问我怎么了。我就告诉外婆说,外公不疼我了,说我是坏孩子,骂我还抢走我吃的东西,拿去给他的牛孩子。外婆笑着跟我说:“好、好、好,不哭了,你在这先玩着,等下外婆回去帮你骂你外公去,外婆拿东西给你吃啊!乖!”外婆又蹲回河边,在洗着什么,出去好奇,我也跟过去了。原来她在洗犁,看见了犁,我的心情心情瞬间就好了,我问外婆为什么要把缝隙里的泥土刷掉,留着多好。她说,犁,每年用过之后都要洗干净了,拿出去晾干,不能晒,得留点水气,这样放起来,既不会烂也不容易开裂。那时我还不明白外婆话里的含义。除了犁我还看见两样东西,之前注意力都在犁身上,没怎么注意但这两样东西。直到后来听我父亲提起,我才知道,它们一个叫做牛轭,是挂在牛脖子上的,一个叫做牛杠,是挂在犁鼻尖铁环上的,两者用两根长铁链连着,就组成了牛拉犁的连接装置。
后来我就回自己家住了,以至于再也没见过外公家的犁,因为外公累了,睡下了,永远的沉睡在武夷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我的两个舅舅不会犁地,自然而然地,那犁也就传不下来了,听外婆说,早被卸来给灶王爷取暖用了。
我知道,外公带着木犁走了,但木犁和外公写在田野的故事还在,保存在土里,人们随时可以翻阅,即便那个山村的地都成了荒地,可故事还在。其实外公和木犁也在,一直都在,木犁躲在灶王爷家里,外公躺在田边的山里,为了写完上一代人的故事,必将永远都在。
二、再见木犁
七岁,是我记忆里家庭团圆的开始。
父母都没什么文化,他们很希望我能好好读书,将来能有出息。所以就因为老师打给奶奶的一个电话,我的父母便结束了多年的打工生活。
父亲既不如叔叔文化程度高能当老师,也没有伯伯驾驶的手艺能开车,好在他年轻的时候跟爷爷学过务农,懂得耕地、播种、插秧,还会种些青菜、水果,倒也能养家过日子。
三月初,父亲到爷爷家将爷爷前些年用的木犁给拿了来,种起家里荒了的地。牛,是爷爷养的,省了租赁的钱。父亲毕竟多年没用过犁了,在我的印象中,那一年父亲耕地用了很长时间,有两个周末我都跟着去过。最让我感到欢喜的是,我又看见了木犁,而且这次是可以那么真实的感受着它的力量。
爷爷的木犁与外公的木犁,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是被磨得锃亮的圆环,一样是开裂的缝里贴满泥土的底座。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爷爷的木犁,在犁臂中间,向右嵌着一个十几厘米的握把,父亲称它为犁耳,是在每次起犁时最为方便的手提处。父亲教我,起犁的时候,右手向后拽一下绳子,牛就会往后退一步,连接装置就会松些,左手握着犁臂将犁往左翻一点,等到犁铲松动了,左手再改握犁耳,往后一带,整个犁就提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改变方向再次下犁。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它的神奇。
从那时起,往后每年开春,总会有一两个周末,我都会跟着父亲去看他耕地,给它挡挡牛头,递递水。时间就像爷爷养的老牛,年复一年在田野里踏着步子,数着年轮,压弯了父亲的脊梁,辗转到我初中都毕了业……
我还没来得及长大,牛却老了!
外公睡着了!外公家的犁也睡着了!
爷爷老了!爷爷传下来的犁也老了!
木犁老了,关于木犁的故事还在,在我的脑海里。年幼的我,还来不及长大,来不及长大去讲述木犁的故事。
三、木犁老了
我的高一,好像一场梦一样,只有经过,没有结局。梦一醒,带来的变故就太多了。
2012年的秋天,我考进县城唯一一所民办私立高中,有幸进了最好的班。得知成绩的那天,父亲的脊梁明显直了不少,母亲只顾着杀鸡去了,是我点燃了父母的希望。这样的日子维持得不久,我开始迷恋网络游戏,期中考试的成绩在班里垫了底,从此,对学习再无兴趣。翻墙逃课、抽烟干架,我都学会了,学校再也无法容忍那样的我。就在元旦晚会的第二天,我被劝退了。父亲把我接回家中,第一句话就是:“不读书,你想干什么,难道就像我这样,一辈子种地?”我不敢看他,不敢看我的母亲,我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望,亲手浇灭他们的希望。
那半年,父亲将我留在身边,他说,放我出去,指不定哪天就要他去监狱里接我回来了,倒不如带在身边好好体会生活的艰辛。
我在家跟着父亲,学会了砍柴、种菜还学得一身好厨艺。三月开春的时候,我去爷爷家牵牛,父亲扛着老木犁,带着我和老牛一起去耕地。我跟着父亲,也学会了用犁耕地。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我学会了耕地的同时,老木犁断了。但是地还没有耕完,父亲便去买了一架新犁。新犁几乎都是铁质的,仅剩底座是木条而已。不知道是不是我与木犁太过亲密了,我对铁犁一点感情都没有。它篡改了先人的智慧,从原来仅有一处犁铲是铁质的变为仅有一处底座是木质的,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父亲似乎也不怎么喜欢它,他总说铁犁没有木犁好用,耕地的时候耕得不深,而且还不稳,老牛拉着都费力多了。我不知道,父亲是在心疼牛还是在心疼犁。
父亲让我跟在他的身边是对的,如他所愿,我没有学坏,而且还学会了很多东西,不论是为人还是处事,都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经历了这半年的务农生活,我切实体会到了父亲的艰辛,得到了成长。后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又重回学校,重读高一。
当所有人都觉得我这次会在读书这条路上安稳走下去的时候,又一次发生了意外。天性的叛逆,再加上抵不过贪玩的诱惑,高二的时候,跟着别人参与赌博,当场被校领导抓获,于是,我又一次回家了。
回到家里,父亲还是那句话:“不读书,你想做什么?”我带着愧疚,抹着已经没有感情的眼泪说:“我想去当兵!”父亲默不作声地走了,我知道,父亲同意了我的选择。
这一年,我没出去,就留在家里陪着父亲务农。很多事都和以前一样,三月开始耕地,无非就是换了铁犁,但我照样学会了。每天的山水都一样,每天的日出日落也没太大的变化,唯一缺的,是爷爷的身影。
前年的六月,爷爷得了脑梗,也睡着了。
或许是怀念他的木犁,所以睡了;或许是真的老了,所以睡了。我更愿意相信前者,因为山里的老人都是不服老的。
四、人是物非
两年的军旅生涯,转眼就走完了。
2015年9月6日中午,我回到家中。午饭的时候,父母都在,奶奶也在,我给他们拍了一张餐桌上的合影,只觉得温馨。他们问了很多,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那顿午饭没有鱼没有肉,但我吃的很香,一碗是父亲从田里摸来的泥鳅,一碟是白菜,一碗是芋头,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青菜,但我知道,这些蔬菜都是父亲自己种的,原来,这就是久别的家的味道!
午饭后,在家周围转了一圈,发现后院里放着两台我从没见过的机器,我问父亲那是做什么用的,他说是用来耕地的。这时我才想起,头年春节打电话回家,母亲就说过父亲年前把爷爷传下来的牛卖了。当时我心里就一个咯噔,怎么就把牛给卖了,卖了牛家里的地怎么办,原来现在还有这种机器了啊!我想,这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科技创新带来的硕果吧!我跟父亲说,挺好的,这东西比犁方便多了,还不用去费心思养牛。
父亲听了我的话,点了支烟说:“方便是还方便,就是田打得不够深,秧不好插,芋头也种不下,还得自己带锄头去挖,想想还是以前的犁好用啊!”顿了顿,父亲还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只是长长的叹了声气:“诶——”
我问父亲:“你是喜欢用木犁还是铁犁啊?”
父亲吐了口烟:“还是木犁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