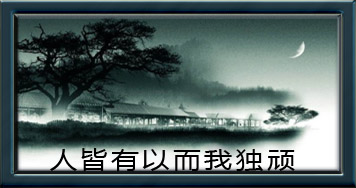【流年·满庭芳】天光水影中的婺源(征文·散文)
【流年·满庭芳】天光水影中的婺源(征文·散文)
![]() 这是一个晴朗的上午。缆车把我送上高高的山岗。我放眼远望,田野、树木、池塘、河流还有远山,都在灿烂的阳光下,泛着清亮的光芒。天空中是自由漂浮的白色云朵,偶然有几只鸟儿在白云下掠过。大地明媚而温暖,眼前的山坡上长满金灿灿的黄菊,宛若此地春天的油菜花一般,盛大无垠,令人惊艳。
这是一个晴朗的上午。缆车把我送上高高的山岗。我放眼远望,田野、树木、池塘、河流还有远山,都在灿烂的阳光下,泛着清亮的光芒。天空中是自由漂浮的白色云朵,偶然有几只鸟儿在白云下掠过。大地明媚而温暖,眼前的山坡上长满金灿灿的黄菊,宛若此地春天的油菜花一般,盛大无垠,令人惊艳。
是的,这正是晚秋中的婺源。仿佛千百年前,我就与她有缘,与她有个约会。直到此时,我才带着悠长的相思,从江南深深的青石小巷中走出,用双脚走过那些杂花生树的山岭,用双桨划过那些清波荡漾的溪河,迎着春夏的菲菲梅雨纷纷柳絮,穿过秋冬的萧瑟落叶朗洁霜雪,在无数的岁月轮回之后,拨开历史的云烟,一睹她的芳容美貌。
很多来到婺源的人,都盛赞她的粉墙黛瓦。公元740年,唐玄宗李隆基决定将安徽休宁县的回玉乡和江西乐平县的怀金乡划出设置婺源县,县城设在了清华镇。回玉、怀金、清华,唐玄宗不愧是盛唐最有才气的皇帝。说来也巧,不知何时,婺源有了李唐王朝的一支后人。以后,经历宋元明清各代,婺源这回玉怀金之地,就有了书院、阁楼、祠堂、牌坊、古塔、园林、古村,粉墙片片、黛瓦层层,门前水声,窗后鸟鸣。那些典型的徽派建筑,散落绿树翠竹间,白墙与青瓦错落,青翠与黑白相映,宛若仙境。
很多来到婺源的人,都被她漫山遍野的鲜花迷醉。春天,那片近千亩的黄灿灿的油菜花,仿佛金色海洋。微风吹来,吹起芳波花浪,游人的鼻端会扑来阵阵清香。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有一首写油菜花的小诗曰:“篱落疏疏小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个时节,被人称为鲜花小镇的篁岭村,桃花、迎春、梨花、杜鹃与油菜花交相辉映,沾着雨露的花朵,在阳光下闪烁出五彩缤纷的光点,妩媚恬静,馥郁芬芳。蜜蜂与彩蝶在这花海中上下翻飞,让人不饮自醉。
而我走进婺源,却觉得最美的不是那些晚秋中层林尽染的山岭,不是倚着山岭而建的白墙灰瓦的古村,也不是那些五彩缤纷的春华秋实——在篁岭我实实在在地见识了那盛大的“晒秋”民俗和那遍野的如金河流淌的贡菊花。我以为最美的是婺源的水,那些澄澈如镜的池塘、水潭,那些缓缓流淌的溪流、河川。
婺源的水不似我居住的苏南的水,没有像太湖那样一望无际恣意汪洋的盛大水域,没有像长江那样澎湃汹涌浩荡奔流的宽阔水体。婺源的水,更多的是像被树木的枝叶切割的光影,像是被天上的仙女随意抛洒的珠玉。那些池、塘、潭、和分散在山岭、山谷的零碎稻田,那些涓流如线的小河、山溪、沟渠,隐藏了婺源人千百年来的岁月符号,包含着亘古以来所有的生命密码,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自身,都依赖这些千年闪亮的水源生存。
据说,远在商代之前,婺源人的先祖就生活在这片山水之间,他们不断的缠斗、接纳、融合形成了中原人所称的山越族。这里山重水复、物产丰饶,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岁月里,时间仿佛变得如同流水般永恒,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唯有山峦在四季变幻色彩、流水在晨昏轮替颜色。后来,中原大乱。晋人南迁、唐人逃难、宋人避乱,他们不约而同的沿着溪河,躲进婺源。于是,这里开始有了稻田、有了瓜棚、有了大屋顶的民居,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融,让时间与空间、山峦与流水,都变得鲜活而充盈。
河水、溪流像是男人,他的理想在远方。而池塘、泉潭却像女人,她坚守着信仰不动不移。四面群山,水瘦如线,缺少耕田。婺源的男人不得不跟着溪流的指引,通江达海,纷纷出山,走出去最多的是读书人和商人。多少年后,他们中有人发达了,发了大财、当了大官,于是回家修桥铺路盖房子。男人走了,女人在山野和薄田间坚守,坚守着贞操,深藏着挂牵。等着儿子、丈夫,等着远方的人。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南唐词人温庭筠的这首小令或许最能道出婺源女子等待远方归人的心境。我是从江湾走进婺源的,汽车从山前的一个弯道转过,只见一道溪流飘然而落,像是一条白练缠绕着河岸,向着远山缓缓流去。河岸上是一群呱呱鸣叫的鸭子,鸭子身后是一座灰白的古旧老屋。雕花的窗棂有些歪斜了,一张少妇的脸庞正转动明眸向外张望。我忽然想到,这在光影里瞬间定格的一瞬,或许已经叠加了千年万年。在历史的光影里,有多少娇羞的少妇,就这样张望着、张望着……婺源绵细流短的溪流,像极了思妇的泪线。而那池塘中由泪水滴落溅起的涟漪,像极了女人满是褶皱的裙摆。
在漫长的岁月里,天空、山岭、林木、村落、狗和篱笆墙,都成了河流、池塘的底色,一年年,一代代叠加、沉淀。河流为婺源人打开通向远方的时光之门,池塘让婺源人的生活多了浪漫与丰润。婺源的水照射着春光秋晖,也融入风雨霜雪。商人归来带回财货与富裕,官员退隐携来文化与智慧。于是穷乡僻壤的婺源不仅是朱熹、洪秀全、金庸的生命之根,也由那潺潺溪流,迎来李白、苏轼、黄庭坚、何执中、宗泽、岳飞……这样一批声名显赫之人。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是婺源土著,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人。他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后人尊他为“朱文公”,评价他为“理学正宗”,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圣人。正是他的这首小诗,让少年时的我,结识了这位朱夫子。年少轻狂,好发奇想。那时,我常常不解,如此圣人,如何这般格局狭窄,那个池塘怎地只有半亩大小?及至今日到了婺源,眼见山岭纵横,谷地崎岖,满目起伏,才晓得,就这半亩方塘,也算是天光云影下的大气象了。
朱熹一生,重视教育。他的足迹踏遍江南半壁河山,亲手创办了同安县学、武夷精舍、考亭书院,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在婺源的考水村明经书院,朱熹留下了“明经学校,诗礼人家”的墨迹。婺源人守着青山绿水,口诵四书五经。世代耕读,人称“文人圣地”。据《婺源县志》记载,仅一个小小的考水村,自北宋熙宁起的两百多年间,就出了十六位进士。“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陶渊明的诗句,或许正是婺源子弟世代耕读的写照。
过了江湾,我们望山前行。有人说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也是婺源的后代子孙。他的祖上故里就在浙源的凤山村。据说,当年他的远祖北宋太常寺太祝查元修,梦里得到神人指点:“见凤而止,遇凰而住。”于是他一路北行,来到婺源的凤凰山下定居。时光荏苒,查氏遂成婺源望族。金庸原名查良镛,他把镛字一拆为两,用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笔名。2005年金庸接受《环球》杂志驻香港记者廖翊采访,金庸对记者说:“我和你算得上老乡——我的祖籍是江西婺源,后来才迁到浙江海宁的。”
婺源是个世外桃源,风景如画,民风淳朴。而金庸却用他的一支笔,独创出如梦如幻的武侠江湖。他笔下那些惯用降龙十八掌、葵花宝典的江湖大侠、各路英雄,习武修行之地,大多是明霞可爱,流水弦歌之处。“三九大老,紫绶貂冠,得意哉,黄粱公案;二八佳人,翠眉蝉鬓,销魂也,白骨生涯。”金庸的武侠世界,具有奇幻的美,哲理的美,风光的美,不知婺源的奇山美水是否冥冥中也与他的武侠世界相合相契。
游罢“鲜花小镇”走下篁岭,长长的浮桥之下,一股清溪从两山间的峡谷汨汨流淌而出。它越过涧石,爬上岩头,曲曲弯弯,顺势而下。晚秋的阳光下,它闪闪发亮,映照着岸边的林木、翠竹、野花,清澈而欢畅。它在山湾处变成一股澄澈的激流,与左边下来的溪流汇集而变宽。溪水在空谷中发出咝咝声响,那是它欢快的歌唱。我想,它还会汇集更多的溪流,用更大的力量冲出山去,通江达海,奔向海洋。婺源的汉子们,自远古到近代,就像这婺源的溪水,去赶考、去经商,他们为着家人的幸福、个人的前程,年复一年地走的更长更远。
有河就有桥,桥是人的捷径,也是河的装点。有了河流,就有了雨亭、水埠、桥梁和桥梁两侧的沿河小路、临水街巷。婺源的美,多一半在小桥流水。梁桥、拱桥、浮桥、吊桥、廊桥,婺源的桥多姿多彩。就材料而言,有板桥、竹桥、石板桥,如今也有了铁桥、钢筋水泥桥。婺源的桥不仅方便人通行,还有蓄水、通舟、调节水势的功能。有了桥,婺源的绿茶、砚石、木材、竹器、山货,才能便捷地走出大山深处。有了桥,也就成就了一代代婺源的名商大贾、官宦人家。也由此,在山外发了财的商人,当了大官的书生,回归乡里,第一件想到的善事,就是修桥铺路。
婺源的桥,最美是廊桥。“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廊桥又称风雨桥,晴天遮阳,阴天避雨。站在岸上看桥,那雕梁画栋的长廊桥身倒映在溪水里,随水流动,闻风漂移,风吹来,桥影弯曲,一条鱼儿忽然跃起,桥影又碎成了涟漪。站上廊桥向外望,眼前碧波荡漾,游鱼嬉戏。远处天空湛蓝、山岭朦胧、河流明灭、村落依稀,让人有一种“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奇幻错觉。那种错落有致的秀美,将人带入天人合一的意境。
婺源的池塘、泉潭大多精致小巧,它们或方或圆,或规整或天然,却都纯净透明、若明镜照天。它们像是天庭仙女不经意间摔落人间的梳妆镜,零零碎碎地散落在山坡、谷地、村落、林间。滋养着生命,慰藉着魂灵。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照着姑娘、媳妇浆洗衣裳、淘米洗菜,看着农人、商人、书生劳作、算计、苦读,听着狗吠、牛叫、蛙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站在高岗,远望那些大大小小、随意坐落、闪烁明亮的池塘、泉潭,我忽然有些感动:世上万物,都如金刚经所言。自有天然的秩序,来来去去,一如钟摆。
岁月、历史、生命,其实质都是一种时间现象。时间的钟摆,由洪荒无涯的宇宙操控,在天地间摇摆。当它摇荡到1851年1月11日这个节点,咣当一声,历史被敲响了。远在婺源千里之外的一位38岁的落魄书生洪秀全,站在广西金田的犀牛岭上,宣布向大清王朝开战。于是,从那时起一场血雨腥风,在岁月中弥漫了十四年。江南为之变色,婺源也未能幸免。苍山如海,夕阳如血。史载,洪秀全麾下的天平军曾在婺源与清军大小作战八十场,十二次攻入婺源县城。战争宏大而惨烈,溪流中漂浮尸首、池塘中流淌血痕。
洪秀全,这个史书上言之凿凿地说,出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的造反者,却原来是婺源人的后代子孙。如果不是走进婺源的大山,来到车田溪畔,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位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的“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教主,他的生命之根会在世外桃源般的婺源。
从时间隧道穿越,在那个盛开黄荆花的季节,一位叫做洪延寿的老者,越过安徽的乌龙山脉,走进婺源的大山深处,在大鄣山下溪水畔,一个开满黄荆花的地方,老者种下一棵香樟树。从此随着这棵香樟一圈圈的年轮扩展,这里逐渐形成一个洪氏子孙聚集的村落——车田村。洪秀全就是大唐归隐长史洪延寿的后裔,他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耕读世家、四书五经,没有引导他走上仕途,光宗耀祖。地摊上的一本小册子,却让他皈依了基督,在血与火的厮杀中,做了“天王”,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打的东摇西晃。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披着西方洋教的外衣,骨子里其实还是孔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诲。
像历史上的所有皇朝开创者一样,定都南京当了“天王”的洪秀全,也曾千里迢迢,逆着溪水,来到婺源寻根祭祖。他来到婺源洪氏开山鼻祖洪延寿种下的古樟树下,意气风发的吟诵他的祭祖词:“如盖亭亭樟覆霓,专程祭祖到轮溪。残庐依旧莽荆发,故墅犹新鸡鸟啼。河曲流长翁醉钓,山崇峰峭月忧低。裔今壮志乘天马,大训堂开阅战车……”如今,时间的钟摆,带着中国人走进新的时代。当我站在洪秀全当年祭祖的古樟树下,发思古之幽情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早已灰飞烟灭,洪氏家族留在婺源的宗祠“大训堂”也早不见踪影。唯有脚下的轮溪还依然澄澈清凉,缓缓流淌。我在这清清溪水中照见了自己的影子,却不知道能否在其中找到历史的踪迹。溪水流淌着时间,时间在流逝中带走了历史的密码,让后人无法破译。
“净几明窗,好香苦茗,有时与高衲谈禅;豆棚菜圃,暖日和风,无事听闲人说鬼。”岁月匆匆,人事沧桑。洪秀全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婺源山里人关于“长毛”的传奇,还有可以载入史册的《天朝田亩制度》。
我在中午的阳光下,沿着轮溪边上的小路缓缓前行。阳光投进溪水,水面上波光粼粼,像是无数斑斓翻飞的金蝴蝶。有哲人说,沿水而行,最容易催发人的思绪,智者爱水。也有人说,邻水而行,最易催动诗情,激动的心,涌动的水,最易产生共鸣。只可惜,我既不是哲人,也不是诗人,我写不出哲理,想不出诗句,只见清清流水,映照着蓝天白云。
人生苦短,大地永恒。
为作者的好文笔点赞。祝再创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