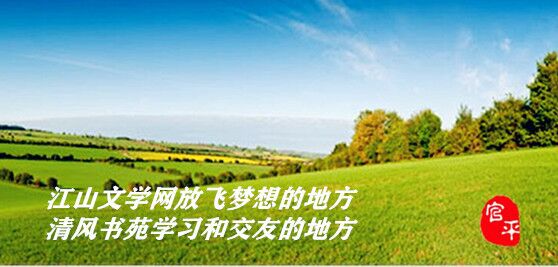【八一】火草粑的味道 (外一篇·家园)
【八一】火草粑的味道 (外一篇·家园)
![]() ◎火草粑的味道
◎火草粑的味道
今天在街上,碰到了一个老农卖的一种野菜,我们这里叫火草,它一般生长在清明时节,所以书上又叫清明草。
火草是我家乡人的独特叫法,在《本草纲目》上说,它的名字有鼠曲草,佛耳草,米曲,茸母,香茅,无心草,黄蒿等等,就是没有叫火草的名字,是不是蒿草讹化而来呢?不得而知。
据说火草可以入药,具有化痰、止咳、降压、去风等功效,南宋诗人陆游曾有“更煎药苗挑野菜,山家不必远庖厨”的诗句,这里的“药苗”,指的就是火草。它的叶很小,略略呈椭圆状,浅绿浅绿,叶面茎梗上覆有短短的灰白绒毛。老的,顶梢有一簇簇小黄花。
而火草耙,顾名思意就是掺和火草做成的耙耙。说到火草耙,不禁想起了母亲。记得儿时,母亲每年都要做火草粑给我们吃的。火草只能在清明节前后十天左右采摘,因为采摘早了火草芽苗才现,收益不大,采摘晚了火草茎叶俱老,又韧又涩,难以下咽。而每年的这段时间母亲都要带着我们兄妹去附近的山上摘火草,家乡毕节城周围的纱帽山、石牛石马山、虎踞山,文笔山,灵峰寺等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
采摘时,多选嫩的掐。回家后,母亲精心捡去杂质,漂洗干净,用大火煮开,趁水没有冷却加入糯米粉,白糖和细包谷面,揉捏成一个个窝窝头,放入蒸锅蒸熟。那火草的清香,面粉的甘甜,吃起来的柔软劲道,真的好醇好香。
再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调味品丰富了,烹调手法也多样化了,火草耙有素蒸的,有油烙的,市场上也有了火草耙专卖点,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位三十左右岁的女同志在一块长方形的面板上摆上火草耙,然后用一根带子把面板套在脖子上,几乎天天在街上叫卖,高声喊着:“买火草粑吃喽,热哄嘞,买火草粑吃喽,热哄嘞”……那声音充满着为生活奔波的沧桑,直入耳膜,钻进心扉。但也许是职业特点吧,她的耙耙菜少面多,吃来总感觉没做出当年母亲做的那种味道。说到这,今天我也享受不到了当初等待吃火草粑的那种期盼,以及兄妹几个围着父母亲吃着火草粑时的那种血浓于水的温馨甜蜜亲情的味道。因为母亲离开我们已有三年,这些都只能埋藏在深深的记忆之中了,想到这,心里不由又泛起一缕难言的滋味。
时光荏苒,年复一年,满山遍野的火草“春风吹又生”,那淡雅的小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而于我,火草耙,是春天的味道,也是清明的味道,更是对母亲怀念的味道。
◎糯米面的味道
糯米面,就是用来做汤圆的那种面粉。
记得儿时,糯米面是用糯米在碓里磕出来的。具体做法是,先把糯米浸泡几日发胀至用两个指头轻捏成粉的时候,就带上竹子编织的大小簸箕,箩筛,瓢儿等,到有碓的人家去磕。
碓,有一根约长三四米的圆木,圆木的顶部有一根0.5米左右长的竖头,上面用铁皮包裹着碓头,正好对着下面用石头打制的碓窝,碓尾制成两翼,翼翅刚好嵌进两旁固定的石门里。
然后用脚用力地踩住碓尾,使碓头在碓窝里来回上下的磕糯米,将糯米磕成粉未,再用箩筛反复将细面筛下,剩余的米粒又放进碓里再磕,直至全部磕成粉未后,放在大簸箕里,摊开阴干。以后,加入用猪板油,白砂糖,玫瑰花,花生,核桃仁,芝麻等拌成的馅子,就做成了香喷喷的汤圆。
说到用猪板油,白砂糖,玫瑰花,花生,核桃仁,芝麻等拌馅子,不自禁的想起了父亲,儿时,我们家的汤圆馅子就是父亲用这些食材做成的。这是过春节最累人的活,而每逢过年父亲都做这活,记得父亲做馅时,也许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吧,鼻涕都差点流到馅盆里了。就这样,我们依在父亲身边,看着父亲在重复擦鼻涕的辛苦中把馅子做好。
岁月总是沉淀沧桑,回忆会牵引出许多美好和忧伤。宛如此刻,年味悠悠回忆中,想起了岁月不饶人,父亲日渐苍老,八十高龄的父亲也不再是从前,特别是前久生病住院了两个多月,虽然康复出院,但人老抵抗力弱,静养保养不能大意。春节就要来临,传统年味已淡淡而去,但只要父亲安康,就是我们当儿女的幸福。
糯米面,于我,是冬天的味道,也是过年的味道,更是惟愿父亲健康的味道。
有一种爱此生无法偿还,有一种情此生无法忘却。这就是养育之恩!希望子欲养,而亲都在,不给自己留遗憾。祝老人家日渐康健,快乐每天!向老师问好,老师写的文章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