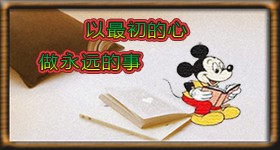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我们的老板(小说)
【流年】我们的老板(小说)
![]()
一
一切从头开始吧。
我四十五岁那年,突然发现自己活得很失败:体制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专生,原单位倒闭后不得不频繁更换工作,社保医保无处挂靠,基因里又一桩成功的小生意也找不到。我的气色代表了我的颓败。有一回,我偏头痛数日不愈,不得不去县医院神经内科找大夫。我前面是一个胳肢窝夹着公文包,穿着雪白雪白衬衣的大背头领着他的母亲在看头晕症,这个大背头我认识,他是县委组织部知工办的干事。一个窄脸大夫坐门诊,十分细致地询问病情,掰开老太太的眼睛用小手电探照眼底有无病灶,让老太太伸出舌头察看舌苔,又用一把不锈钢小锤轻轻叩击膝盖,叩一下,老太太跟着哆嗦一下……我庆幸遇到了一个好大夫。接着,就在我慢条斯理地组织语言时,窄脸大夫问起了我的病情。这会儿知道心疼时间了,两分钟不到就给我看完病,一口否定我提出的疑是早期脑梗,说我是在胡思乱想。他接着喊下一位,甚至连我抽烟和喝酒的习惯都没问。当我带着阿斯匹林、西比灵和另外一些常规的头痛药回到家时,感觉受到了什么侮辱。
我决定离开这个发展迅猛却江湖气十足的豫北小县,去省城投奔我的两个中专同学:每年一度的同学聚会,他俩一个坐宝马,一个开大奔,争抢着从后备箱里往外搬“五粮液”“剑南春”,还有成条的“软中华”。那阵势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从马路沿上捡来似的。我想他俩指头缝里露露,就够我一辈子吃喝了。说走就走,人生容不得太多迟疑。长途汽车站检票员脸上有一种疲惫的冷漠的表情,间或一点点看不起乘客的高傲,她们用下巴示意我把行李放上安检机后,又用金属探测器在我身上上下扫描。我非常讨厌这个被迫抬起双臂的动作。我在省城新北站下车,门口到处都是拉客的黑车,却看不见张同学的宝马在哪里。我拖着一只破旧的拉杆箱正在东张西望时,一辆载人摩的从我面前呼地一下闯过,两只轮子从我伸出去的一只脚面上“嘭”一下碾过去。摩的司机头也不回,狠狠骂了一句开跑了。这时张同学沿着斑马线从马路对面跑过来,接过我手里的拉杆箱子。我们是打的离开北站的,他衬衣领口的污渍和皱巴巴的西装提醒我:之前他的宝马可能是装饰门面的一件道具,要么就是他的人生出现了问题。
很快,我知道他从事的神圣职业是什么了。在省城西郊租来的一个未装修的毛坯房里,张同学把我当作他的新同事,就这个伟大的行业作了一番启蒙教育:一个全国第二十三家拿到直销牌照、准备把安利集团拍在沙滩上的新型直销公司,只需12000元启动资金就能打开通向巨额财富的大门。下课后,张同学和他的同事们在毛坯房里就着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一张酒店专用圆桌,开始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晚餐,话题自然离不开成功后的憧憬:购买什么配置的轿车,多数人的想法是在东区购一套四室二厅的学区房。有人一边说笑,突然又抹开了眼泪。有人给我一杯内蒙古生产的“闷倒驴”,我不敢拒绝,结果喝得嘴里火烧火燎。晚上张同学让我跟他一块睡地铺,拐弯抹角打听我的积蓄,听说我只有两万元存款时他非常不满:“你可是有名的沉实户,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钱都哪去了?”
我吓坏了,天没亮就悄悄溜出来,拨通了另一个孙姓同学的手机。
孙同学果真开着大奔来接我,省城上下班高峰期的路况简直一派地狱景象。孙同学把我安排在一个五星级宾馆,陪我聊了一天一夜。宾馆的卫生间是透明玻璃隔成的,让人觉得很别扭,尤其是两个男人在一块的时候。孙同学告诉我那是为了点燃激情而专门设计的,我心说自己的饭碗都顾不住了哪还有什么激情可言。孙同学是倒腾医疗器械发的家,大奔不是借来的,他带着我大把大把地花钱,一点心疼的样子也没有。孙同学说他很空虚,整天除了数钱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他领着我去放生,把从菜市场买来的上百只鳖拉到豫西一个小山村,扑扑通通倒入浑浊的池塘。放生是一种时髦,富人们的恕罪或心理释放。我们前脚走,那个小山村手执各种捕鱼工具的孩子们后脚就包围了那只池塘。孙同学接着又带我去豫晋交界处的太行深山参加心灵鸡汤方面的培训,一人一身汉服一把折扇,在导师的指导下背诵《弟子规》,更多的时候是被导师赶到山沟里面壁思过。山庄老板被他们出的餐标吓坏了,冰箱和山坡散养鸡场已经无能为力,不得不下山去城里的农贸市场紧急采购一批高档食材。在这群汉服中间,我先是形单影只,继而又自惭形秽。我也瞧出来了,我和孙同学是走不到一块的,我们不在一个阶级:我尚在为温饱奔走,人家却在为钞票多得数不过来而犯愁,脑袋快被金钱涨破了。有一回,孙同学带我造访一家深不可测的爱情机构,感情在那里遭到极度挑战。为此我染上了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隐疾,虽然使用了强效药物,却一直摆脱不掉——病菌仿佛住进了我的身体里面。
最后我不得不打道回府,离开了水土不服的大省城。
二
跳下长途汽车,在县城那个标志性建筑下面,我呆头呆脑地站了好一会儿。马路对面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吹嘘过头的售房广告,广告下面是一家正在营业的中型酒店,门头上有三个醒目的吸塑发光字:烙馍村。我下意识地按了按上衣兜,那里有5000块钱,从省城回来的路上突然冒出来的。当时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自己碰到了坏人。听说有一个在长途车上作案的新型犯罪团伙,专门往你包包里塞手机和现金,其中一人大喊大叫拽住你不放手,说你偷了他。另外两个会冒充公安把你架下车去接受处理。等长途客车开走后,他们就会对你下手,通常是暴打一顿后再洗劫一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让你哭喊无门。我出了一身冷汗,等待着厄运的降临。谁知一直到市里,那个大喊大叫的人还是没有出现。我冷静下来后理了理思路,哦,我想起来了:上车前,孙同学给我买了一堆饮料零食,装在一只超市手提袋里。过了黄河大桥我扒开一看,里面除了尖叫、脉动、洽洽瓜子和双汇牌火腿肠外,还躺着一沓钞票。我的心头不由一热,泪水一下子盈满了眼眶。下车的时候,忍了一路的泪水终于吧嗒吧嗒砸下来。
现在,我决定先把这笔钱存进银行,我可不想把孙同学的一片心意弄丢了。人倒霉了哈事都可能发生,不光喝口凉水炸牙,放屁都可能砸伤脚后跟。说来连自己都不大相信:有一回我拧衣裳时竟把手腕拧伤了,差点脱臼;还有一回,我正穿衣裳时水壶嗷嗷尖叫起来,媳妇在卫生间冲我喊叫,仿佛家里失了火一样,我起身往厨房跑,却被穿了一半的袜子绊倒了,磕破了自己的眉弓。这时我肚子也饿了,存完钱就去烙馍村点一个凉菜,外加一杯扎啤一碗放了黄花菜和云丝的羊肉烩面,几片肥嘟嘟的黑木耳。如果运气好的话,再问问他们要不要帮厨的。县城真是一个能丢下最后一点谦虚的魔鬼。一个四十五岁的老笨叔,不敢再东张西望了。
令人欣慰的是,烙馍村酒店的橱窗上正好贴着一张A4纸打印的招聘启事:打荷一名砧板一名,工资面议。我的运气太好了!进去后,我立即修改了自己的菜单,一杯扎啤变成了两杯,素凉菜变成了荤素拼盘。上的什么凉菜我忘了,但我记得烙馍村的凉菜盘确实与众不同,还有收银兼打菜的那个姑娘不停地往菜上加菜:骨堆堆一大盘!感觉像是一块钱当成了两块花。她是个时髦、苗条,很有吸引力的姑娘,从头到脚无可挑剔。尤其她身上迸发出来的农村女孩特有的那种朴实和信任感,让人感到亲切无比,就像碰见了自己的本家侄女。人生路上我虽然缺乏成功的案例,但毕竟是个过来人,能一眼看出她是个善良的姑娘。我对烙馍村一下子有了好感,决定留下来。
吃完烩面结账的时候我说明来意,姑娘说她们需要打荷的小弟和会手艺的配菜师傅,她问我:你以前在厨房干过吗?我摇摇头说,我会劈柴、照看炉子。姑娘嘎嘎笑了,在刘海儿和笔直的眉毛下,她的眼睛出奇地亮,“我的大叔呀,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用斧头劈柴?现在炒菜用的都是天然气,柴火早过时了,煤炭也不大用了!”我坚持不走,哪怕让我洗碗择菜也行,我不信烙馍村就不需要一个忠心耿耿的老家奴。姑娘没办法,就用内部通话器把老板叫了下来。
一个比我年轻几岁,穿着白色厨师服的汉子从拐弯楼梯走下来,他一边下楼一边解开腰间的蓝色围裙摘下头上的白高帽拿在手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路大国——既是老板又是大厨,像他的名字一样生了一张国字脸,厚嘴唇,身材瘦削,并非我想像的那样:凡是酒店老板,都该有一个凸出来的大肚子和傲慢的脸相。他身上有很重的烟熏味和葱花味,头发一绺一绺黏糊糊地贴在头皮上。我伸出手,向我未来的老板陈述来意,他却没有半点惊喜,有的只是疲惫。他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却并没有答应收留我,我心里一阵阵发凉。我缺少谋生技能,人生舞台上总是扮演着失败的角色。这回我决定拯救自己。我说我从省城到县城,在我几个同学的盛情下,一路吃过不少酒店和夜市大排档,却没有一家像烙馍村这样干净整洁,凉菜盘又深又大,打菜的手法又是菜上加菜。我敢把手放在胸口发誓:这样的店一定会顾客盈门。那天我的口才出奇的好,但我相信我讲的话并非全部是奉承。
我的夸夸其谈丝毫不起作用,路大国紧蹙眉头,仍然没有同意。打菜兼收银的那个姑娘听了我刚才的夸赞之后脸色生动,替我讲起好话:“老板,打荷不是没人嘛,为啥不叫这位大叔试试呢?我看他也是个实诚人,干活肯定差不了。”
路大国犹豫着,对那个姑娘说:“打荷要的是眼疾手快,年轻人比较适合,他都四十五了。况且,打荷都是学徒工,待遇很低的。”我再次陷入失望,目光无助地在餐厅睃来睃去,等待那个姑娘能重新为我说些好话。(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跟人家非亲非故的)
就在这时,门口出现了一阵骚动,几个在散台吃饭的客人站了起来。起因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拉着她的二三岁的孩子去寻厕所,或者打算到店外的空地上把事情解决掉,谁知孩子跑到正门口却憋不住了,蹲下来就把问题解决在了酒店的大堂里。年轻的妈妈一时间手足无措,满脸歉意地望着服务员。嘴里咬着肉块的客人放下筷子,脸上露出了不满和无奈的表情。年轻的妈妈问服务员要垃圾斗,准备有所行动。这时一个长着双下巴,发髻高挽,脖子和手腕上金光闪闪的女人从楼上噔噔噔跑下来。这女人是个大腿肚,走路非常有力,高跟鞋仿佛要把地板戳出几个窟窿似的。大腿肚一边抱怨酒店一楼为什么没有厕所,一边拽起那位年轻妈妈和她的孩子就走。年轻妈妈满脸愧意犹豫着,一脸横肉的大腿肚训斥她:“别管它,一堆服务员干啥的?”把她拽出了门外,把一个难题留在了店内。有这样一位母亲带着,要不了多久,这个年轻妈妈也会飞扬跋扈起来。
路大国很气愤却又不能发作,那个打菜的姑娘,后来我才知道她叫艳菊,手忙脚乱地去找垃圾斗和锯末。正在用餐的客人纷纷抗议,把怒气全转向了酒店,有的甚至提出了退餐,如果不能让那团秽物迅速从他们眼前消失的话。是时候了!我果断站了出来,一边对自己嘟囔了一句,一边抓起餐桌上的一叠餐巾纸,神色凝重地朝那个难题走去。
像我这样既没手艺又没有背景的中年人,只有选择像机器那样干活,同意人家给你最低的工资,同意酒店所有人把今天这件光荣而艰巨的差事当作我长期的任务之一。无论怎样,烙馍村还是收留了我。
三
要是你没有开过酒店,尤其像烙馍村这样规模不大省略了很多岗位的店铺,你就不知道有多么麻烦,决非很多人想像的那样:老板穿着丝绸唐装,吮着茶壶里的信阳毛尖,指头间夹着玉溪烟卷,就把嘎嘎响的钞票一张一张装进口袋里面了。我亲眼目睹过路大国一整天的生活节奏后不由替他犯愁,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一脸疲惫,间或挥之不去的焦虑——他的每个手势和眼神,都带着那种让人容易产生误解的表情。不少熟人来酒店吃饭,见了他就提醒他的脸色不对,还有他的黑眼圈,让他注意休息和养生,并举例证明:谁谁谁三十多就脑梗了,嘴歪眼斜的;谁谁谁还不到五十岁就脑卒中,硬是把自己累死了。挣恁多钱干啥?还不知道是给谁挣的?
每天一大早,正在酣睡的传菜员和学徒工中间不定哪一个会被路大国从被窝里拎出来,极不情愿地揉着惺忪的睡眼,从床头的插座上拽下正在充电的手机,打着哈欠跟路大国一起去市里进货。路大国一直想买一辆客货两用的皮卡,资金却总是紧张,他不得不继续忍受这辆二手的“长安之星”面包车:前保险杠面板怼了两个坑,车体上的剐蹭因为没有及时补漆已经生锈,两个型号不一的倒车镜显得很滑稽。有一回,因为图省钱加了一家杂牌加油站的汽油,居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长安之星”的发动机正跑着突然一下子抱死。更换后的发动机大不如原车发动机,经常抛锚,把路大国和他的鸡鸭鱼、干鲜、青菜一起扔到半路上。他让传菜员和学徒工轮流跟着他去市里,一是帮他看车验菜,二是抛锚之后再帮他推车。好多回,去进菜的年轻人撅着屁股在“长安之星”后面使得直喘粗气,路大国也从驾驶室里跳下来,歪着身子,一手掌握方向盘一手推车。这些90后大多是夜猫子,不去网吧待到后半夜是不会上床睡的,“宁愿三岁没娘,不愿五更起床”,深睡中被路大国从被窝里拎出来,简直忍无可忍,却又敢怒不敢言。一路上他们都在打瞌睡,头一栽一栽的。到市里验货的时候仍然是满脑子浆糊,总是出错,路大国经常发脾气却又无可奈何。后来我自告奋勇替代了他们。我经常五点钟醒来后就再也无法入睡,我会去新建的文化广场看人家打太极拳打陀螺,有时也跟着老太太们扭几圈“小苹果”,一直磨蹭到上班时间。后来一打听,不少跟我一样的穷人都有这个早起的习惯,尽管乡镇换届、县财政催收和城区拆迁规划轮不到我们操心,我们却还是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