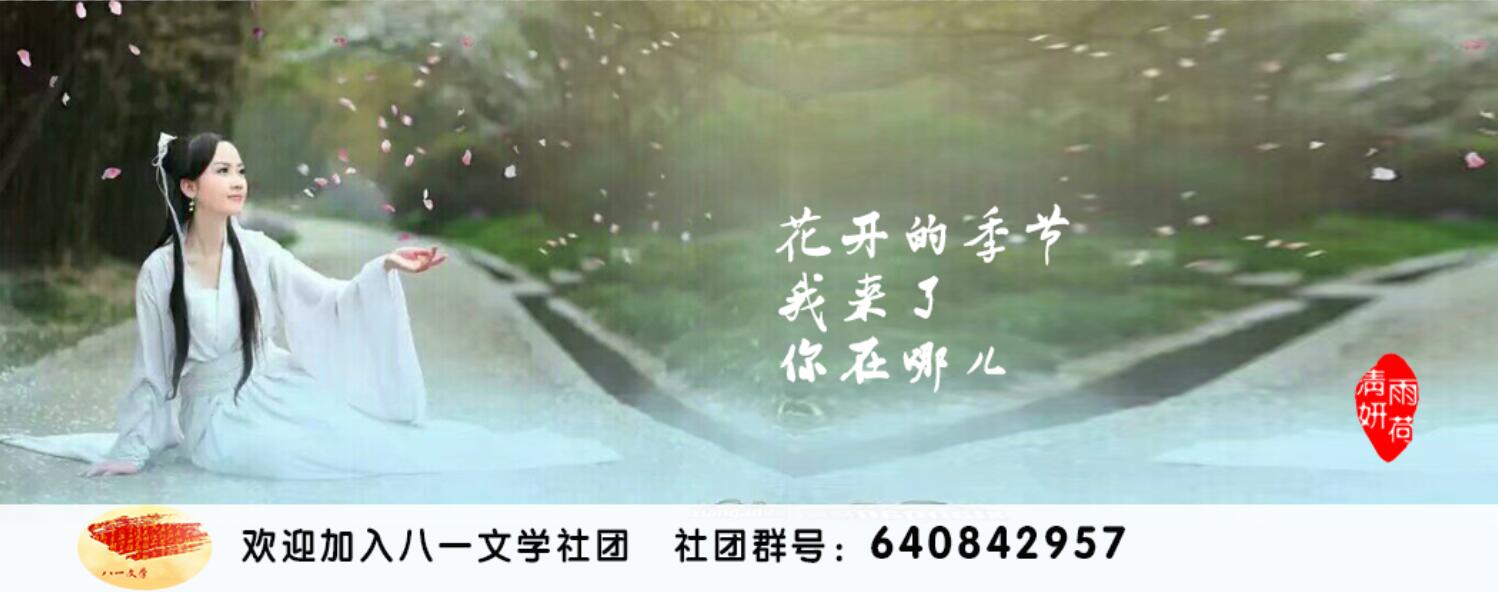【八一】默记少时但店镇(散文·家园)
【八一】默记少时但店镇(散文·家园)
![]()
今年初冬,事隔三十多年,我走进了故乡小镇——鄂东黄冈团风县但店镇。它是团风县的东北门户,318国道穿境而过。也曾是我小时候羡慕的“城市”。镇因驻地而得名,远在前清时期,本地但姓人家在此开设铺店,故名但店。1949年以来,行政区划几经变更,由解放初的第六区变更为但店区、但店乡、到如今的但店镇。
对于但店,我有着较深的少年记忆。走近它,遗落于风尘中的往事,渐行渐近。但店曾经的美,也象是电影分镜头一样,一一呈现在我眼前。那种美丽,含蓄而内敛,虽落满岁月尘埃,仍饱含着时光的味道。朴素内含静美,简约不失繁华,沧桑不减韵味。
还是八、九岁的时候,父亲在但店镇基层人民银行工作,趁着放假的时候,我央求母亲把我送到但店住些时间,体验一下“城镇”的生活,那是我羡慕的一种奢华,一种幼小的虚荣。但母亲没有时间送我,我就大胆地提出来,我自己走去。母亲说:“你有这大的胆子去?我就让你去。”我当时正是年少不怕事,说走就走。母亲给我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我空着手就走了。临行前,母亲交待说:“你从湾里走到大队,再上公路,沿着公路右边一直往前走,大约有20多华里的路程,看见两边房子很多的地方你问一下是不是但店。”我记住了母亲的嘱咐,从家里出发,顺着乡村小路,一路小跑,很快就到了公路。那个时候的公路,是土基路,车少人稀。为了安全,我还是靠着路的右边,一路走一路问一边欣赏着路途的风景,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到但店。
那是我第一次到但店,第一次见到街道、百货商店、生产资料商店,排列整齐的房子。父亲所在的单位处在正街的左侧,对面就是百货公司等商业单位。街道用水泥倒成的路面,自东到西,法国梧桐树分列两边,绿绿葱葱,排列整齐,像是两列士兵一样把守在那些个单位的门前,街面干净、整洁,给人一种清新之感。
到但店的第二天,正是但店逢集的日子。听父亲说,每逢这样的日子是小镇最热闹的时候。而此时的我,爱看热闹。晚上很是兴奋,一大早就早早起床。最先开市的是馒头包子餐馆。凌晨五、六点,月落星稀,小餐馆屋内热气蓬蓬、面香笼罩,室内灯光斜映街面,打破了小街的寂静。人们从各个村落一齐涌到小镇,络绎不绝、人流如潮。农人们或背、或挑、或提、或拉、或抬,家禽、谷糠、蔬菜、鸡蛋、红苕、柴火、土罐,以及簸箕等手工艺品……品种不一定丰富,但足以让赶集的人们交易一个早晨。太阳升起,整个小街,充满了叫卖声、吆喝声,很是热闹。
不一会儿,赶集的人们都交换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陆陆续续到小餐馆进餐。肉丝面条、面窝、油条、包子、馒头是那时候的奢侈食品。小小的我看着直吞口水。不一会儿,老板娘把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送到我的面前,原来是父亲替我买的。那带着肉味的香气,扑鼻而来,香气无比。我几乎是连喝带吞地吸到肚子里去的,以致没有好好好尝一尝肉丝面的味道。
沿小镇边缘有一条小河,属于巴河水系。在小镇的外围形成一道水湾,蜿蜒着从小镇面前向东流去,与她的母亲河长江交汇。四周有田野村落的倚靠,山上有郁郁葱葱的树林。我站在小河边,好奇地看着这美丽的风景,这也是我第一次站在这样宽、这么长的河边,让我大开眼界。只见河水缓缓地流淌着,河边的小草正在向外冒着头,大胆一点的小草已急不可奈地从地里钻了出来。顺着河流向远看去,一条碧绿的彩带飘在河边,各色的小野花绽开笑靥。清澈见底的河水,将蓝天白云纳入怀中,小河里盛开着朵朵白莲。河水慢吞吞地、缓缓地流着,打着转儿。河中游来游去的小鱼,河滩石缝中钻来钻去的小虾,你追我赶,戏嬉游乐,很是有趣。圆溜溜的河中石,憨憨地立在水里,迎着水流,动也不动。此刻,我感觉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不知是瞬间还是永恒,溅起来的水花在空中留下了永恒的姿态,一幅有静有动的画面便印入我脑中。
小镇充溢着自然的气息,就连景物也是最朴素的。农人们把河水引到了田地里,灌溉禾苗,小河边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但店所出产的稻子、小麦、棉花、花生、山药、柿子、栗子、玉米、红苕等就是这小河的水灌溉而来,滋润着小镇的一草一木,一树一花,养育了小镇的人们。别看但店这个小镇远离喧闹,偏僻一偶,没有什么名山灵寺,也没有什么奇花异草,但她朴实无华,有着桃园的味道,雅致得像是一幅农家田园城镇风景的国画。
小镇在我们那一带,最早安装电灯、电话。我也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电灯。当时觉得非常好奇。我趁着父亲上班之机,一个人呆在屋里,拉着电线开关。一关一熄,一开一亮,我感觉非常神奇。怎么一拉动那根线,灯就会亮,再拉一下又会熄灭?我心里有无数个问号,百思不得其解。一整上午,我不知拉了多少次,越拉越觉得不可思议。正在我拉着起劲的时候,父亲回到了宿舍,见我很好奇,他告诉我电灯的一些简单原理。我似懂非懂,连连点头,很是高兴。也就是从那时起,激起了我学习新知识的兴趣。
今天,沿着但店小镇街上行走,往事也不断涌上心头。记得当时有个铁匠铺,也是我最爱围观的地方。一座小屋的中间,立着一座铁铮。三个男人,一个持小锤,两个轮大锤,围着铁铮,甩开膀子,对着铁块,有节奏地击打。打得那烧红的铁,火花四溅。如同节日烟花,很是好看。
我边走边想,不经意间,我仿佛又听到了打铁的声音。莫非那个铁匠铺还在?我心里这样想着,就顺着响声追寻,果不其然,那个铁匠铺还在。只不过只有一位头发花白、穿着绿色老式军衣的老人,正在敲打着一个铁锄,我们叫做“干劲”。
我走近一问:“老人家,您在打铁?怎么还有人用这样的农具?”
老人说:“只要是种田,总还是有人需要的。”
我又问:“你老今年高寿?”他举起手,向我做了一个八字手势,接着又伸出一个巴掌。原来他有八十五。八十五岁还在举锤打铁,真的是不简单。
我惊叹地问道:“您有八十五岁?真的看不出来。怎么您一个人打?没有人帮你轮大锤?”他指指旁边一个铁疙瘩对我说:“有这个呢,不用再请人了,请人划不来。”原来老铁匠用上了锻压机具。
“你这个铁匠铺一年能赚多少钱?”我好奇地问道。
老人说:“万把块钱吧。自己养活自己冇得问题。”看着面带红光的老人,我不禁肃然起敬。是啊,人生在世,各有使命,无论崇高,或是平凡,都应值得我们钦佩。寻常百姓,不遇劫数,无须流亡,只需守着这样一个铁匠小铺,过着日子,辛勤耕耘,岁月静好,活着便是境界。生活就象那敲打的铁锤,虽有起落,终究落地,不求大富,不显大贵,平安顺心皆是美意。但店小镇,正是有了这样一些一生热爱劳动的人们,才使小镇繁衍生息。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小镇庭院,河上大桥,依然安在。河畔田埂,浣纱荷锄的男女,来来往往。但店小镇的时光,依然从容有序,人们在街上闲庭信步,于人间的烟火之中,过着平凡简单的幸福生活。
少时光阴,只有短短几载,自第一次能自己走到但店之后,后来我就常来常往,直至我十六岁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就再很少到但店了。今日故地一游,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但店镇。尽管街面上还有些脏乱,店铺摆放也不整齐,但我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的。毕竟小镇还在发展之中。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的诗句“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充分表达了我此时走完但店小镇街景的心情。
请继续在八一展示您的才华!o(* ̄︶ ̄*)o
祝您生活愉快!佳作不断!o(* ̄︶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