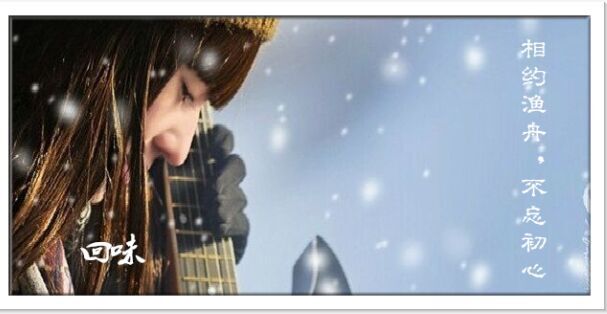【渔舟】父亲(散文)
【渔舟】父亲(散文)
一
她一直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可她一直想知道。
开始,母亲糊弄她,说他就是她父亲。后来,听邻居们乱说,她不是他亲生的。她一直疑惑不已,我是谁,谁是我的父亲呢?
她后来只上到五年级,不读书了,便开始帮着家里干活。弟妹多,她排行老大,长得高高大大的,像个男孩。
父亲脾气暴躁,动辄因一点小事,一句话,张口就骂,举手就打。
起初,父亲打她,她不像弟弟、妹妹们那般会逃跑,挺挺的站着,直直的跪着,清亮的眼睛如水似的,望着父亲举起残缺的家具。日子久了,吃饭时总担心,冷不丁父亲的碗就会飞过来。家中的碗,是买了一茬又一茬,大小不一,花色斑斓。
十五岁那年,这样的事终于发生了。她因说错了一句话,是父亲认为错的一句。她无动于衷地吃着饭,等她发觉耳边呼呼风声,惊愕地抬头,一只还有半碗饭的粗瓷碗擦着眼睛掠过。她没忘记眨眼,但眼睛还是肿了起来。痛,她莫名地恐惧。母亲胡乱地找来一些眼药给她,可是等眼睛消肿后,她悲哀地发现,她的视力几乎为零,眼前终日飞花狂舞。
她开始恨他,恨他的暴戾,恨他的酒后骂人,恨他乱摔东西。父亲一着急,家中所有成员都开始倒霉,她开始关心她的身世,但母亲总是讳莫如深,说他就是她的父亲,叮嘱她不要胡思乱想。
父亲一生最爱的事情就是流浪,自山东迁到东北黑龙江,刚在那休养生息安顿下来,又举家北迁至内蒙。在那儿,他开始开荒种田,那儿的人更是粗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动不动就倒戈相见。
她学会了开车,开着拖拉机,在荒凉的土地上游走着。
春节,家家都在包饺子。父亲心情好的时候,就是大谈他的英雄事迹,走南闯北的不知说过了多少遍的故事,若姐弟几个谁做出不耐烦状,立刻会得到直指心窝的破口大骂,形容词之多,让被骂者恨不得钻地。人多,一直难得有这么其乐融融的气氛,小妹就有点上脸了,笑嘻嘻地顶撞了父亲一句。其实就是纠正他历史传说中的破绽。说时迟那时快,三盖帘白白胖胖的羊肉饺子,全部倒在地上,滚得到处都是。那晚,在家家户户过春节的喜庆日子里,外面鞭炮雷鸣,和着父亲声嘶力竭的怒骂,年就这样过去了。
一直她就想,长大后离开他,远远的离开这个家。十八岁那年,伙同村中的伙伴去外地酒店打工,她认识了一个男孩子,贵州的,矮且丑,但心肠好,常帮助她。从小打骂怕了,一点点温暖足以让她感觉烈日当空,很快地她决定嫁给他。
踏上北去的列车,她带他来到父亲面前,父亲斜睨地俯视着这个年轻人,先是粗口,然后又提起他的脖领子,悬空而起。她气愤不已,冲父亲大叫,我们走!就这样,没有双方父母的祝福,她匆忙地结婚了。
每每打电话,父亲都会发火,说他会看面相,一看这小子不地道,看着面焉,内里做事呢,又说了句不叫的狗才是暗下口呢。谁也没想一语成谶。
或许是男人厌倦了,提起父亲便是一脸的鄙夷。她每每又不由自主地袒护父亲,这样,一次一次地吵架,一次又一次,她开始反思她的婚姻。
后来,男人说,其实你真是像极你的父亲,一样的蛮横,一样的粗俗,从此便分手了。
二
听母亲说,父亲是在1961年去的北大荒。当时,是在家几乎要饿死,逃命吧,就跟着村上的其他人北上。零下40度的日子真难过呀,父亲穿着薄薄的黑棉絮棉袄,抄着手走在滴水成冰的黑龙江北面的小屯里。
东北真是饿不死人,父亲怀着一身精湛的屠夫武艺,成天东家西家的为他们杀猪宰牛,然后拣回一些下货和着屯里的关里的一些人煮着吃,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大声的骂人。母亲就在找他父亲时,听到了父亲,像铜锣一样骂人的父亲,骂的语言豪放新鲜,像刚破肚的牛排一样热烈。
母亲脆声声的叫着,让很多老少爷们寻声转项。父亲这时也注意到了扎着红头绳黑油油大辩子的母亲,那时父亲十九岁。
父亲就搬到母亲家住。后来,父亲就自己盖了间草房,渐渐地就有了大哥,有了我。好多和父亲一样做屠夫事业的,身材都是短颈胖腰,但父亲却是高高瘦瘦的,用姥爷的话说,就是一头关里驴。驴就有个驴脾气,心情好时推磨,拉车,心情不好时则是头犟驴,母亲就成了他打靶的靶子,但过后则是后悔不已,他看着母亲鼻青脸肿的模样,总是哪里痛,哪里痒地呵护。
挨打挨骂,母亲也是气愤不已,看人家邻居男人围着女人转的,也是眼馋,偶尔也是私下落泪。父亲依旧是那个样,连名字也不会认,也不会写,是个纯粹的文盲。可他心灵手巧,看着东北有人编篮子,垒火炕,看一遍,便烂熟于心,做得像模像样的,还有别家都是白菜疙瘩玉米碴子粥时,惟有我们家常冒出诱人的肉香,这是父亲让母亲骄傲的资本。
父亲的心是软的,是村里最豪爽的男人。姥爷家的几个舅舅,哪个没借过父亲的钱,村里有几个上学的学生家里,大娘婶们也常是几毛几毛的借,父亲则喝着地瓜干辣酒,痛快地说,孩他妈,拿钱!
这句孩他妈,就是母亲万能的止痛药。
十里八乡的,没有人敢对父亲弹指,但有一人偏偏诬陷父亲偷杀他的驴,气得父亲差点把他杀驴似的杀死。那人的眼泪鼻涕流到父亲手上,把一尺多长的屠刀染成亮晶晶的颜色,父亲感觉晦气,丢下了刀,他吓得几乎走不了路。当然,这是我后来听母亲讲述的,等我回家时,父亲叫住我,是不是屯上最有名的无赖问我杀他家驴了?
我看父亲瞪着血红的眼珠,吓得要死。想跑,被父亲看出了端倪,提着我的耳朵轻而易举地提到院中。接着,父亲那分贝的骂声开始震痛我的耳膜。父亲又提着我的两个胖脸蛋,腾空悬起,脸似火烧。那年我五岁,是我一生噩梦般的回忆。
其实那个无赖,他经常诈人,偶有成功。那天隔着矮栅门,看到我家杀驴,碰巧的是,他家的驴跑出去串门了。他就怀疑,是父亲偷杀了他的驴。父亲虽脾气暴躁,但真没干过这等偷鸡摸狗的小人之事。正巧,我想去邻屯找虎哥玩,他就在半路截住我,非要我承认父亲杀了他的驴。被他纠缠的没法,他又说你说了,我就让你过去玩,于是我就说了,是父亲偷的,反正是说了就没事了呗。
结果就是,我就挨一顿暴打,好几天不敢出门玩。他也教训了那个无赖,从此,再也没人敢对父亲说三道四了。
唉,驴脾气的父亲,一生不服输的人。
感谢赐稿渔舟,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