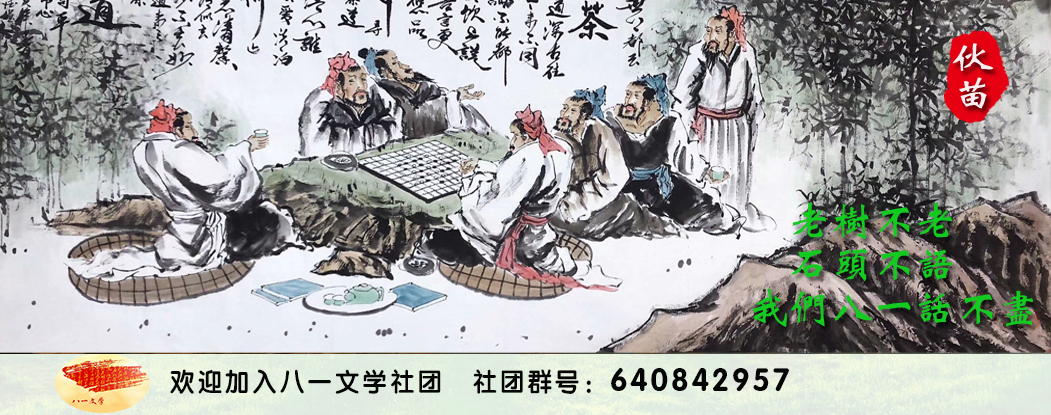【八一】爱菊的老人(散文·家园)
【八一】爱菊的老人(散文·家园)
![]() 路边的野花开了,开得烂漫,仿佛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它的绽放,只要仔细瞧瞧,这花与白菊差不多一样大小,但花瓣一丛一丛的倒像是白菊,我对花研究的太少,面临这白色花,恐怕就是白菊吧!我采撷一朵从蕊里抽出的玉丝,又在鼻下闻了声真有一股清香。虽然不是人种的花,却有一般野花媲美不了的骄傲气息,于是我把她暂时叫上野白菊。
路边的野花开了,开得烂漫,仿佛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它的绽放,只要仔细瞧瞧,这花与白菊差不多一样大小,但花瓣一丛一丛的倒像是白菊,我对花研究的太少,面临这白色花,恐怕就是白菊吧!我采撷一朵从蕊里抽出的玉丝,又在鼻下闻了声真有一股清香。虽然不是人种的花,却有一般野花媲美不了的骄傲气息,于是我把她暂时叫上野白菊。
白菊我是知道的,它洁白无瑕,倘若漫步盛开的几十亩菊园,那么你会被一望无际白色所陶醉。
白菊是性寒的,可以入药,明目而清头风,甘甜亦可泡茶。采撷几朵来用开水沏上一壶茶,坐在黄昏夕阳前的阳台上细品之时,你却感觉到一股清心明目,可口香甜,郁馥悠然来。
记得去年,我从遥远的异乡孤旅回到阔别三十有五年的故乡,我心潮澎湃,目睹故乡的山山水水,心情舒展出一种模样的敬畏。
老屋已经闭门了,锁也锈迹斑斑。翘首的檐角已挂满蜘蛛网,斑斓的墙壁已不是当年的模样。那年,父亲是一位爱画画的人,他在墙壁边缘描绘出当年最了不起的图案,曾经也是轰动了十里八村的人物,我很敬佩他。当我再次静静地站在老屋家门口,一般心酸的泪翛然从眼眶里涌出,总免不住赌物思人,对过去的往事的牵挂。
七十年代初的父亲,可是一位健壮的男子汉。在生产队以务农挣工分为主业,原来他可是一个民间高手画匠,只因为了她才放弃了这份不可多得的职业,在我心目中看来真是委屈了他的一生。
父亲,他面善、和气、憨厚、淳朴。白天随生产队员一起早出晚归,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爱干净的父亲把衣服换下,洗涤一双染有泥土气息的手,有时还擦些当年最奢侈的“蛤蜊油”。他往煤油灯一坐就是一个时辰。他认真、细仔地铺开一叠白纸,拿出笔醮上粉彩去随心所欲地画些山水花鸟的图。那年我还小,记得父亲最喜欢画菊花。初期他菊花画的品种多,黄菊、白菊、粉菊。后来逐渐地只画白菊了。他经常如此坚持与执着,父亲的菊花画图已小有名气了,炉火纯青。为此,有一名中年男子,慕名而来,他只识图爱好者,他还愿意出一元一张收藏,一次性把父亲一摞菊花画图抱走了。这一元一张在七十年代可是高价,一位农村画画师傅得到如此的第一桶金心情可想而知,父亲很感动荣幸。记得那次是父亲第一次就卖了50块钱,他欣慰地笑了,笑得是那么的灿烂。那位爱图者临走时还放在一句话,有多少我收多了,下个月我再来。于是父亲笔耕不辍,已经成了一名画菊、爱菊了不起的人物,只差“菊王”绰号了。
往事的追忆不堪回首。我站在这满目疮痍的老旧屋前,围着转了一周,我思绪万千。时间过去那么年,我想起父亲,也开始爱上了菊花了,尤其是白如洁洁的白菊花。至今,每当菊花出现在我的眼帘,总有一番思念和追忆。
由于父亲爱菊、画菊如命,为此,我对父亲爱菊的嗜好瞬间产生了一种莫生的好奇,总想弄清其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九七八年秋,酷热的夏天悄无声息地渐行渐远,迎接我们的是“秋老虎”,白天仍然保持那份闷热,即使你坐在树荫下也是摇着蒲扇。
那年的秋天,刚上初中。我那岁头刚好十五周岁。再过两年就毕业了,面临马上就要参加全省中考,父亲为了我能顺利考上高中,他每天夜里亲自煮两只鸡蛋给我补身体,并鼓励我说:儿子,鼓把劲,等你考上高中我带你去看望你母亲。我当时纳闷,家中的母亲是谁的母亲?是妹妹的,难道不是我的母亲?而我的母亲身在何处?怎么重来没有听到父亲提起过她呢?被父亲这么一说我真想迫不及待地想见母亲,难道我的母亲不在这,她又在哪?
父亲知道了我的心事,他再也没有提过此事。为了一句话,我更加刻苦学习,为了一句话,我更加早日考上重点高中,早一刻见到我思念的母亲。
父亲是一位勤奋的人,画白菊视为他每天的必修之课,难道这与母亲有关?我为了不让父亲难过,也不忍心让他叙述往事,姑且我暗暗地下了决心。我把我的座右铭贴在床边,我终于鼓着勇气写上歪斜的几个字:高中后见母亲!
一日,父亲走到我经常写作业的桌边,他停留了好一会儿,我站在哪里,从他背影知道了父亲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沉重,我不敢多想,只有避开,收敛我欣酸的悲怆。
夜里,我苦思冥想,用猜测的排除方法想从中找到合适的答案。可是我是晚辈那有权力过问这事情的来龙去脉?问爷爷奶奶他们不理我,我不敢问妹妹的母亲,怕他不高兴。不过从父亲酷爱白菊我好像知道了点蛛丝马迹。我想问父亲又担心他怒怼,所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其中的秘密,这颗心一直悬着多年。
两年后,我如愿以偿地上了重点高中。我还是不敢开口问父亲,我怕他眼睛里噙着泪、伤心的苦楚。
七月中元节,父亲又开始闷闷不乐。我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到这几天父亲抑郁、思念、无奈的表情。每年的七夕之后,农村有个祭祀祖先的习俗。清明扫墓,中元烧冥纸祭祀祖先这是必不可少的。
七月十五日的上午,父亲穿好了一套平时舍不得穿的“礼服”。这天,他终于穿得很整洁,衣服是旧了点,没有皱褶,看上去很有当者的风度。在那个年代,我打懂事起才看见父亲如此庄严、肃穆、很像一位高大可攀王者风范,没有霸气却有威性,炯炯有神。我叫了一声父亲,他“嗯”了一声,似乎不悦。他走到我写作业的老书桌边轻轻地说:儿子,今天多烧一个包吧!我疑惑不解地望着他,父亲那平静的面靥冷若如霜,所以我不敢多问,也不敢对峙,只有接过祖先谱开始一个一个祖先写下名字。这时我才知道母亲的名字姓白名菊。我沉默不语,斜视父亲一眼,只听见父亲再次平静说道:给你娘写清楚地址,不然收不到我们的祝福和礼物,儿子。我终于明白了生我的母亲叫白菊,不听话的泪水流落面颊,而我父亲静静地走开了。
时间过去那么多年,每每看见真实的白菊花或者翻阅泛黄的父亲生前留下的墨宝绘画,我内心的一股思念的潮汐涌来,吞噬了我的全部。
父亲是勤劳的农民,他也是一位民间画手,他已离我远去三十三年了。
秋来了,叶儿逐黄,一阵一阵秋风吹来,给我们特殊的一股凉意。
我再次回到故乡,踏上荒冢的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我找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坟墓。墓碑模糊了,隐隐约约可看清父亲和母亲的名字。我抚摸着父亲的遗像,虽然很模糊,总有个父亲形象图还在,可是母亲长什么样子我还是一个未知数。由于风雨吹打以及阳光曝晒,父亲和母亲的坟墓还在。我围着他们俩老的坟墓走了一圈,脚步放得慢,矜持呼吸的声音,很怕惊醒这位曾经令我敬佩的老人以及日夜思念的母亲。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父亲已有九十五了,母亲呢?岁数还是一个问号。
一堆黄土,长满杂草,墓前不知什么时候长满菊花,是不是父亲在那里还是喜欢洁白如雪的白菊?我只有仰望天空,喟然长叹。
一阵秋风吹来,犹如一双无形温柔的手,摇曳着墓碑前的许多菊花,清香扑鼻,仿佛及牵扯我对父母双亲的思念。我跪下了,在这静谧的山野又多了我一份对母亲的思念,想见她美丽的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