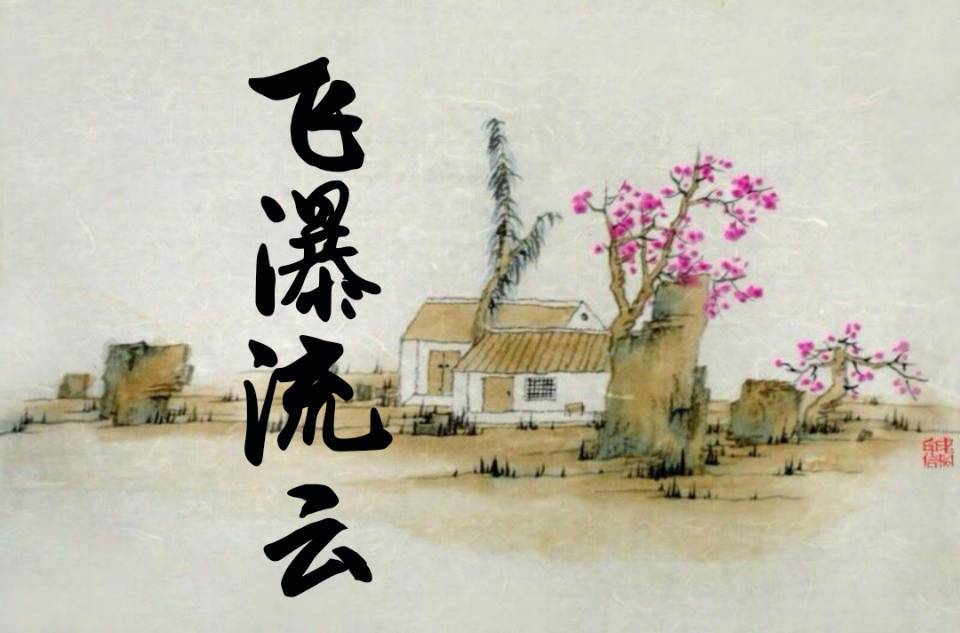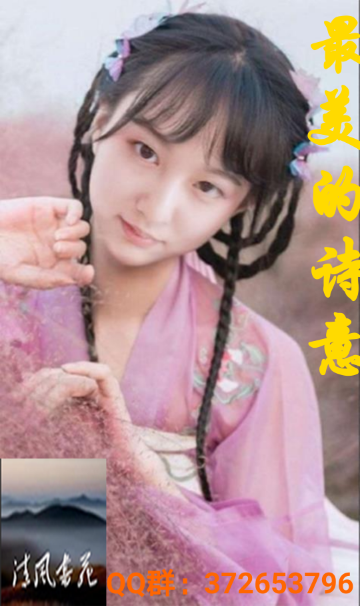【清风】浓浓的鸡汤浓浓的父爱(散文)
【清风】浓浓的鸡汤浓浓的父爱(散文)
![]() 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随着春节的临近,我真的开始想家了,想念亲切如昨的故乡,想念古稀之年的双亲,想念那香浓鲜美的鸡汤。
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随着春节的临近,我真的开始想家了,想念亲切如昨的故乡,想念古稀之年的双亲,想念那香浓鲜美的鸡汤。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农村,贫穷依然很普遍。那时候,很多人家的孩子初小毕业后,就要离开学校回到农田,帮着父母操持农活;或者找个有手艺的老师傅,跟在后面做几年学徒,将来也算是个有手艺的人;或者父母稍有点本事的,便托人把孩子送到乡办厂、村办厂做工,赚取点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然而,等到哥哥、姐姐和我陆续初小毕业时,父母却作出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那就是让我们继续上学,直到走进大学的殿堂。
那个时代,如果仅仅供男孩上学,倒能得到邻居们的赞赏,但父母偏偏还要供姐姐上学,便引来了邻居们的议论。父亲是位乡村兽医,母亲是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家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六亩承包田和父亲微薄的工资。所以,当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时,不但引来邻居们的嗤之以鼻,也令我们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绝境。
然而,父母却始终初心不改,辛勤劳作之余还额外承包了四亩多香瓜地,以此来解决我们学费上的缺口。不仅如此,父亲甚至固执地认为,孩子们上学要用脑子,光靠吃饭喝粥是没有营养的。于是,他们还挤出时间,在院子里垒起鸡窝,拉上绳网,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食和田野里的杂草,硬是饲养了一群鸡。从此,这些鸡们,便成了我们兄妹三人打“牙祭”时固定的祭品了。
那时,我们兄妹三人都住校,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父亲总会计算好时间,磨刀霍霍向公鸡,开始他的杀鸡工程。于是,每个星期六的傍晚,码头边总会出现一个瘦弱的身影,佝偻着腰身,捣饬着拔了毛的公鸡。每当此时,总会有过路的邻居发出或赞赏或嘲讽的声音。然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父亲却都是淡淡地笑着,不做任何的解释。
当我们陆续抵达家中,正是饥肠辘辘之时。闻到厨房里飘出阵阵香气,顿时令我们食指大动、口水涟涟。我们纷纷放下书包,嬉笑打闹地奔向厨房,在大块朵颐之前让眼睛先享享福。这时,恰逢父亲开始独特的“炝菜”制作,只见他用汤勺小心翼翼地从汤锅里捞出鸡珍、鸡肠、鸡肝和鸡肫等鸡杂,分别细细地切成薄薄的片状,再装入一个敞口盘子里,加入盐、酱油和拍碎的大蒜瓣等调料,稍稍搅拌,便会冒出不一样的香味,让我们肠胃的活跃程度瞬间达到峰值。
那时候的孩子懂事早,没有父亲的允许,决不会偷偷吃上一块。看着我们一脸的馋样,父亲没有斥责,只有挂在脸上的淡淡的微笑。因为爷爷奶奶没有和我住在一起,所以在开饭前,父亲总会先用一只大海碗,从锅里捞出些许鲜嫩的鸡肉脯,再盛些鸡汤,让我送给他们一起品尝品尝。
一碗鸡汤,捧在我的手心,如同一件易碎的稀世之珍。我一边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一边贪婪地嗅着诱人的香气,恨不得一口全部吞下肚。待我兴冲冲地赶回来后,全家才依次坐上席,开始这种难得的饕餮盛宴。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尽管内心对美食有着极度的渴望,但我们绝不会去争抢,通常都由父亲来分配,大家才会心安理得地享受美食。
这时,父亲已坐到桌子的上席,踌躇满志地抓起筷子,如同分封功臣般,对每个人一周来学习进行总结讲评,夸赞一人,则挟起一块鸡肉,再夸赞一个,又挟起一块鸡肉,母亲也在分封范围之内。
父亲杀鸡还有一个技巧,充分利用他的专业技能,找到鸡大腿到鸡胸脯中间的关节,巧妙地切割成鸡大腿两个、鸡二腿两个,这样我们就可能每人分到一块鸡腿肉了。在我们兴奋地享受美食时,父亲则淡淡地捞起鸡头、鸡脖、鸡爪,皱着眉头慢慢地咀嚼起来。偶尔目光交汇,他又露出满足的神情,夸张地说道:嗯,鸡头、鸡爪,都是我的最爱,你们享受不到了。然后,便引来我们一阵轰笑,嘲笑父亲不懂鸡肉的美味。
如今,我们兄妹三人已走出大学的殿堂,在都市里开始着自己的生活。而年迈的父母,仍然坚守在那片藏着我们许多回忆的故土,时时盼着儿女的归来。
思绪渐渐蔓延开来,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瘦弱的身影,腰身已经越发变得佝偻,眼睛禁不住湿润起来。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今年过年,我一定要回家,再喝一口父亲做的美味鸡汤。